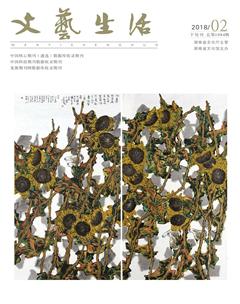一縷情思系家國
李肖肖
摘要:《詩經》中有許多詩篇反映了那個時代貴族間的政治婚姻。出于鞏固政權的需要,王室貴胄們以婚姻為紐帶,來壯大自身勢力,維護各諸侯國之間的政治穩定。在上層婚制和成長環境的雙重規約下,貴族女兒們的人性訴求被政治利益無情吞沒,以至于她們的婚姻觀念中沒有愛情的概念,有的只是男權政治反復灌輸強調的家族、邦國利益。從家族利益出發考慮一切,既是家族規約的要求,亦是她們在生活環境影響下,意識中朦朧存在的本位觀念。
關鍵詞:貴族聯姻;利益聯結;貴族女兒;婚姻觀念
中圖分類號:H13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5312(2018)06-0001-02
一、引言
《詩經》中有許多詩篇反映了那個時代貴族女兒的婚姻狀況,這些詩篇有的描寫了貴族女兒婚嫁時盛大華麗的媵婚場面;有的透露了貴族女兒婚嫁后歸寧不得的邦家之思;還有的展現了她們被拋棄后的精神世界。由于上層禮法和成長環境的雙重禁錮,這些貴族女兒對愛情的本能需要被淹沒,在她們的婚姻觀念里充斥著的是邦家宗族的觀念。本文以政治聯姻這一在《詩經》時代普遍存在的貴族婚制為背景,結合先秦婚姻禮制,重點分析《詩經》中的《鄘風·載馳》、《小雅·黃鳥》、《小雅·我行其野》三首詩,來透視先秦時期貴族女兒的婚姻觀念,以期明晰貴族婚制的潛規則對這些貴族女兒意識形態和婚姻趨向的影響。
二、《詩經》中的貴族婚戀詩及其政治功能
在《詩經》中記載了許多合二性之好的貴族婚姻,如《大雅·綿》中記載了周之大王古公亶父率領族人在遷往岐山之下的過程中娶了姜姓女子為妻。姜姓是遠古部落中的大家族,其與大王姬姓家族的結合無疑促進了周部族的壯大,因而周族人得以在岐山之下穩固發展。在《大雅·大明》中記載了古公亶父的兒子季歷與殷商的近畿國家摯國任姓的女子聯姻,大任生文王,文王又與商朝有莘國姒姓女子結為婚姻。《史記》載:“帝禹為夏后而別氏,姓姒氏。”大姜、大任與大姒作為周室三母,亦是貴族女兒,其與姬姓周部族的聯姻在保障幾大氏族間安全穩固,促進彼此發展壯大中無疑發揮了重要作用。在《史記·外戚世家》中,司馬遷日:“自古受命帝王及繼體守文之君,非獨內德茂也,蓋亦有外戚之助也。夏之興也以涂山,而桀之放也以末喜。殷之興也以有娥,紂之殺也嬖妲己。周之興也以姜原及大任,而幽王之禽也淫以褒姒。”即充分肯定了貴族聯姻與夏、商、周三代王朝興亡之間的緊密聯系。《禮記·郊特牲》中說:“夫婚禮,萬事之始也,娶于異性,所以附遠厚別也。”娶異性女子是為了讓遠者歸附,以姻親的形式將異族納入本部族的勢力范圍,來維護彼此邦家之間的安全穩固。就周代社會而言,統治者實行的是分封制,要想使諸侯歸順,遠國來附,周王室自身首先要有強大的實力,而這種實力的建立與鞏固則需要外援,取得外援的最佳方式莫過于政治聯姻,結成甥舅之國。由此來看,在整個先秦時代的政治建構中,政治聯姻是固國安邦的一項重要手段。在娶妻助祭宗廟、繁衍子嗣的時代主題下,這些貴族女兒們還要擔負起聯結異族,維護邦家利益安全的責任。所以那些在當時被評價為賢德后妃,貞順之婦的貴族女兒,這些贊譽也都是從其為家族利益帶來的好處角度所給出的。“女子,從人者也。”這極其簡短的一句話道出了封建社會中國女性悲劇命運的根源,她們沒有獨立的社會地位,只能“從人”。“婦人在家制于父,既嫁制于夫,夫死從長子。”家庭和婚姻限制了她們全部的生活范圍,禁錮了她們的一舉一動,也侵蝕了他們的意識觀念和精神世界。
三、成長環境和上層婚制規約下貴族女兒的婚姻觀念
(一)貴族女兒婚姻觀念中家國意識的成因
在《詩經》時代的婚約習俗里,處于支配地位的是“父母之命,媒約之言”,正如《齊風·南山》中所歌:“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娶妻如之何?匪媒不得。”在世代沿襲的婚約習俗下,絕大多數的女子只能無條件地接受父母的安排,而政治聯姻在穩固邦家中的重要作用決定了貴族女兒們比起下層婦女,還要擔負起為家國利益考慮的責任。雖然在男權社會里,這些貴族女兒沒有自主選擇的權利,但作為有生命的個體,她們有自我的意識和價值判斷,她們之所以甘心做家族之間政治利益的犧牲品,除了父權和禮制的客觀因素外,主觀方面則在于這些貴族女兒們已經不自覺地將家國利益置于自己婚姻的首位。分封制體系下的弱肉強食,使得這些貴族女兒不得不為邦家的安全穩固貢獻自己的一份力量。所以,她們不得不奉獻出自己的人生幸福,在別國充當賢德、貞順的妻子,以扮演好維護邦家利益的角色。當然,并不是所有的貴族女兒都有這樣的認識和思想高度,甚至可以說她們中的大多數都沒有這樣的意識,只是在生長環境和正統觀念的浸染下,不自覺地擁有了這種備受家族重視的婚姻觀念。
(二)由《鄘風·載馳》、《小雅·我行其野》、《小雅·黃鳥》透析貴族女兒們婚姻觀念中的家國意識
在《詩經》所涉及的貴族婚戀詩中,最能體現貴族女兒“一縷情思系家國”的莫過于許穆夫人。《列女傳》記載:
許穆夫人者,衛懿公之女,許穆公之夫人也。初,許求之,齊亦求之,懿公將與許,女因其母而言曰:‘古者諸侯之有女子也,所以苞苴玩弄,系援于大國也。言今者許小而遠,齊大而近。若今之世,強者為雄。如使邊境有寇戎之事,惟是四方之故,赴告大國,妾在,不猶愈乎?今舍近而就遠,離大而附小,一旦有車馳之難,孰可與慮社稷?衛侯不聽,而嫁之于許。
歷來對許穆夫人的評價,都集中于說她是一位有政治眼光的愛國女性,但很少有人解析這一政治眼光得以形成的現實環境。在壁壘森嚴的男權統治下,許穆夫人的這種政治洞察力更加鮮明地體現了她從小所接受的教育:“苞苴玩弄,系援于大國。”她之所以對當時諸侯國之間弱肉強食的現實環境有那么深刻的認識,根本原因也在于她所成長的現實環境,在于她生命意識中的家邦本位觀念,因而在自己的婚姻大事中,她能有如此的眼界和想法。毫無疑問,在許穆夫人的婚姻觀念里,家國利益是她考慮的首位。因此,在得知自己的宗國被滅時,她不再畏懼夫權的淫威和當時的禮制,毅然奔赴漕邑吊唁衛侯。面對家國淪喪的現實,這意味著她一度置于生命本位的精神支柱倒塌了,所以她無暇顧及“既嫁從夫”的教條,為了挽救宗國,這位衛國女兒毅然沖破了經圣藩籬,在男權統治的時代里,高度凸顯了她的家國情懷。
在《小雅·我行其野》中,同樣表現了這位貴族女兒婚姻觀念中的家國意識。盡管這是一首棄婦詩,但其語詞風格不同于《邶風·谷風》、《衛風·氓》等棄婦詩中下層婦女的悲吟。在這首詩中,這個被拋棄的貴族女兒講到的是:“婚姻之故,言就爾居。爾不我畜,復我邦家。”由于庶民女子嫁到外邦去的可能性是極小的,且《詩經·小雅》中的作品多為貴族所作,所以這應該是一位貴族女子,嫁到異邦諸侯之國而遭棄的自述。鄭箋云:“樗之蔽芾始生,謂仲春之時,嫁娶之月。婦之父,婿之父,互謂婚姻。我乃以此二父之命,故我就女居。”孔穎達解釋說:“我嫁他族以求夫,唯得無行不信之惡夫。既得惡夫,遇己不善,乃責之言:‘我以我父之婚,爾父之姻,二父敕命之,故我就爾而居處為家室耳。我豈無禮而來乎!而惡我也!你既不我蓄養,今當復反我之邦家矣。”這一貴族女兒秉承父命,為自己的家邦而婚配異邦,在被拋棄后,支配這一貴族女兒生命意識的依然是自己的邦家。可想而知,這些貴族女兒們從小就被禁錮在正統禮制的藩籬中,所受的教化便是要在以后成為賢德后妃,守禮貞婦,事事從邦家利益出發,扮演好鞏固異族大邦關系的婚姻角色。
從這一政治背景來解讀《小雅·黃鳥》這首詩,則更能強烈地感受到這一貴族女兒婚姻觀念里根深蒂固的家國本位觀年。鄭箋云:“婦人自為夫所出,而以刺王也之由。刺其以陰禮教男女之親,而不至篤聯結其兄弟。夫婦之道不能堅固,令使夫婦相棄,是王之失教,故舉以刺之也。”孔疏云:“兄弟謂婚姻嫁娶,是謂夫婦為兄弟也。夫婦而謂之兄弟者,《列女傳》曰:‘執禮而行兄弟之道。何休亦云:‘國安危可否,兄弟之義,故比之也。”胡承珙在《毛詩后箋》中云:“此詩自傳、箋以后,人人說殊。王氏、蘇氏以為賢者不得志而去;呂記、嚴輯以為民適異國,不得其所之詩。然以經文證之,此言‘復我邦族與《我行其野》之‘復我邦家正同。彼明言‘婚姻之故而與此詩相次,則此詩自亦為室家相棄而作。毛鄭之說,不可易矣。《易林·乾之坎》:‘黃鳥采菜,既嫁不答。念我父兄,思復邦國。焦氏正用毛義也。”因而胡氏認為這是一首貴族棄婦之詩。
從詩的內容來看:“此邦之人,不我肯穀。言旋言歸,復我邦族”以及“此邦之人,不可與明”鄭箋云:“‘明當為‘盟。盟,信也。”這首詩涉及的應是兩大邦族之間的政治聯姻。這兩大邦族結盟為誓,約為甥舅之國,來保障彼此之間的利益,而這種男權社會的外交策略也深刻影響到了成長于斯的貴族女兒,以至于她深明自己的婚姻屬性,所以在被拋棄后,受生命意識中家邦觀念主導的這一貴族女兒的話語中充斥著的是“復我邦族”。正因為清楚自己的婚姻是兩大邦國進行利益交換的籌碼,所以她才反復提到“此邦之人”以及“歸我邦族”。由此來看,受正統禮制嚴格制約下的貴族女兒,她們的人性訴求早已被貴族政治扼殺在搖籃里,成長環境使得她們的婚嫁觀念總是不自覺地含有濃厚的政治意味,與家國利益相聯系。
四、結語
任何時代,任何階層的意識形態都是那個時代政治、經濟的反映。先秦時期分邦建國的政治體制規約了那個時代的禮樂制度。貴族聯姻制既是鞏固王室地位的需要,也是各諸侯國保障自身安全穩固的需要。這種政治上的需要也就直接決定了貴族女兒們的婚姻走向并根深蒂固地影響了她們的婚姻觀念,使得她們在被動接受的婚姻中只知有家國的存在,不知有愛情的存在;只知自己的婚姻關乎邦族利益,卻不曾意識到自身的情感需要。這種貴族聯姻的影響也是極其深遠的。在整個中國封建社會里,政治聯姻都普遍存在著,即使是在思想高度解放、民主政治高度發展的今天,名門望族間的政治聯姻也依然為數不少。
時代在前進,文明在演進,我們依然需要反思當今社會的婚姻制度。畢竟愛情才是婚姻中的天然因子,所以男女雙方應該以自己真實的情感需要作為締結婚姻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