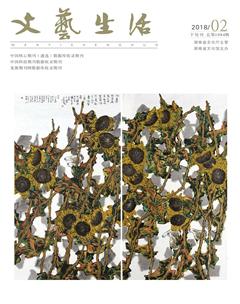蘇軾《黃州寒食帖》賞析
楊陽
摘要:作為文人書法的代表人物,蘇軾自小接受傳統儒家教育,在思想上融會貫通,博學而不死學,在文章上大有建樹,影響了北宋文壇。作為一名丈人,書法是其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卻不是其在意的地方,他認為書法是丈人的一部分,無意于書。雖是如此,他卻很好地將書法融于綜合修養,其修養也直接影響了他的書風。
關鍵詞:《黃州寒食帖》;文人書法;書風;情感
中圖分類號:1207.2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5312(2018)06-0005-01
一、逆境的灑脫——《黃州寒食帖》其文
《黃州寒食帖》,蘇軾撰并書,墨跡素箋本,行書17行,129字,現藏臺北故宮博物院。此帖是蘇軾行書的代表作,被譽為“天下第三行書”。元豐三年(1080年)二月,45歲的蘇軾由于“烏臺詩案”,被貶黃州團練副使。這是蘇軾第一次被貶,由大學士被貶黃州,這一落為大落之勢。
這樣的貶謫,無論是官職的變遷,地方的適應,還是從精神上,對于蘇軾都存在太多的反差。縱觀其一生來看,初次被貶是難以接受的。政治抱負上郁郁不得志,在生活上也是過得非常潦倒。宋神宗元豐五年(1082年),也是其被貶黃州的第三年,四月寒食節那天,蘇軾寫下了兩首寒食詩,詩中發人生之嘆,屬于遣興的詩作。詩的內容也是被貶的這三年經歷,因為種種遭遇,蒼涼、惆悵成為了這文中的主調。在這種心境和環境下,有感而發,讓這兩首詩意味耐人尋味,不過遺憾的是,因為蘇軾這件作品的書名所累,兩首詩的內容卻少有人問津。這當中的內容意義深遠,是研究蘇軾生平重要線索和論證。
詩中天寒連雨,滿景荒涼,或許蘇軾并沒有所說的這么凄慘,或許他別有用意。畢竟藝術來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詩文作為一門藝術亦不離其中。而看其在黃州三年的日子倒也自在,職位雖小但空閑,自清荒地,開墾種植,荷月帶鋤歸,又有愛妾朝云相伴,日日詩書暢言,研究吃食,“東坡肉”即從此出。可他又為什么如此形容他的處境呢?因為是人生中的第一次被貶,心境上是想不開的。只是還有一個原因,新黨排斥,不想讓他太舒坦,所以在詩文方面則一改之前《赤壁賦》的灑脫,多幾分傷感憂郁。這或許是故意寫給那些不喜的人聽的。
二、理性的率意——《黃州寒食帖》其書
《黃州寒食帖》橫34.2厘米,縱18.9厘米,129字大小不一,最大者與最小者對比相差甚遠,卻依然氣息流暢,富于變化跌宕。全帖展現了蘇軾特有的造字處理方法,無意于筆法,點畫信手本煩推求,卻又使得技法豐富,使后人多為推求。這種我行我素的書風特點,總讓人有太多的敬佩。如仙人之氣,道家無為,意氣豐富。有人評蘇軾“多病筆”,卻說字雖肥,而展現了“短長肥瘦各有度”的自信,這種自信多得益于他的經歷與修養。“石壓蛤蟆”的字形,遇到了宋人尚意的意氣灑脫,而使《黃州寒食帖》由此相傳。
書法的創作,一般都遵循書法的自然規律,這當中包含文人的載體,情感的變化深入,書法創作的自然元素等。由緩入急,由平漸急,而至于筆墨酣暢處,則為書法化時,是為高潮也。從一開始思考這三年的經歷讓蘇軾寫下了第一筆,單純以為憑借一腔抱負而國富民強的心受到了強烈的打擊,這個打擊來得太意外,最終以迫不得已來接受。因為有這一情感的升華,在一個寒雨連綿的夜里,寫下了這兩首詩。本來只是篇草稿,片紙閑情,都以為會煙消云散,率真之處,可見一斑,相較于《祭侄文稿》而言,則表現出了更多的理性。詩稿一般只是作為譽抄的對象,而使有大小錯落,各種線方向的轉變也是無意的,是率意的,可千百年后的今天,再去細細品味其中韻味,多有滄桑的美感,有些地方太多的技巧無法復制。嘆服之間卻也不得不佩服,有率真的同時,也會理解出這種率真又有不少的理性。從重疊的那幾個字來看,輕輕一點即表現出了作者的停頓節奏,輕緩有致,錯落有間。再相比《祭侄文稿》而言,因為文體的不同,也注定了作者的情感不同,顏魯公急憤,更加悲切。所以在錯誤處,蘇軾則選擇了更加理性的右邊點點式,屬于文人的范疇。與顏魯公不同,他的修改方式服務于他的書風和線條的感覺,在行文、結字、用筆及修改的細微之處,共同演繹著宋人尚意的和諧樂章。
《黃州寒食帖》中,蘇軾以極具魅力的藝術創造力展現了其過人的長處,正如其所說,“各有度”的處理下,則更加體現了一個藝術家過人的創造力。因為在藝術的創造中,除去技法之外,能夠體現藝術升華的就是對“度”的把握,有了很好的狀態和感覺,安排下來的面貌則是和諧平靜又耐人尋味,內有乾坤的變化。所以這樣的作品出示人面,蘇軾自信地認為“誰敢憎”,獨立、自信,這種融于一體的進發是成功的,對藝術的一種無為的創造。要達到藝術的設計,便需要藝術家的率意。而蘇軾的這種理性中的率意,則是更好地把握一個度,這也是《黃州寒食帖》的獨特魅力所在。欣賞此帖,往往能看見蘇軾的內心和經歷對其的情感變化,由此引發出來書法創作是直觀的,最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