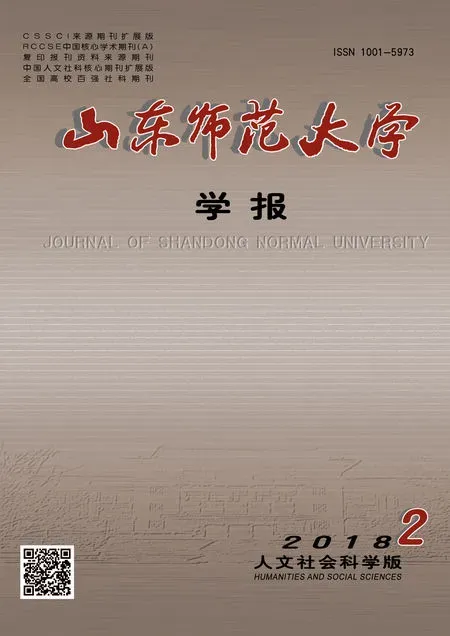桂馥《札樸》標點瑣議*
張金霞
( 山東師范大學 文學院,山東 濟南,250014 )
給古書加標點是古籍整理的一項重要內容,也是一項最基礎最根本的工作 。標點正確與否,直接反映出一個人對作品的理解程度。標點錯了,其他如注釋、翻譯、研究等都無從談起。魯迅就曾說過:“標點古文真是一種試金石,只消幾點幾圈,就把真顏色顯出來了。”①《魯迅全集》卷五《點句的難》,北京:同心出版社,2014年,第404頁。在現代標點符號推行之前,古人是在文中需要停頓的地方加上句讀。句讀是讀書的一項基本功,古人也十分重視句讀問題。《禮記·學記》:“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群……”其中所說的“離經”,就是指斷開經文句讀。服虔是東漢著名的經學家,給《左傳》做過注釋,但是搞錯了一處句讀。唐代孔穎達發現了這個問題,就對《左傳·昭公十六年》的這一處斷句錯誤進行批評:“尚未能離經辨句,復何須注述大典?”②《十三經注疏》,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這個批評很尖銳。
無論是句讀還是施行現代標點,都是一項十分重要而又繁難的工作,不容小覷。要做到標點完全正確不出差錯,可謂難之又難,必須具備語言學、文字學、文獻學等多方面的知識,同時又要從思想上高度重視這一工作。楊樹達在其《古書句讀釋例·敘論》中說:“句讀之事,視之若甚淺,而實則頗難。《后漢書·班昭傳》云:‘《漢書》始出,多未能讀者,馬融伏于閣下,從昭受讀。’何休《公羊傳序》云:‘講誦師言,至于百萬。猶有不解,時加釀嘲辭,援引他經,失其句讀,以無為有,甚可閔笑者,不可勝計也。’觀此二事,句讀之不易,可以推知矣。”③楊樹達:《古書句讀釋例》,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呂叔湘也說:“標點古書是一件不很簡單的工作。”④呂叔湘:《通鑒標點瑣議》,《中國語文》1979年第1期。
近幾十年來,我國在古籍整理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在政府有關部門和各方專家的共同努力下,出版了大批施加了新式標點的古籍,有效地保存了古籍,極大地方便了廣大讀者,是一項功在當代、利在千秋的偉業。
在已經出版的施行了新式標點的古籍中,大多數水平都較高,但也有一些不能盡如人意,比如有的本子斷句、標點錯誤的情況時有發生,有的甚至還比較多。這不僅不能給讀者提供方便,反而會貽害讀者。中華書局1992年版桂馥《札樸》,就屬于這一類。
桂馥,清代《說文》四大家之一,著有《說文解字義證》,同時有多種著作傳世,《札樸》就是其中之一。《札樸》是桂馥晚年所作的學術筆記,內容廣博,于經學文獻、語言文字等均有重要價值。《札樸》在清代有兩個刊本:一是刻于嘉慶十八年(1813)的小李山房校刊本,一是刻于光緒九年(1883)的長洲蔣氏心矩齋校刊本。后來又有1958年商務印書館據蔣氏心矩齋校刊本排印的斷句本和1992年中華書局以小李山房校刊本為底本的點校本。中華書局點校本的出版方便了讀者,很多研究桂馥及其《札樸》的人都以此為據。但是,這個本子又確實存在許多不當之處。為了對古籍整理負責、對廣大讀者負責,就需要指出其中的錯誤來。中華書局1992年點校本《札樸》的標點失當之處頗多,今擇要略陳如下(原為豎排,今改橫排,標點符號隨之作相應變動)。行文次第主要以點校本《札樸》頁碼為序,但如有相類似的問題,也做相應的集中,以便討論。
1.P4“冶容”條
《太平廣記》引《易·蠱》:“容誨淫。”《南都賦》:“侍者蠱媚。”五臣作“冶媚。”《一切經音義》云:“《聲類》蠱,弋者反。《周易》作冶,冶容誨淫。劉瓛曰冶,妖冶也。《西京賦》:妖蠱艷夫。”
今按:桂馥此條是說“蠱”有“弋者反”一音,讀與“冶”同,在古代文獻中“蠱”與“冶”可通用,《周易·系辭上》之“冶容誨淫”,《太平廣記》引作“蠱容誨淫”。點校者沒有讀懂這段文字,又受“蠱”字迷惑,誤以為是《周易》的蠱卦,致使自己標點錯誤。不但如此,點校者還在校勘記中批評《太平廣記》引用有誤。校勘記曰:“《易·蠱》‘容誨淫’,此出《周易·系辭》,不是《蠱》的內容,《太平廣記》引誤。”這樣真是太主觀了。
正確的標點是:《太平廣記》引《易》:“蠱容誨淫。”
2.P6“六宗”條
六宗,鄭氏以為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案:《月令》:“孟冬之月,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鄭《注》:“天宗,謂日月星辰也。季冬之月,乃畢山川之祀,及帝之大臣、天之神祇。”鄭《注》:“孟月祭其宗,至此可以祭其佐也。帝之大臣,句芒之屬。天之神祇,司中、司命、風師、雨師。”馥案:鄭既以司中、司命、風師、雨師為宗,今又以為佐,其說六宗,有星辰無日月,其說天宗,則日月星辰兼有,豈天宗六宗各別,不相涉邪?蔡氏《月令章句》說天宗云:“日為陽宗,月為陰宗,北辰為星宗,五經異義。”賈逵說六宗云:“天宗三,日、月、星辰;地宗三,泰山、河、海。”
今按:此條的標點問題較多,下面分述之。
(1)“孟冬之月”下有兩條“鄭注”,這就不對了。原來,“季冬之月,乃畢山川之祀,及帝之大臣、天之神祇”乃是《禮記·月令》原文,而非鄭玄的注。這就是把《月令》的文字當成注文了。
(2)再看“蔡氏《月令章句》”之后的部分。《五經異義》是書名,東漢許慎著。賈逵是許慎的老師,許慎在《五經異義》中引用了他的老師賈逵關于“六宗”的說法,桂馥在此引用之。而標點者誤把“五經異義”理解為一般的語句,放在蔡氏《月令章句》引文之內,這就錯了。正確的標點是:蔡氏《月令章句》說天宗云:“日為陽宗,月為陰宗,北辰為星宗。”《五經異義》賈逵說六宗云:“天宗三,日、月、星辰;地宗三,泰山、河、海。”
3.P7“予弗子”條
啟呱呱而泣,予弗子。《釋文》:“子,鄭將吏反。”案:《列子·說符篇》:“禹惟荒土功,子產弗字。”孔《傳》:“聞啟泣聲,不暇子名之。”
今按:此句意思是大禹因為忙于治水,兒子啟出生后卻無暇顧及,沒有給他起名。“子產”,是指兒子啟出生,點校者卻在“子產”下加上了專名號,誤把這里的“子產”當作鄭國的政治家子產了。另外要說明的是,“禹惟荒土功,子產弗字”一句,出自《列子·楊朱篇》,而非《說符篇》,這是桂馥記憶有誤。
4.P8“夔夔”條
《札樸》一書,引文特多。此書點校者常把引文誤作非引文、非引文而誤作引文,引文脫落和引號外溢的情況常常發生,特在此集中討論之。下面5到9條都屬于此類情況。
5.P16“予造天役”條
《大誥》:“予造天役。”《釋文》引馬注:“造,遺也。”案:“遺”當為“遘”,傳寫之誤。《漢書·翟義傳》引《書》“予遭天役,遭有遘義。”故馬注訓遘。
今按:“遭有遘義”是桂馥的解釋,而非《漢書》引《書》之文,故不應在引號內。
6.P64“鷸”條
《說文》:“鷸,知天將雨鳥也。”《禮記》曰:“知天文者冠鷸。”……《說文》所引《禮記》,今無此文,《逸周書》:“知天文者冠鷸。”
今按:《禮記》曰:“知天文者冠鷸。”此為《說文》引文,因此,應在《說文》的引號之內。其實桂馥在后面已經指出了《說文》所引《禮記》此語,今傳本《禮記》無。
7.P82“記曰”條
僖二年《公羊傳》:“宮之奇果諫。”《記》曰:“唇亡則齒寒。”何休云:“《記》,史記也。”馥案:《記》與《志》同,《左傳》所稱前《志》、《軍志》、史佚之《志》,皆是也。
今按:僖二年《公羊傳》:“宮之奇果諫。”《記》曰:“唇亡則齒寒。”標點有誤。按照這樣標點,只有“宮之奇果諫”是僖二年《公羊傳》的內容,《記》曰“唇亡則齒寒”是與前面并列的另一內容。實際上,“《記》曰‘唇亡則齒寒’”是宮之奇的話,即宮之奇向虞國國君進諫的話。所以,正確的標點是:僖二年《公羊傳》:“宮之奇果諫:‘《記》曰:唇亡則齒寒。’”
8.P88“喭”條
9.P94“山徑之蹊間介然用之而成路”條
山徑之蹊間介然絕句。《文選·長笛賦》:“是以間介無蹊,人跡罕到。”五臣注云:“竹間介然幽深無蹊徑,人跡稀至也。”襄九年《左傳》:“介居二大國之間。”杜注:“介,猶間也。間介連文,不得以介下屬。”
今按:杜預的注文只有“介,猶間也”,下面“間介連文,不得以介下屬”是桂馥的話,不能放在引號之內。
10.P19“擭穽”條

今按:“雍氏春令為穽,擭溝瀆之利于民者”,出自《周禮·秋官司寇》。其文云:“雍氏掌溝瀆澮池之禁,凡害于國稼者。春令為穽擭溝瀆之利于民者,秋令塞穽杜擭。”據鄭注、賈疏等可知,“穽”“擭”都是用來捕獲野獸的,“為”是動詞,“穽擭溝瀆”都是“為”的賓語,因此,“穽”后不應加逗號。點校者在“穽”后斷開,似將“擭”當作動詞了。
11.P20“簡”條


書中涉及到《說文》的標點錯誤還有幾處,在此一并說明。
12.P44“求牛”條

13.P71“褚”條
《說文》:“褚,卒也。”卒衣有題識者。
今按:卒衣有題識者。標點有誤。“褚”“ 卒”二字,《說文》均收錄。《說文·衣部》:“褚,卒也。從衣,者聲。一曰制衣。”《說文·衣部》:“卒,隸人給事者衣為卒。卒,衣有題識者。”因此,“衣有題識者”是《說文》對“卒”字的釋語,意思是“卒”是一種上面有標識的衣服。正確的標點是:“卒,衣有題識者。”
14.P84“末減”條
《說文》徐鍇本“瀎”下云:“減瀎,拭滅貌。”鍇《系傳》曰:“《左傳》:‘三數叔魚之惡,不為瀎減。’本此字,今作末,假借。”馥案:“減瀎”當為“泧瀎”,“末減”當為“瀎泧”。《集韻》:“瀎”下云:“泧瀎,拭滅。”《說文》“泧”下云:“瀎,泧也。《玉篇》作‘泧瀎’。讀若茮榝之榝。”《史記·倉公傳》:“望之殺然黃。”徐廣讀“殺”為蘇葛反。馥謂“瀎泧”猶“抹摋”。《漢書·谷永傳》:“末殺災異”是也。
今按:《說文》“泧”下云:“瀎,泧也。《玉篇》作‘泧瀎’。讀若茮榝之榝。”標點有誤。正確的標點是:《說文》“泧”下云:“瀎泧也。《玉篇》作‘泧瀎’。讀若茮榝之榝。”“瀎”和“泧”兩字,《說文》均收錄。《說文》:“瀎,試滅貌。”又“泧,瀎泧也。”
15.P24“爞爞”條
《廣韻》“烔”下云:“熱氣烔烔,出《字林》”。《爾雅》:“爞爞,熏也。”《詩》:“蘊隆爞爞。”徐邈音徒冬反。《韓詩》作“烔烔”。《續漢書·郡國志》:“陳留郡封丘有桐牢亭,或曰古蟲牢。”同“蟲”聲相近,故“烔”或作“爞”。
今按:同“蟲”聲相近,故“烔”或作“爞”。標點有誤。桂馥此處是說《詩經》中之“爞爞”,或作“烔烔”,“烔”從“同”得聲,“爞”從“蟲”得聲,“同”“ 蟲”聲相近,那么“烔” “爞”聲亦相近,所以“爞爞”亦可作“烔烔”。這樣,正確的標點是:“同”“ 蟲”聲相近,故“烔”或作“爞”。點校者沒有弄通此條主旨,憑想當然將“同”理解為一般語詞了。
16.P31“淵回”條
秉心塞淵,其心塞淵,其德不回,求福不回,徐方不回。回猶違也。《左傳》:“君無違德。”《論衡》引作“回德塞淵”,即《左傳》“昭德塞違”也。《會稽典錄》虞翻稱“丁固塞淵好德”。
今按:《左傳》:“君無違德。”《論衡》引作“回德塞淵”,即《左傳》“昭德塞違”也。標點有誤。
《左傳·昭公二十六年》:“齊有彗星,齊侯使禳之。晏子曰:‘無益也,只取誣焉。天道不,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彗也,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徳不回,以受方國。”君無違德,方國將至,何患于彗?《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若德回亂,民將流亡,祝史之為,無能補也。’公說,乃止。”《論衡·變虛篇》引用了此段,其中“君無違德,方國將至,何患于彗”,《論衡》引作“君無回德,方國將至,何患于彗”。楊伯峻《春秋左傳注》于“厥徳不回”注曰:“回,違也。杜注:‘言文王德不違天人,故四方之國歸往之。’”所以,“君無違德”與“君無回德”意義相同。那么,此處的標點應為:《左傳》“君無違德”,《論衡》引作“回德”。“塞淵”即《左傳》“昭德塞違”也。
17.P34“荼”條
出其東門,有女如荼。《箋》云:“荼,茅秀。”

18.P46“五盾”條
《司兵》:“掌五盾,各辨其等,以待軍事。”注云:“五盾,干櫓之屬,其名未盡聞也。”案:《釋名》:“盾,大而平者曰吳魁,為魁帥所持也;隆者曰須盾,須所持也;約脅而鄒者曰陷虜;狹而長者曰步盾,步兵所持,與刀相配者也;狹而短者曰孑盾,車上所持者也。”馥謂五盾之名,此或是與。
今按:“馥謂五盾之名,此或是與”是個問句,“與”是句末疑問語氣詞,后來寫作“歟”。桂馥的意思是典籍中所說的五盾之名,《釋名》所說的這五種可能就是吧? 因此,這句句末要用問號。
標點符號與句讀不同,句讀只要將句子斷開就可以了,但標點符號是輔助文字記錄語言的符號,用來表示語句的停頓、語氣或標示詞語的,具有表達作用。有時候,同樣的文字,標點符號不同,表達的文意就不同。所以,標點符號的使用需要準確,而不僅僅只是斷開而已。本書中類似的應該用問號而用了句號的還有幾處,今一并列之于下:
19.P340“魏王基碑”條
武虛谷見魏王基殘碑。案:《后漢書·鄭康成傳》:“其門人東萊王基。”章懷注云:“基,字伯興,魏鎮南將軍安樂鄉侯。”《魏志》基本傳:“散騎常侍王肅著諸經傳解及論定朝儀,改易鄭玄舊說,而基據持玄義,常與抗衡”云云。初不言為鄭之門人。基卒于景元二年,年七十二,其生當在初平元年。鄭以建安五年卒,基時十一歲,即已列鄭門邪。
今按:“邪”是句末疑問語氣詞,同“耶”。因此,“即已列鄭門邪”后的句號應改為問號。
20.P346小鄭公云峰山尋舊跡摩崖“釋文”條
未幾,遂率僚佐同往游焉。對碣觀文,發聲哽塞,臨碑省字,興言淚下。次至兩處石詩之所,對之號仰,彌深彌慟,哀纏左右,悲感旁人。雖復曾、閔之誠,詎能過也。
今按:“詎”是個表示反問的副詞,“詎能過也”是反問句。因此,此句的句號應改為問號。
21.P409“綠鳩”條
“趙州人家,養一綠鳩,似斑鳩而無繡項,色近鸚鵡不鮮明。戴祚《西征記》云:“祚至雍丘,始見鴿,大小如鳩,色似鸚鵡。”馥案:鴿無綠色,戴所見即綠鳩與。
今按:“戴所見即綠鳩與”中的“與”是句末疑問語氣詞,因此,句號應改為問號。
23.P66“盛”條
文十二年《經》:“盛伯來奔。”莊八年《公羊經》:“夏,師及齊師圍成。”《傳》云:“成者,盛也。盛則何為謂之成?諱滅同姓也。”《字通》作“郕”。《廣韻》:“郕,地名也,在東平。”《玉篇》:“東平亢父縣有郕鄉。”隱五年《經》:“衛師入郕”《谷梁》云:“郕,國也。”杜注:“《左傳》云:‘東平剛父縣西南有郕鄉。’”
今按:此條有兩處標點存在問題。
(1)《字通》作“郕”。桂馥的意思是“郕”是地名,典籍中又寫作“盛”“成”等,而“郕”是通用寫法,故曰:字通作“郕”。因此,“字通”不是書名,不能加書名號。
又,P368“酘酒”條存在同一問題,其中的“字通”,亦非書名,茲列舉如下:
吾鄉造酒者既灑復投以他酒更釀,謂之酘酒。《字林》:“酘,重醞也。”《抱樸子》:“一酘之酒,不可以方九醞之醇。”《字通》作“投”。梁元帝詩:“宣城投酒今行熟。”《晉書·劉弘傳》:“酒室中云齊中酒、聽事酒、猥酒,同用麹米,而優劣三品。投醪當與三軍同其厚薄,自今不得分別。”
(2)杜注:“《左傳》云:‘東平剛父縣西南有郕鄉。’”
按:杜預,字元凱,西晉時人,酷愛《左傳》,自稱有《左傳》癖,所著《春秋經傳集解》是現存最早的完整的《左傳》注本。《左傳·隱公五年》:“衛之亂也,郕人侵衛,故衛師入郕。”杜預注曰:“郕,國也,東平剛父縣西南有郕鄉。”“東平剛父縣西南有郕鄉”是杜預的注文,而如按點校者所加標點,則成了《左傳》的原文而又被杜預引用了。正確的標點是:杜注《左傳》云:“東平剛父縣西南有郕鄉。”
今按:襄二十三年《傳》:“啟,牢成御胠,商子車御。大殿,商子游御。”標點有誤。《左傳·襄二十三年》原文為:“秋,齊侯伐衛。先驅,榖榮御王孫揮,召揚為右;申驅,成秩御莒恒,申鮮虞之傅摯為右。曹開御戎,晏父戎為右。貳廣,上之登御邢公,盧蒲癸為右;啟,牢成御襄罷師,狼蘧疏為右;胠,商子車御侯朝,桓跳為右;大殿,商子游御夏之御寇,崔如為右;燭庸之越駟乘。”杜預對此段中的三個關鍵詞進行了注釋,曰:“左翼曰啟;右翼曰胠;大殿,后軍。”即“啟”是指左翼部隊,“胠”是指右翼部隊,“大殿”是指后軍。桂馥在引用時分別省去了各自御車的對象。正確的標點是:襄二十三年《傳》:“啟,牢成御;胠,商子車御;大殿,商子游御。”
25.P83“詒”條
定元年《谷梁傳》:“夫清者非可詒讬而往也,必親之者也。”范注:“詒讬猶假寄。”馥案:《詩》:“子寧不嗣。”音嗣,《韓詩》作“詒”,云詒,寄也,曾不寄問也。
今按:《詩》:“子寧不嗣。”音嗣,《韓詩》作“詒”,云詒,寄也,曾不寄問也。標點有誤。此處《詩》之引文出自《詩·鄭風·子衿》首章:“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陸德明《經典釋文》:“嗣,如字,《韓詩》作‘詒’。 詒,寄也。曾不寄問也。”正確的標點是:《詩》:“子寧不嗣音?”嗣,《韓詩》作“詒”,云詒,寄也,曾不寄問也。
26.P103“栻”條
《廣雅》:“曲道栻梮也。”梮有天地,所以推陰陽,占吉兇,以楓子棗心木為之。
今按:《廣雅》的體例是用一個常用詞解釋一組同義詞。“曲道”指棋盤,又可以用作占卜的器具。“曲道”亦謂之“梮”。“梮” 亦作“局”。王念孫《廣雅疏證》:“梮,通作局。《說文》:局、簙,所以行棋也。《方言》:‘所以行棋謂之局,或謂之曲道。’”“栻”是古代用來占卜時日的器具,后稱為星盤。因此,此處標點應為:“曲道、栻,梮也。”
27.P106“東閣”條
《隸釋》:“《司空孔扶碑》有東閣祭酒,丞相亦當有之。”《魏書》:“羊肅,武定末,儀同、開府、東閣祭酒。”
今按: “《司空孔扶碑》有東閣祭酒,丞相亦當有之”是桂馥的話,不是《隸釋》之文,不應加引號。
《魏書》:“羊肅,武定末,儀同、開府、東閣祭酒。”此《魏書·羊深傳》文。其文云:“深字文淵,梁州刺史祉第二子也。子肅,武定末,儀同開府東閣祭酒。”所謂“儀同”,是說本官在儀制、儀衛上同于某官,比如說“儀同三司”,所同的官的官階一定高于本官的官階。這里的“儀同開府東閣祭酒”,是說羊肅除本官外,又儀同于開府東閣祭酒。“儀同”后不能加頓號。中華書局版《魏書》、王利器《顏氏家訓·風操》集解引《魏書·羊深傳》“儀同開府東閣祭酒”,其間都沒有頓號。
28.P109“淛”條
浙或作淛,又作制。《莊子·外物篇》:“自制河以東,狾或作猘。”《淮南·氾論訓》:“猘狗之驚,以殺子陽。”
今按:此條是討論文獻用字的,其體例是首先指出某或作某,然后再舉出文獻例證證明之。“自制河以東”是《莊子·外物篇》中的文句,是用來證明“浙或作淛,又作制”的,而“狾或作猘”則是另起一句,提出新的文獻用字現象的,不是《莊子》中的文句,因此,不能放在《莊子》的引文之內。
29.P130“挍”條
《玉篇》:“挍,報也。”此與《顏子》“犯而不挍”合。郭忠恕《佩觽》分“校”、“挍”為二字。
今按:“犯而不挍”出自《論語·泰伯》,其文云:“曾子曰:‘以能問于不能,以多問于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于斯矣。’”“校”,《開成石經》作“挍”。“吾友”,歷來的注釋家都認為是指顏回,如何晏《論語集解》引馬融注曰:“友謂顏淵。”據此,則此處的“顏子”是指顏淵其人,而非書名,不能加書名號。
30.P135“輕脫”條
《三國志》:“多言為將輕脫。”案:僖三十三年《左傳》:“秦師輕而無禮,必敗。輕則寡謀,無禮則脫。入險而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杜注:“脫,易也。”
今按:《三國志》:“多言為將輕脫。”標點有誤。這句話是桂馥的敘述語,不是引用《三國志》的。

31.P157“欻”條
《史記索隱》引孔臧與《孔安國書》:“舊書潛于壁室,歘而復出。”
今按:此處乃《史記·儒林列傳》司馬貞索隱之文。“孔臧與《孔安國書》”中的“與”是動詞,意思是孔臧寫給孔安國的信,因此,“與”應在書名號內。古人給人寫信,一般是“與……書”,如是回信,則是“報……書”或“答……書”,如是替別人寫信,則是“為……與……書”。例如《文選》所收:曹丕《與吳質書》、丘遲《與陳伯之書》、曹植《與吳季重書》,吳季重《答東阿王書》、司馬遷《報任安書》、楊惲《報孫會宗書》,陳琳《為曹洪與魏文帝書》、孫楚《為石仲容與孫皓書》等等。這是慣例。如“與”放在書名號外,則義無所屬;如“與”講成連詞,則“孔臧”和“孔安國書”成了并列結構,不符合文意。
32.P161“廟寢”條
《巧言》之《詩》曰:“奕奕寢廟”。
今按:“奕奕寢廟”是《詩經·小雅·巧言》中的詩句,因此,此條《巧言》之《詩》曰的《詩》的書名號應去掉。
33.P191“賜惡姓”條
江西有哀氏、辜氏,皆賜姓。今哀改為衷,辜猶未改。
信案:永樂間,有哀姓者,上憎其名為豎,改作衷,見《寄園寄所寄》。
今按:“上憎其名為豎,改作衷”,標點有誤。此條是討論的有關惡姓一事,哀姓即屬于惡姓。“哀”和“衷”兩字字形相近,“哀”字中間加上一豎就成為“衷”字。永樂皇帝憎惡哀姓不雅,因而在“哀”字中間加上一豎,改作“衷”。正確的標點是:上憎其名,為豎改作衷。
34.P208“魴”條
35.P397“火把節”條。
六月二十五日夕,家家樹火于門外,謂之火把節,蓋祀鄧賧詔夫婦也。五詔于是日同。為南詔焚死鄧賧詔,妻慈善夫人又畏逼,死。土人哀之,故歲祀至今不絕。
今按:“五詔于是日同。為南詔焚死鄧賧詔,妻慈善夫人又畏逼,死”數句,義不可通。唐代,我國西南少數民族烏蠻有六個部落,總稱“六詔”。六詔即蒙雋詔、越析詔、浪穹詔、鄧賧詔、施浪詔和蒙舍詔。“詔”本是其部落首領的稱謂,六部落有六首領,稱“六詔”,亦稱六部落為“六詔”。唐開元二十六年后,蒙舍詔并吞其他五部,因其在其他五部之南,史稱“南詔”。南詔并吞其他五部時,“五詔于是日同為南詔焚死”,而鄧賧詔之妻慈善夫人又畏懼逼迫,也死了。因此,這幾句標點應該是:五詔于是日同為南詔焚死,鄧賧詔妻慈善夫人又畏逼,死。土人哀之,故歲祀至今不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