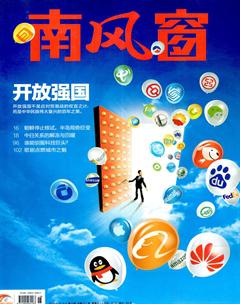穿越繡幕繁弦,與馬可·波羅同行
何子維

八百年前,照卡爾維諾的說法,每當馬可·波羅描繪了一座城市,忽必烈就會自行從腦海出發(fā),把城市一點一點拆開,再將碎片調(diào)換、移動、倒置,以另一種方式重新組合。只有馬可·波羅的報告能讓忽必烈汗穿越注定要坍塌的城墻和塔樓,依稀看到那幸免于白蟻蛀食的精雕細刻的窗格。
八百年后,5月的廣州繁花似錦,全世界藝術(shù)家云集繡幕繁弦,把廣州大劇院拆開、調(diào)換、移動、倒置,以另一種方式重新組合,讓原創(chuàng)歌劇《馬可·波羅》穿越已經(jīng)坍塌的城墻和塔樓,讓我們從舞臺上重溫忽必烈的豪邁與柔情。
站在窗口的男人
相比照搬、引進西方經(jīng)典歌劇,《馬可·波羅》作為廣州大劇院的首部原創(chuàng)歌劇,不僅將一個題材從無到有的在舞臺上呈現(xiàn),更重要的是體現(xiàn)了高水準的創(chuàng)作。
恩約特·施耐德(Enjott Schneider)是德國作曲家協(xié)會會長,1997年就開始與中國音樂家的合作。就像數(shù)千年來的歐洲人對東方土地充滿好奇一樣,無論是香料、絲綢、瓷器、茶葉的物產(chǎn),還是遠方的商人與士兵帶回的消息,都激發(fā)著施耐德對于東方文明的想象。
盡管施耐德認為對中國音樂有一定的認識和理解,但作為一名德國作曲家,要創(chuàng)作一部用中文演唱的歌劇《馬可·波羅》,是一個挑戰(zhàn)。
為了體現(xiàn)歌劇的音樂性作為“現(xiàn)代文化交融的典范”,施耐德翻閱大量資料,運用在電影音樂方面的積累,在獨唱、重唱與合唱的設(shè)計上,加入了諸如二胡、揚琴、笛子、鑼、镲、木魚等中國民樂,把《馬可·波羅》這樣一個歐洲人的故事植入了原滋原味的中國元素。在沒有太多外部輔助下,施耐德獨立完成了創(chuàng)作。
執(zhí)棒管弦樂隊的國際華人指揮大師湯沐海對于歌劇《馬可·波羅》與觀眾的見面充滿了期待,他希望大家可以用耳朵記住,那些波瀾壯闊的史詩格局,尖銳復(fù)雜的矛盾沖突,哀感頑艷的壯士悲歌,還有蕩氣回腸的愛恨情仇。在他看來,只有音樂與戲劇彼此心領(lǐng)神會,才能達到成熟。而這個結(jié)果,只有歌劇辦得到。
《馬可·波羅》被看成是一部歐洲人的寫真,所以來自丹麥的倫敦科文特花園皇家歌劇院前歌劇總監(jiān)擔(dān)任導(dǎo)演的卡斯帕·霍爾騰(Kasper Holten)反復(fù)強調(diào)說,“我們想創(chuàng)造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世界。”為了讓這個世界達到更好的視覺效果,來自英國的“設(shè)計大牛”盧克·霍爾斯(Luke Halls)也加入《馬可·波羅》,在中國首次將D3舞臺控制系統(tǒng)運用到歌劇舞臺,將舞臺設(shè)計成了一個可以旋轉(zhuǎn)的巨大階梯。
執(zhí)棒管弦樂隊的國際華人指揮大師湯沐海。
階梯的意象本身就是一個相當古典的戲劇設(shè)計,也帶著鮮明的時代隱喻——上層社會的權(quán)力斗爭和政治斗爭帶給個體、給人性的變數(shù)。
在馬可·波羅進入中國這個陌生世界的歷程里,階梯等級上下浮動,是對自然主義意義上的古代中國社會的描繪。再現(xiàn)了宋末元初的風(fēng)云際會、興衰更替,以及圍繞東西方貿(mào)易、文化交流而展開的正義與邪惡、文明與野蠻的較量。
看過霍爾滕作品的觀眾會發(fā)現(xiàn),霍爾滕富有激情且高效的領(lǐng)導(dǎo)力,用歌劇向觀眾舉起一面鏡子,讓我們直視著我們——該如何對待情感?該如何處理文化?該如何觀察我們自身?
這樣的直視實在太過嚴肅,無法讓人身心放松。以致有人產(chǎn)生疏離,放棄獨立地理解作品本身,甚至畏懼,把歌劇束之高閣,變成脫離大眾的藝術(shù)。事實上,霍爾滕提醒我們,歌劇不一定具有現(xiàn)實主義,不一定是世界的本來樣子。
歌劇是感覺——霍爾滕的這種感覺,是最不快樂的時刻望向窗外的感覺。路過的人只看到有一個男人正在看向窗外,但無法察覺他內(nèi)心世界的蕪亂。如果我們總是站在現(xiàn)實主義的窗口看歌劇,就不得不面對那些細節(jié),那些苦澀的歷史和頭疼的哲學(xué)。
歌劇是一處自由的空間,一回心魂的酣暢表達,是要以藝術(shù)的真去反抗現(xiàn)實的假,以劇場中的可能去解救現(xiàn)實中的不可能,以這舞臺或銀幕上的實現(xiàn)去探問那布滿于四周的不現(xiàn)實。
當舞臺上的人物說:我愛你,我恨你,恐怕我要死了。我們可以按下暫停鍵盤,只消花五分鐘,去探索這愛的、恨的和悲涼的感覺是什么,就已經(jīng)足夠了。
是起點,也是啟蒙
《馬可·波羅游記》在中國稱得上是有口皆碑的作品,如何把這個過于豐饒的文本改編成歌劇,廣州大劇院花了三年的功夫。
一方面,是要把一個古代冒險家的傳奇,與“一帶一路”和“全球化”的時代背景契合起來。另一方面,則要兼顧中國觀眾對于歌劇這個藝術(shù)形式的接受度。這不僅需要人力和財力,還需要勇氣,需要打破原來的認知,需要去建立一個平臺。
廣州市文廣新局局長陸志強表示,廣州在戲劇文化建設(shè)上有一個大目標和一個小目標。小目標就是希望通過三五年氛圍的營造,打造出“戲在廣州”的城市氛圍,大目標是將廣州打造為“戲劇之都”。
無論是打造“戲在廣州”,還是打造“戲劇之都”,劇院是基礎(chǔ),劇目是靈魂。廣州大劇院除了建筑外觀可以作為廣州城市的象征之外,更需要打造出一批叫得響、演得久的劇目。
這些年來,廣州大劇院聯(lián)手羅馬歌劇院、紐約大都會歌劇院、英國科文特花園皇家歌劇院等世界一流劇院和一線歌唱家,引進了《媽媽咪呀》《貓》《音樂之聲》《劇院魅影》《羅密歐與朱麗葉》等多部世界經(jīng)典音樂劇。制作推出了《圖蘭朵》《阿依達》《茶花女》《卡門》等多部“廣大版”經(jīng)典歌劇。但這些畢竟是引進,是改編,不是原創(chuàng)。
《馬可·波羅》作為廣州大劇院的第一部原創(chuàng)歌劇,是起點,也是啟蒙。歌劇自意大利誕生四百年后,才在20世紀20年代和中國音樂發(fā)生交接,那時候中國歌劇不過是兒童歌舞劇。從好奇,模仿,引進,改編,到創(chuàng)作,這個過程就是啟蒙。就像康德認為的啟蒙就是從一個不成熟的狀態(tài)走出來,這個出走是一個不間斷的過程,絕對不是一次性的動作。

《馬可·波羅》的排練。
走出來,不止是從我們認知的世界里走出來,還要在我們活動的半徑里走出來。“當我們邀請世界各地藝術(shù)家時,他們基本上都對《馬可·波羅》這個題材很感興趣,”廣州大劇院總經(jīng)理助理、原創(chuàng)歌劇《馬可·波羅》執(zhí)行制作人陳睿說,“他們很好奇,愿意嘗試。所以基本上第一時間就答應(yīng)了。”
廣州大劇院作為絲綢之路國際劇院聯(lián)盟成員之一。以《馬可·波羅》為媒介,通過“請進來,走出去”的良性互動,發(fā)揮了其文化橋梁的作用。就像當年馬可波羅來到中國,表達他對中國文化的景仰。
現(xiàn)在,廣州大劇院把歌劇這種形式作為一個載體,敞開自己的胸懷,吸納全世界的藝術(shù)家們來到廣州,在當代的中國的文化自信和開放精神的氛圍里,共同創(chuàng)作一個出自中國而又屬于世界的藝術(shù)作品。它的意義,就不只是一個跨時空的一個文化啟蒙了。
歌劇的最好的時代
歌劇在中國,確實碰到了最好的時代。
現(xiàn)在,西方許多知名的劇場和歌劇院陷入了極度缺錢的困境,就像西方的文化和制度正在受到的挑戰(zhàn)一樣,而中國則以開放式姿態(tài)正在構(gòu)建制度和文化的自信,并且保持謙遜。
能夠參與《馬可·波羅》這部歌劇的創(chuàng)作過程,陳睿感到很幸運,也很感激。她認為積集起這么多一流藝術(shù)家來創(chuàng)作《馬可·波羅》,實質(zhì)上是為廣州大劇院上了一堂課,一方面是可以感知世界一流藝術(shù)創(chuàng)作的理念,另一方面則可以學(xué)習(xí)管理世界一流藝術(shù)作品的專業(yè)經(jīng)驗。
《馬可·波羅》的排練期間。演員們的排練基本上是“白+黑”,白天不停歇,晚上還要加班。即使是明星級主創(chuàng),只要是國外演員,要用中文表演,也得上中文課。
所謂天才,其實是意志的結(jié)果。所謂藝術(shù)理想和激情,其實是人生歷練和視野,在舞臺上通過這樣一個特殊的自由的公共空間的反射。
“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馬可·波羅》中文天祥的扮演者,青年藝術(shù)家王云鵬始終在尋找一種方式,以表達文天祥的民族氣節(jié)和舍身取義的生死觀。王云鵬認為,這樣正氣凜然的人生觀對于我們現(xiàn)代人來說,是很重要的,也是缺少的。
優(yōu)渥的生活一直在偷偷吞噬我們的精神。詩人北島就毫不留情地批判說,我們正在退人人類文明的最后防線,處于一個毫無精神向度的時代,一個喪失文化價值與理想的時代,一個充斥語言垃圾的時代。在所謂全球化的網(wǎng)絡(luò)時代,雅和俗的結(jié)合構(gòu)成最大公約數(shù),簡化了人類藝術(shù)的表現(xiàn)力。
在與物質(zhì)的對抗中,歌劇的觀念是很稀缺且珍貴的。這是在采訪《馬可·波羅》劇組的時候,給記者留下的一個深刻印象。
歌劇不止于一種藝術(shù)形式,更是一種觀念。無論創(chuàng)作者,還是觀眾,在觸動歌劇的剎那間,世界變得很小,過去近若咫尺,我們突然發(fā)現(xiàn),千百年來,有些靈魂從未離開過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