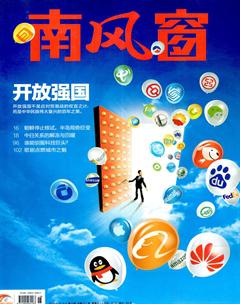要有一些博弈論的眼光
李哲夫

近日,關聯合英法以化武事件為借口,對敘利亞實施了導彈轟擊。對此,有人擔心美俄之間會直接交手,甚至由此而引發第三次世界大戰也說不定。這可能是有些過慮了。
事實上,雙方并沒有突破托馬斯·謝林所說的戰略博弈的畛域。互相雖然都似乎志在必得,但也都有對事態發展彼此心照不宣的平衡點。一方揚言要對使用化武者實行導彈打擊,一方則強硬表示要攔截來襲的導彈,甚至不排除打擊發射導彈的平臺。看起來是夠劍拔弩張的,但實際上,這種放狠話的相互威脅,不過是沖突博弈的一種慣用之術而已。
當然,話說出了是要兌現的,美英法果然發動了打擊,而且發射的導彈數量還不少,但在選擇打擊目標上卻很有分寸,完全避開了俄軍的基地和攔截導彈陣地,而且打擊過后又馬上表示,暫時沒有再次打擊的計劃。對此,俄雖然被打了臉,但也沒有更大的損失,不至于不能忍下這口氣。況且從長計宜,俄所支持的敘政府軍方面畢竟已經完全掌控了戰場上的主動權,而美英法的一兩次導彈打擊,并不會挽救反對派的頹勢。因而,這—次事件,只不過是美俄在敘戰略較力長途跋涉的一個階段罷了,是不大可能出現事態失控的局面的。美俄在敘利亞博弈的路還長,現在還遠不是說誰勝誰敗、誰贏誰輸的時候。
由此,使我想到了托馬斯·謝林在上個世紀60年代所撰寫的《沖突的戰略》一書,在這部出色的闡述博弈理論的著作中,作者用深入淺出的語言,讓人們在興致盎然的閱讀中,受到智慧的啟迪。而謝林也因對博弈論的貢獻,使他在近半個世紀后即2005年,榮獲了諾貝爾經濟學獎。
沖突是國際領域中最為常見的現象之一,而如何認識和對待沖突,就成為各國政治家、外交家和商貿界不能不經常面對的問題。有意思的是,在國際關系中,發生“雙方利益完全對立的完全沖突狀態是非常罕見的”,而絕大多數沖突,雙方之間除了有沖突利益之外往往還有共同利益存在,因而國際沖突基本上不應該是“零和博弈”而應該是“非零和博弈”。
這也就意味著,博弈一方的所失并不一定是另一方的所得,而尋求雙贏的結局則往往更符合雙方的共同利益。因而,對于國際領域中這一司空見慣的沖突現象,我們首先需要的是要有一個準確的清醒的判斷,然后冷靜地理}生地智慧地對待之。這樣才有可能棋高一著,占據主動,在與對方討價還價中找到雙方利益的最佳平衡點,從而爭取握手言和、互惠互利的結果,而不至于彼此受損、兩敗俱傷。當前,對于中美之間的貿易沖突,我們似也應當如是對待之。
在沖突的博弈中少不了威懾手段的實施,對此,作者也有深入的研究。“威懾理論是一門關于如何巧妙地運用智慧,避免使用現實武力的理論。”這在軍事方面最為典型:“威懾涉及武力的潛在使用,而非實際使用;威懾是為了警告并說服潛在敵人,只有避免某些舉動才能維護其自身利益。”這也完全可以擴展到經貿領域。而一旦動用了現實武力或現實經貿報復手段,那就意味著威懾的失敗。
如果雙方之間的關系是完全的共同利益關系,或者是完全的沖突關系,那么威懾就沒有意義。完全的共同利益自然不需要發出威懾,而完全的沖突,則只有動用實際的武力或實際的打擊手段才有作用。
要最大限度地發揮威懾的作用,有時一方會使用破釜沉舟、孤注一擲的策略,從而表明志在必得的決心和魚死網破的勇氣,以迫使對手不得不做出讓步,從而取得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效果。然而這也是風險極大的一種博弈,一旦未能嚇住對手,下文則要么屈服,要么被迫進行沒有勝算的交手,結果都會是更大的損失。威懾行動實行后,雙方往往會堅持到最后一刻,這就有如兩輛相對狂奔的汽車,誰先露怯,不敢冒相撞的風險而踩了剎車,誰就不得不在其后的談判中向對方做出較大的讓步'當然這種游戲也有極大的相撞風險。
今日世界上,國際領域里的博弈大戰層出不窮,在觀察這一萬花筒式的國際現象時,有一些博弈論的眼光當不無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