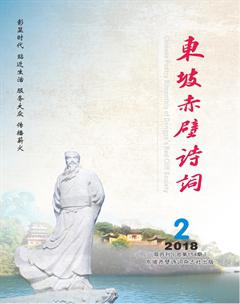我讀詩亦如詩讀我
王樹良
讀詩,既是我“認識”詩的過程,也是詩“認識”我的過程。詩人讀詩如同飲水,如同呼吸新鮮空氣,如同吸收各種營養成分。亦如情侶之戀,你愛她,她卻不一定愛你,那是一廂情愿的單相思。所以,首先要專情于詩,愛讀詩,多讀詩。其次,要深讀詩,讀懂詩,進而精讀名人名作。閱讀今古詩詞評論和理論文章,品其風骨。然后與詩詞才有互動,她才欽佩和專情于你。
我們所經過的幾個讀詩階段,不是一蹴而就,而是循序漸進。詩有三境,學詩亦有三境。我們讀詩、做詩亦有三境。初為普讀,再而深讀,進而精讀。
第一階段是普讀。這個階段,只是觸及到詩的物象,知其美而不知其所以美。在這一過程中,首先要了解詩詞格律,進而掌握詩詞格律,使你讀詩更體會其音律美、節奏美,興趣更濃。這只是相當于初小的加減乘除口訣,能夠掌握格律才算步入詩詞門檻。這一時期,特別喜歡寫詩,天天躍躍欲試,儼然覺得才思敏捷。這便是詩境中所言的“其初不識好惡,連篇累牘,肆筆而成”的初級階段。這個時候自鳴得意,信心十足,誰要改了兩個字,就特別反感,甚至于奔走相告,自己的詩,簡直是神圣不可侵犯。不少人大都有這個經歷,這個階段如不作心理調整,不閉關修煉、充電,那么,就無法突破,無法進入第二境,自始至終會在那兒孤芳自賞。學詩進入初級階段后,如同修禪,有頓悟,漸悟,徹悟,達到何種境界是小乘之法、或是大乘之法,全在個人修為。這一階段的普讀,作為年輕時期,應多記多背古人詩詞。這便是古人所說的“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寫詩也會吟”。從而為自己的創作打下堅實的基礎。在閱讀名家作品和自己創作的作品時,要有謙虛嚴謹的學習態度。要做到這一點很難。在如今這個網絡發達的時代,詩人們在一個個大拇哥的贊頌下成長,哪還有人說真話。當然,也不乏善意的贊美和交流。如何正確對待這種廉價的捧殺,也是詩詞愛好者的必過之關。
詩詞是一門綜合性學科。知識面越寬廣,人生閱歷愈豐富,才情積累愈豐厚,個人品第學養愈高,入詩便愈快。嚴滄浪云:“大凡人無才則心思不出,所欲言而不達;無膽則筆墨畏縮,無見識則不能取舍,無力而不能自成一家。功名之士,決不能為泉石淡泊之音;輕浮之子,必不能登大雅之響。一首詩景浮于眼前,情激于心中。有情無景,則詩境而不出;有景無情,則才思而不出。”我們需要大量閱讀古今名作,在閱讀作品和自己創作時,要有嚴謹的學風和謙虛的學習態度。能與嚴師益友交流,是非常重要的途徑。
讀詩第二階段是深讀階段。也應是創作詩進入第二階段。我們寫詩,如不繼續修煉,可能永遠停滯在第一階段的詩境,仍是不計美丑,肆筆而成,一天可寫五六首,甚至更多。進入深讀的第二階段,要研讀古今詩論文章。這便是第二境所說的“漸知羞愧,始生畏縮,成之極難”階段。你知道詩詞結構的嚴謹,你知道意境的提煉之難,你知道煉句煉意煉眼之難,你學的越多,你的筆下已不是無知無畏了,是被有法的條條框框限制了,所以,下筆必畏縮了。這時,你珍愛自己的作品了,知道反復斟酌了。這說明你進入第二境了。
第二階段讀詩,已進入深讀了。我們學習和研究對各時期、名家、地域的詩風有深入的了解,對你所喜歡的詩風,有較深入的了解,如同書法,你是喜歡二王的,或是顏柳的,還是蘇黃米蔡的,入得師法,練習更得法。這時讀詩,才能細心體會各個時期、不同地域、不同詩人的不同詩風。由不知其所以源,到略知其源。為什么?因為詩有詞理意興。南朝人尚詞而病于理,宋人尚理而病于意興,唐人尚意興而理在其中。漢魏之詩,詞理意興無跡可求。古人寫詩,尤其是晉唐詩人,寫詩以景出,所言甚小,所指甚大,以引喻、博喻而言志言情。有位詩友說:“唐詩我讀起來,也不過如此嘛!”其實,我也曾有過這樣的想法。因為我還沒有深入了解唐詩。這很正常。隨著學識的增長,見識的提高,才可窺測其深邃的內涵。既觀其貌,又視其神,詩才會日益親近。
嚴羽《詩辯》中云:“夫學詩者以識為主,入門須正,立志須高,以漢魏晉盛唐為師,不作開元天寶以下人物。若自退屈,即有下劣詩魔入其肺腑之間,由立志之不高也。行有未至,可加工力,路途一差,愈鶩愈遠,由入門之不正也。故曰,學其上,僅得其中;學其中,斯為下矣。”我們讀別人書法作品,落眼便知有無師承。也可從你的書品詩品中知其品第,知其秉性和情懷。初學寫詩填詞,也可知師法如何。一首詩的起承轉合,如同人的氣脈血液,不通暢則氣血虧損,陰陽不調,音啞則元氣虧損。詩者起承轉合,乃詩人一生的必修課。詩的高妙,在于將世事萬物,玩味于斑斕的文采和精妙的意境之中。言他人之所未言,是指立意的高深不同,絕非是詞語的趨新斗尖。詩有別裁,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若非多讀書、多窮理,則不能極致。所謂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詩者,吟詠情性也。盛唐諸人,唯在興趣,羚羊掛角,無跡可尋,故其妙處,透徹玲瓏。那么,詞雖大開大合,是有其開合原理的。這個靠自悟,只要深讀古人之詞,才會領略其前后左右顧盼之妙。掌握了詩詞結構的嚴密,雖難求警語,尚可示人。古人云,起句響難得,結句響,更難得。如杜詩,起句好者有“群山萬壑赴荊門”,結句好者如“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我個人認為,結句也有不好的,如杜甫的《登高》:“風急天高猿嘯哀,渚青沙白鳥飛回。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臺。艱難苦恨繁霜鬢,潦倒新停濁酒杯。”起句首聯大有空谷傳響、哀轉久絕之音。中二聯有吞吐于江河之氣概,寓今古之圣理,發天地之幽情。以頸聯直貶廟堂之多病,把一切的景語與情語烘托到了極致,真乃曠代之佳作。但其不足之處,首先站得甚高,而最后轉結,僅為自己的艱難苦恨、一杯濁酒使意境陡轉成狹隘和萎縮。這么大的情懷,一下跌入了深谷。假如把“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這種意境,作為結語,那就大不一樣了。那就更展現了作者的博大胸襟,更展現事物必然的規律。但此詩,仍不失為杜甫的曠世絕作(這只是我個人見解而已)。學詩,宜知其古而不泥古,取其精華,方能進入佳境。李商隱學杜之精華,絕妙之警廣為后世流傳。黃山谷學杜多為趨新斗尖,雕詞琢句,已失去三百篇至盛唐以來詩歌的原旨。詩自宋后受理學影響,更顛覆了盛唐以前的詩風。寓理沒有什么不好,但詩到以理言詩寄托表面化,則詩之意興全無。如書法、繪畫,畫得滿滿的,或筆劃毫無生氣,沒留取遐想的空白和生動的氣息,那就沒有咀嚼的回味了。
藝術的境界在于品味,而不是刻意的雕琢和粉飾。做到雕而不雕,天然去雕飾。過于的雕飾失其自然,如刀削斧砍,有貼膏藥、打補丁之嫌。一個有內在氣質的對象,她不需濃妝艷抹。而素面朝天,讓人有久絕風塵的天姿之美。這便是詩的高貴之處。言雖淺,意其厚,感事致深,景雖淡而情愈濃,使自然與詩境達到天人合一。正如王國維所說的“一切景語皆為情語”。其實,這個說起來容易,做起來卻不易。
讀詩的第三階段,便是精讀階段。在深讀的基礎上,對名家名作進行反復精讀,讀其手法,讀其結構,體會深意。不同層次的閱讀,會有不同層次的見解和心靈的碰撞。詩者乃譎諫也,因為詩不可露,露則失風流。詩既言情,寄托心志,不可言盡。詩不在雕琢,而是把玩于塵世萬物,心在物外,身置事中。非是訴說,直言反難透徹。而以景言情,則留出一個大大的空白。這便是古代藝術家的高明。村婦罵人,會罵的罵豬罵狗,不會罵的直接罵人。這會得出兩種結論。前者罵留給了別人情面,人家生氣,但沒理由反駁,為以后相見,還留有余地。后者之罵無任何退步,反目成仇。究竟哪個高明?這便是詩品中的含蓄、委曲的妙質。溫庭筠《憶江南》詞:“梳洗罷,獨倚望江樓。過盡千帆皆不是,含暉脈脈水悠悠。腸斷白蘋洲。”古今詩評,多從藝術角度和閨婦思夫的角度去評論,其實,溫庭筠此詞意在言外,借閨婦的幽怨之情,表達了作者在政治上的企盼與失望交集的內心展現。
姜白石云:“作詩求與古人合,不如求與古人異;求與古人異,不如不求與古人合而不能不合;不求與古人異而不能不異。”
寫詩求與古人合,乃形制也,詩法也。不如求與古人異者乃其神也,韻致也。而不如不求與古人合,又不能不合者,乃形制物象之變異也。而不求與古人異而不能不異者,乃神韻之變異也。故其形神皆有合而不合,異而非異也。其形與古人合,則神與古人異也。嚴羽論詩云:“盛唐人作詩有似粗而非粗處。”滄浪之所言,粗之反義乃精,拙之反面乃工,必體認確切,以拙之為工,不必斤斤然于表面,而底里自然高妙;遇到刻劃之題,利在工巧,利在精細;若作平淡之韻,拙則利于古樸,粗則合于自然。這與創作題材和個人取向有直接關系。其大題必小作,利于工巧。其小題而大作,利于粗拙古樸。詩外有詩,方為佳構。古人做詩,不是一個層面,而是幾個層面。你認識她有多高,她才知道你多高。你讀《西游記》讀故事,是一個層次,至于其更深層次,很多學者研究得出了不同結論。例如讀崔護的《題都城南莊》,詩云:“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映紅。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不同層次的讀者,會有不同的解讀。不少人認為,這是一首懷戀女子的戀詩。首先,這首詩手法獨到,采用了省略法、合述和分述手法。一個“去年”,省去了今年,去年情景是人面桃花同彩,相互映襯,而今年人面是人面,桃花是桃花,卻各不相同。這便使詩境一揚一抑,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但是崔詩的根本立意,在于以此寄托他落第心情的變化。去年考后,乘興游南莊,正是春風得意,桃花盛開,流露出勢在必中的信心,所以是人面桃花相映紅,該是多么愜意;而重來尋舊,桃花依然在春風中含笑綻放,此時此景,其人面往哪兒擱啊,則似乎桃花在那兒對人面有所羞辱和譏笑。此乃典型的情景交融,意在詩外。寫詩,需有詩的語言。詩詞作為藝術品,既有藝術的水準,也是作為詩歌有其大眾化的教化作用。唐人寫詩,都是既好懂又便于吟誦,既典雅又富有深刻的思想內容。
詩如一切之藝術,得其物象為下,得其個性為中,得其神韻方為上妙。詩如文人之衣冠、風度,讀詩便知其舉手投足,知其風雅。亦如同咀嚼食物,初聞有香,細嚼知味,咽之回味。與詩相交,感化于人,你讀懂詩,詩也讀懂你而依戀于你,與你結下不解之緣,樂伴終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