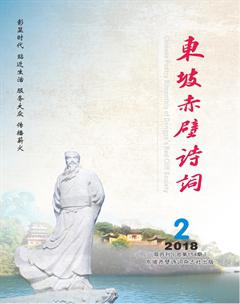反常合道 莫玩花招
近年,在孟浩然田園詩詞創作中,通過語言特殊組合,實現語言張力,來產生內涵與外延的膨脹力,以增加詩詞意境的寬度與深度。其手法特征為,顛覆傳統,突破規范,掙脫慣常,超越常識,錯位嫁接,歸納為“反常出新”。然仙道與魔道僅一步之隔。因此,要嚴格掌控適宜度及其應用范圍,防止滑向岐途,力避以“獵奇”和僅“圖新鮮”為目的,以致對沖抵銷“反常出新”的藝術魅力與成果。
一、反常出新,須合乎法度
董培倫說,詩詞“必須繼承傳統才能創新”。蘇東坡亦言:“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二人所言即是,在傳統規范和規則的基礎上,方可創新,才能“出新意”。所謂“反常”,主要有三:一反常識之常。如丁芒《梨園飲綠》:“三巡茶罷澆愁盡,滿腹豪情載綠歸。”此“綠”字是用來借代“新綠茶葉及其韻味”。二反語意之常。如孫宇璋《移民新村》:“機耕機播機收割,摟住春風贊脫貧。”用“春風”比喻黨的惠民政策、農民脫貧致富的美好光景,這樣就可“摟”抱了。又如徐光泉《田園雜興》五:“村姑緊握分秧器,細為春田織綠衣。”“綠衣”用來比喻機插青秧,編織而成。三反語序之常。如李明德《南鄉子·秋游天鵝洲》:“如織銀魚碧水游”,乃“游碧水”之倒裝。將謂語“游”字倒置于賓語“碧水”之后。如吳華山《家鄉水》:“沒孔風吹笛,無弦溪弄琴。”應為“風吹沒孔笛,溪弄無弦琴。”將補語移置于主、謂、賓語之前。
二、出人意料,須合乎情理
蘇東坡又言:“詩以奇趣為宗,反常合道為趣。”“為著避免平凡,盡量在貌似不倫不類的事物中,找出相關特征,從而把相隔最遠的東西出人意料地組合一起。”(黑格爾語)因而我們要注重字詞語言上的翻陳出新,同時要追求立意構思的推陳創新。所謂“合乎情理”,一般有五。
一合景物環境之情理。如李明波《雁蕩山》:“云浮雁蕩掩仙蹤,小徑悠悠步玉峰。酒酌桃紅詩染綠,超然物外沐東風。”其“酒紅詩綠”似覺異乎尋常。但與作者所處山中環境聯系起來,便豁然貫通,在山上桃花樹下含觴賦詩,所酌之酒映桃紅之影像,所詠之詩皆青山如黛、蒼翠欲滴之景象。這樣,就深化并拓展了詩意。
二合地理物理之情理。如樂本金《湖上漁歌》:“漁歌唱出滿湖霞。”試想:漁民起早下湖,邊劃船布網,邊高唱低吟漁歌,迎來旭日,朝霞滿天,輝映湖面,水天一色,這不是唱出“滿湖霞”嗎?又如李素芹《荷塘》:“香傳笑語聲。”“香”與“聲”本不相涉,“香”由氣味傳播,嗅覺器官感知;“聲”由聲波傳播,聽覺器官感知。但兩者在同一地點與范圍之內,同時傳播,其“聲”似乎追“香”而至,故人錯覺“香傳笑語聲”了。這是通感手法。
三合人物行為心理之情理。如李輝耀《山間老農》頷聯:“手握銀鋤頭點地,肩扛日月汗生煙。”“頭點地”,乃“臉朝黃土背朝天”之謂;“肩挑日月”,乃“早挑日頭晚挑月”之謂;“汗生煙”,乃“大汗淋漓冒熱氣”之謂。以此描寫老農辛勤勞累之情形,反映當代農村勞力以老年人為主之現狀。又如劉貴連《春插》:“姑娘羞說后生帥,直贊農機會插秧。”姑娘暗慕插秧機手,由于含羞不便表白,卻連連夸贊插秧機,以博后生答訕交談。刻畫姑娘的表情與心理活動細膩入微,尤為傳神。
四合事物進程、發展規律之情理。如郭省非《改革開放三十年》:“拔盡鳥云散霧霾,愁花謝盡樂花開。精挑幾粒明天籽,種入春風長未來。”詩中“明天”、“春風”“未來”及“種入”,俱為借代、象征。其意實為,趁著政策開放非凡成就的大好形勢,向小康社會宏偉目標邁進。這樣“精挑”之“籽”,就可“種”了,發育成長為“人民幸福,國家富強”的參天大樹。
五合寫作技巧之情理。無數實踐證明,充分運用比喻、夸張、借代、象征、通感等多種手法,可以不需破壞語法規范,不用組織語言異質沖撞,仍然能夠反常出新。如星漢《回鄉偶書二》:“春風吹拂滿書包,如餅朝陽掛柳條。布谷催耕聲太晚,麥苗已到小兒腰。”此詩乃比興手法,白描取象。作者滿懷回鄉喜悅,出門晨眺,耳目所及,隨景賦形,情逐景生,筆筆生機,不假雕飾,語言清新,沁人肺腑,耐人品味。
三、重組架構,須適于創新
趙翼曾言:“詩文隨世運,無日不趨新。”說明創新是詩詞的生命。如若反常,必須創新;不出新意,切莫反常。任何一種反常,必須要有重建的創新價值,務必建立和營造語言新秩序,務必“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否則,就是“獵奇”和僅“圖新鮮”而玩弄語言花招。因此,反常出新要求切實做到“三有”:即有理、有利、有節。有理,應崇本抑末。反常出新,要處理好“反常”與“合道”的關系,解決好“不可能”與“合情合理”的問題,講究大道理,生發大情趣。不搞邪說歪理,不搞低級趣味。如沙永松《秋韻》:“即今挪用中秋月,蓋下豐收大印章。”時至中秋,即使收成未成定局,也是豐收在望,此乃秋韻之真諦。假如只言“挪用中秋月,蓋上大印章”。尚不能透示秋韻本質,只有加上“豐收”二字,才能充分展示其精髓,且妙趣橫生,韻味尤足。
有利,必至矣盡矣。反常出新,就是要通過語言特殊組合,使之深化內涵,拓展外延,生發新意象,營造新意境。如果只是現存詞語的更換與替代,那就沒有什么意義了。因為任何替代詞語,都沒有其本身準確深刻,除非一物二名或多名。詞語通常順序顛倒使用,那就得區別對待了。能夠顛倒者,用得好,可以增加新鮮感;不宜顛倒者,萬萬不可。至于生造詞語、不當縮語,絕對不行。如宋自重《參觀英山新農村建設》:“萬壑千溪起畫欄,茶園深處柳如煙。誰將天上神仙墅,撒向青山綠水間?”此詩用虛實相生、動靜互彰之法,一個虛擬設問,就反常出了新意,本是敘述句,一下變成了描寫句。既出詞語之新,更出立意構思之新。
有節,須適可而止。反常出新,需要及時抓住好機遇,嚴格掌控適宜度,不可“狂轟濫炸”而“過之成災”。一者“反常”就是破壞正常語法規范,打亂正常思維與語言習慣。“出新”的重組再建,往往容易產生一些怪僻晦澀的詩句。二者反常容易,而“出新意于法度之中”的合道很難。三者反常出新的機遇甚少,成功的詩例猶如鳳毛麟角。四者反常過多過濫,使人極易厭煩。若鹽之于菜肴,無則清淡寡味,多則咸重難咽。現有兩例可證:其一,《中華詩詞年鑒》2004年卷中一詩:“全會三中拂煦風,轉移重點啟新程。敬尊知識禮賢士,平改錯冤伸正公。審判江林良息憤,健嚴規法恣消蹤。吸資開改揚中粹,紀末雙番超速成。”詩中“全會三中”“敬尊”“正公”“規法”,顛倒了不宜顛倒的詞語順序;“平改”“紀末”乃“平反改正”“本世紀末”之生硬的不當縮語,“錯冤”“健嚴”“規法”“開改”,乃“冤假錯案”“嚴格健全”“改革開放”之不宜顛倒的不當縮語。“良息憤”“恣消蹤”乃詞語搭配不當且有生造之嫌。“中粹”為何意?猜想可能是中國國粹吧。其二是描寫農村土地整治的詩:“交通網絡到田邊,硬化農商運轉權。歸并村居新生活,混凝幸福砌家園。”詩中“網絡”尚可作名詞動化而用,“硬化”“歸并”“混凝”“砌”,乃替代更換“強化”“集中”“創造”“建設”。至于“農商運轉權”為何意,猜想可能是“農商貿易交流權利”吧。如此令人生厭的句句反常,究竟出了多少新意?是讓讀者欣賞藝術呢,還是苦猜啞謎呢?
袁枚《隨園詩話》論詩云:“能翻陳出新最妙。”此說與當代詩壇倡導的“繼承創新”甚合。所以,在孟浩然田園詩詞創作中,既要追求語言上的出新,即語言新鮮(包括吸收現代新鮮生動的口語),又要追求立意構思上的創新,即立意新高,構思新巧,內容新穎,意象新奇,意境新趣,詩句新雅,風格新異。這樣,就需要我們勇于探索,善于嘗試。鍥而不舍,勇往直前,必將闖出一條反常出新的陽光大道。
(陳惟林,系第二屆孟浩然田園詩詞大賽創作獎獲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