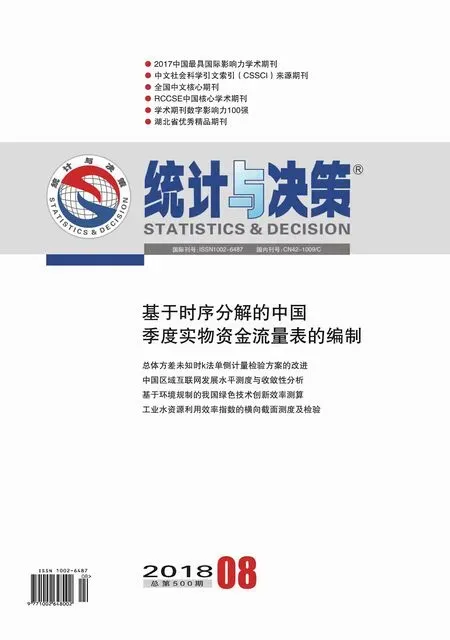產業集聚與區域創新能力耦合協調發展研究
李國鳳
(河南大學 商學院,河南 開封 475001)
0 引言
近三十年來,產業集聚優勢已經超越低成本優勢而成為吸引外資的主導力量。高妍伶俐(2014)[1]認為企業為了尋求更多發展機會和擴大發展空間,通過深化區域合作來提升區域創新能力,這己經成為各國融入全球價值鏈的主流趨勢之一。郭明翰(2014)[2]認為在這樣的背景下,對產業區、產業集聚、區域創新體系等方面的研究大量出現,這些研究從不同角度強調了在復雜的經濟環境中,產業集聚發展與區域創新能力構建之間不可分割的關系:產業集聚對促進區域創新能力提升具有重要意義,而區域創新能力的提升又保證了產業結構優化,并且為產業集聚驅動力轉型奠定了基礎。縱觀國內外相關研究[3-8],無論從理論或是實踐層面上探討產業集聚和區域創新能力之間的關系都具有很重要的意義。本文從探索兩者發展基本規律入手,探明產業集聚與區域創新能力的內在聯系,分析兩者之間的互動關系,從而探討產業集聚和區域創新能力協調發展的可行性路徑。
1 產業集聚與區域創新能力的耦合協調模型
1.1 主成分分析法
本文對產業集聚與區域創新能力互動績效評價采用主成分分析與協調發展度模型相結合的綜合評價方法,具體步驟如下。
(1)對指標數據進行標準化處理
根據數據 Xij=x11,x12,....,xnp(i=1,2,...,n;j=1,2,...,p):


據此,可得出產業集聚與區域創新能力子系統的標準化數據。
(2)計算相關系數矩陣
通過上個過程得到的標準化數據,得出產業集聚和區域創新能力兩子系統的相關系數矩陣R。
設R的特征根 λi≥λi+1(i=1,2,...,p),特征向量 ?j=(e1i,e2i,...,epi)1,計算第k個主成分的方差貢獻率:

求出每個指標權重:

根據方差貢獻率αk計算每個指標的權重。xi為旋轉后載荷矩陣中每個指標的得分情況。權重δi為正,說明該指標與系統綜合發展水平成正相關關系,為負則情況相反。
1.2 耦合協調模型
為準確得出產業集聚與區域創新能力兩個子系統的協調發展程度,進一步評價兩者的協調發展,必須在計算出產業集聚與區域創新能力兩系統綜合發展水平的基礎上,構建產業集聚與區域創新能力的耦合協調模型。其計算步驟如下:
(1)極差法無量綱化
為了消除數據的數量級不同以及量綱不同造成的影響,有必要對原始數據進行極差法標準化處理。
當指標xi與綜合發展水平為正相關時:

當指標xi與綜合發展水平為負相關時,指標xi的正負向關系由主成分分析法得出的各個指標權重判別。
(2)綜合評價值的計算

式(4)、式(5)分別代表產業集聚和區域創新能力綜合發展水平的評價函數,ai和bi表示權重(通過主成分分析得出)xi和yi分別為極差法求得的產業集聚和區域創新能力子系統內指標的無量綱化值。
(3)耦合度的計算
對產業集聚和區域創新能力這兩個子系統,可以根據式(6)構建耦合度函數:

其中,C∈[0,1]。當C=1時,兩系統高度耦合;當C=0時,兩系統基本不耦合。
(4)耦合協調度的計算
經過耦合度的計算,通過式(7)和式(8)構建耦合協調度函數,以便衡量兩個系統之間的協調狀態。

其中,D為兩系統的耦合協調度,α和β代表著產業集聚和區域創新能力的重要性,兩者相加等于1。
2 產業集聚和區域創新能力的互動績效評價體系構建
2.1 產業集聚子系統評價指標體系的構建
本文從集聚整體績效的角度來構建產業集聚綜合評價指標,指標體系分為兩級,一級指標包括六個方面:集聚程度、競爭合作、創新能力、集聚效益、開放程度和集聚保障。在每個二級指標下均有若干二級評價指標相對應,如表1所示。
在指標體系的構建中,確定所選取的各個指標在總得分中應占多大的權重,是一個比較困難的問題。本文采取的是專家賦權法,給出對各個指標的重要性排序和評價數據,然后應用主成分分析法對評價指標進行處理,從而有效地確定各個指標的權重。
2.2 區域創新能力子系統評價指標體系的構建
本文在區域創新能力評價指標體系的設計時,在文獻綜述與調研的基礎上,分析了區域創新能力的影響因素。借鑒吳豐林(2011)的思想,本文談到從區域創新資源、區域創新環境、技術創新產出、對外合作潛力和創新制度保障五個方面構建區域創新能力評價指標體系。因此,本文將區域創新能力子系統評價指標體系分為二級,如下頁表2所示。

表1 產業集聚綜合評價指標體系
3 產業集聚和區域創新能力的互動發展耦合協調度評價
3.1 數據來源和樣本選取
本文數據選取《中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2008—2015)、《河南經濟統計年鑒》(2002—2015)、《河南省科技年鑒》(2002—2015)、中國資訊行網站的精訊數據(2002—2015)和河南科委官網數據。選取了河南省中原城市群鄭州、洛陽、開封、許昌、新鄉、焦作、平頂山、漯河和濟源九座城市作為樣本進行整體研究。
3.2 產業集聚子系統
(1)主成分提取

表2 區域創新能力子系統評價指標體系
本文使用SPSS 19.0錄入2004—2015年的28項指標,選擇“分析”—“降維分—“因子分析”—選取變量—“描述”中因子提取方法選擇“主成分”方法,從而得到方差貢獻率分析表以及旋轉后的主成分載荷矩陣。結果顯示,中原城市群產業集聚子系統選取符合要求的3個主成分,這三個主成分的的累積貢獻率為89.050%。
按照累積貢獻率大于85%的原則,前三個特征值大于1的主成分,累積貢獻率為89.050%,得出提取三個主成分可以概括出大部分信息的結論。
(2)計算指標權重
通過式(1)將每項指標的因子載荷量分別與對應主成分系數相乘并且求和,得出2004—2015年間中原城市群產業集聚子系統每項指標的權重。其中,指標權重為負說明與產業集聚綜合發展呈負相關關系,在無量綱處理時分子為最大值減去指標原數據。對原數據進行極差法標準化處理,得出產業集聚子系統評價指標的標準化值根據式(2)和式(3),將產業集聚評價指標體系的無量綱矩陣與指標權重相乘求和,得出2004—2015年產業集聚子系統綜合發展水平值(見表3)。

表3 產業集聚綜合發展水平值
3.3 區域創新子系統
本文使用SPSS 19.0錄入2004—2015年的26項指標,具體過程如產業集聚子系統主成分分析的操作步驟一樣,得到方差貢獻率分析表以及旋轉后的主成分載荷矩陣。按照累積貢獻率大于85%的原則,前五個特征值大于1的主成分,累積貢獻率為93.976%,得出提取五個主成分可以概括出大部分信息的結論。
通過式(1)將每項指標的因子載荷量分別與對應系數相乘并且求和,得出2004—2015年間中原城市群區域創新能力子系統每項指標的權重。其中,指標權重為負說明與區域創新能力綜合發展呈負相關關系,在無量綱處理時分子為最大值減去指標原數據。
根據式(2)和式(3),將區域創新能力評價指標體系的無量綱矩陣與指標權重相乘求和,得出2004—2015年區域創新能力子系統綜合發展水平值(見表4)。

表4 區域創新能力綜合發展水平值
3.4 兩系統耦合協調度的測算
根據式(4)、式(5)、式(6),將產業集聚和區域創新能力子系統綜合發展水平值帶入公式,可求得兩者的耦合協調發展度。其中式(5)有兩個參數(a、β)未知,其取值大小根據產業集聚和區域創新能力的重要性確定。考慮到產業集聚和區域創新能力同等重要,本文以a=0.5,β=0.5為中間值,分別按照3∶7、4∶6、5∶5、6∶4、7∶3五種比例測算耦合協調度(見表5)。
根據已有的研究成果,借鑒相關參考文獻,按照耦合協調度的大小將產業集聚和區域創新能力的耦合協調程度分為三級:失調、基本協調、高度協調。

表5 2004—2015年中原城市群產業集聚和區域創新能力協調發展綜合水平
根據產業集聚和區域創新能力協調發展分類體系,將2004—2015年中原城市群產業集聚和區域創新能力協調發展狀況(α=0.5,β=0.5)進行比較可以得出兩者耦合協調發展變化情況,如下頁表6所示。
2004—2008年,中原城市群產業集聚和區域創新能力的耦合協調度很低(D<0.4),處于失調期。2009—2012年,中原城市群產業集聚和區域創新能力的耦合協調度增加(0.4<D<0.5),處于過渡期。2004—2015年中原城市群產業集聚和區域創新能力的耦合協調度逐漸提升(0.5<D<0.8),到達初步協調階段。在失調期,產業集聚與區域創新能力互動機制尚未形成,兩者相互影響較小,耦合協調度較低;在過渡期,區域創新能力逐漸受到重視,但其對產業集聚作用機制還不完善,對產業集聚發展的影響仍不穩定。到了初步協調階段,產業集聚和區域創新能力均被提上議事日程,兩者發展速度趨向一致,耦合協調度進一步提升。

表6 2004—2015年中原城市群產業集聚與區域創新能力協調發展類型
4 結論
本文在搜集統計數據的基礎上,利用耦合協調模型,對河南省中原城市群產業集聚和區域創新能力的互動績效進行評價,并對其互動階段進行判定,主要結論如下:
(1)區別于傳統產業集聚,創新背景下的產業集聚具備高度化、生態化和要素互動化的顯著特征。
(2)集聚視角下的區域創新能力借由各企業的交互式學習、知識的擴散、創新資源的優化配置、創新制度的構建等途徑得以提高。
(3)產業集群與區域創新能力的互動過程存在比較優勢、競爭優勢、創新優勢和財富優勢四個階段(對應起步、發展、成熟和衰落四個狀態),每個階段的資本要素特征、市場環境、產業集聚度和發展特征均不相同。
(4)在全球價值鏈理論、系統理論和循環經濟為指導下,產業集聚合區域創新能力之間存在良性互動的可行性路徑。
(5)實證量化分析表明,2004—2015年間中原城市群產業集聚和區域創新能力耦合協調經歷了失調期、過渡期和初步協調期三個階段,隨著對區域創新能力重視程度的提升,二者的耦合協調度有增大趨勢。總體而言,中原城市群的產業集聚和區域創新能力互動發展處于“比較優勢階段”,此階段的發展是以最小成本獲得積累為核心目標,具有協同創新能力不強、合作程度較低和技術擴散能力弱等問題。
(6)按照產業集聚和區域創新能力不同比重(3∶7、4∶6、5∶5、6∶4、7∶3),對2004—2015年中原城市群產業集聚和區域創新能力耦合協調度進行計算,發現隨著區域創新能力的比重增大,中原城市群產業集聚和區域創新能力耦合協調度有增大趨勢。因此,提高中原城市群對區域創新能力建設的投入力度,會對產業集聚和區域創新能力互動發展產生促進作用。
參考文獻:
[1]高妍伶俐.產業集聚、知識溢出與區域創新能力——基于東、中、西部高技術產業的實證研究[D].廣州:廣州暨南大學碩士論文,2014.
[2]郭明翰.基于產業集聚的知識溢出對區域創新的影響研究[D].南京:中共江蘇省委黨校碩士論文,2014.
[3]邱國棟,馬鶴丹.區域創新系統的結構與互動研究:一個基于系統動力視角的理論框架[J].管理現代化,2011,(4).
[4]張英杰.基于耦合協調度模型的西部地區產業集聚與金融發展的關系研究[C].杭州:“比較研究工作坊”會議,2013.
[5]Yang R.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Impact of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on Regional Innovation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Knowledge Spillover[D].Nanjing:Nanjing University of Finances and Economics,2014.
[6]馬永紅,李歡,王展昭.區際產業轉移與區域創新系統耦合研究—基于系統動力學的建模與仿真[J].科技進步與對策,2015,(1).
[7]傅利平,周小明,羅月豐.知識溢出與產學研合作創新網絡的耦合機制研究[J].科學學研究,2013,31(10).
[8]王鵬,曾坤.創新環境因素對區域創新效率影響的空間計量研究[J].貴州財經大學學報,2015,3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