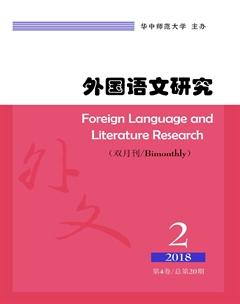勞倫斯·達雷爾《戀人們的吹笛手》中“回家”主題的政治倫理批評
內容摘要:以兩次世界大戰期間的英國殖民政治和社會文化為背景,勞倫斯·達雷爾在其自傳體小說《戀人們的吹笛手》中揭示了“帝國之子”沃爾什有“家”難回的經濟、種族與文化原因。與從被殖民“他者”的視角出發對殖民政治的倫理批判不同,達雷爾從對英國底層殖民者后代沃爾什的英國“家園”情節與文化焦慮的描寫入手,實現了對帝國輝煌之主流話語的政治倫理批判。
關鍵詞:勞倫斯·達雷爾;《戀人們的吹笛手》;回家;政治倫理批評
基金項目: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文學倫理學批評:理論建構與批評實踐研究”(13&ZD128)和華中師范大學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資助項目(CCNU17A06040)的階段性成果。
作者簡介:徐彬,華中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英語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現當代英國文學研究。
Abstract: Within the contexts of British colonial politics and social culture during two world wars, Lawrence Durrells autobiographical novel Pied Piper of Lovers reveals economic, racial and cultural factors that hinder the homecoming of the children of Empire. Different from the narrative perspective of the colonized “other” who launches ethical criticisms on colonial politics, Durrell carries out his political ethical criticism on imperial discourse of glo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Walsh Clifton, one of the descendants of low ranking empire builders, who suffers from British “home” complex and cultural anxiety.
Key words: Lawrence Durrell; Pied Piper of Lovers; homecoming; political ethical criticism
Author: Xu Bin is professor and Ph.D. supervisor at English Department of th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His research focuses on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British literature. E-mail: haihongjiji@163.com
截至1922年,大英帝國在全球范圍內所統治人口的數量達到四億五千八百萬,占當時全球人口總數的五分之一;英國已成為人類有史以來最大的帝國,也是一個世紀以來最重要的世界級強國。然而,在此歷史背景下英國著名作家勞倫斯·達雷爾(Lawrence Durrell, 1912-1990)出版的首部自傳體小說《戀人們的吹笛手》(Pied Piper of Lovers, 1935)中卻講述了“帝國之子”沃爾什有家難回的身份困惑,深度闡發了對底層“帝國建設者”及其后代在殖民地與移民英國后生活狀況的憂慮。
《戀人們的吹笛手》中,達雷爾指出小說主人公沃爾什的回“家”(英國)實際上是離“家”(印度)的流散生活的開始。在此基礎上,達雷爾進而提出并解答了“‘帝國之子沃爾什為何有‘家難回?”的問題。與從被殖民“他者”的視角出發對殖民政治的倫理批判不同,達雷爾從對英國底層殖民者后代沃爾什的英國“家園”情節與文化焦慮的描寫入手,實現了對帝國輝煌之主流話語的政治倫理批判。
一、被遺忘的“帝國之子”
在英國海外殖民地工作的英國人及其后代均可被稱為“帝國之子”。《戀人們的吹笛手》中的“帝國之子”具有英國殖民地建設者的倫理身份,然而也恰是這一身份將其囚困于印度偏遠地區,無法返回英國。在達雷爾筆下,帝國殖民政府對在底層工作的“帝國之子”的生活狀況不聞不問的態度與“帝國之子”對帝國事業的熱忱和奉獻形成鮮明反差。以沃爾什的父親英裔印度鐵路工程師約翰·克利夫頓為縮影,達雷爾描述了默默無聞的帝國建設者們在異國他鄉進行帝國殖民建設的酸甜苦辣和被帝國所遺忘的悲慘境遇,并以此闡發了對英國殖民政治的倫理批判。
小說以沃爾什的降生和母親因難產而去世開始,母愛缺失的主題從一開始就奠定了家園不完整的傷感基調。沃爾什的母親是印度“混血兒”,她的死與惡劣的生活條件有直接關系。達雷爾通過對為沃爾什母親接生的英國女醫生的心理描寫,反映了在印度殖民地邊遠地區為帝國事業工作著的英國人艱苦的生存狀況:“境況對她[英國女醫生]不利,饑餓、恐懼、疲倦…所有這些邪惡的東西都歸結于那個不恰當的詞[…]境況。……她的聲音很低,無助地且情緒激動地自我安慰著‘不能抱怨。不能抱怨。冰冷干裂的嘴唇讓她疼痛難忍”(Durrell 14)。年幼的沃爾什與父親相依為命,直到布倫達姑媽的到來。妻子去世后,約翰將全部精力投入工作之中,成為一個為大英帝國事業而獻身的工作狂,而忽略了對兒子的情感投入。
鐵路修建工作的需要約翰·克利夫頓和兒子沃爾什·克利夫頓搬進印度偏遠山區里名為“埃默洛爾德府”的新家,那是一棟英國在印度殖民早期遺留下來的老房子。在諸如此類的老房子中居住著像約翰·克利夫頓一樣的為殖民事業而定居于此的“帝國建設者”們。恰如這些房子,與其說他們已經扎根于此,不如說他們無奈于此,因為他們是身陷殖民地而無法自拔的人。
以沃爾什家的鄰居卡爾霍恩牧師和索爾比先生為原型,達雷爾刻畫了被遺忘了的、有家難回的英國殖民地建設者形象。卡爾霍恩是英國派駐印度的耶穌會牧師,他和教友們在山里建起了修道院,過著自給自足的生活。在帶領約翰·克利夫頓父子參觀修道院的過程中,卡爾霍恩自豪地介紹道:哥特式的窗玻璃是倫敦英國博物館對面玻璃公司里專業制作人員的杰作。倫敦產的玻璃已成為卡爾霍恩的心靈寄托,與英國相聯系的精神紐帶。卡爾霍恩是帝國派駐殖民地傳教的牧師代表;他和教友們一起在人跡罕至的山區為這項神圣的帝國事業盡忠職守。“他們人數眾多,總會準時出現在事故發生地,如在瘟疫爆發地區、火車撞小孩的現場,總會有至少一名耶穌會牧師出現” (Durrell 37)。此外,他們還以不同方式參與到帝國殖民建設中,如:卡爾霍恩牧師肩負起教育英國殖民地建設者的孩子(沃爾什和英國在當地茶葉種植場場主的兒子帕特里克)的責任;高薩摩牧師在約翰·克利夫頓引薦下成為鐵路建設攝影師。他們的神職身份和帝國建設者的倫理責任是他們在印度邊緣山區生活工作的精神寄托;然而,正如沃爾什所感受到的那樣,他們是值得同情的有家難回的人。
通過對索爾比先生的描述,達雷爾點明了“帝國之子”有家難回的經濟原因。與沃爾什談到回國話題時,索爾比先生言語之間流露出對鄰居阿比斯一家的羨慕和對自己生活狀況的無奈,“他[索爾比]當然知道,英格蘭是任何人都應該去的地方;殖民者省吃儉用地攢錢就是為了實現這一夢想;甚至連印度本地人都喋喋不休地談論著英格蘭(Belitee),希望有一天能看到那令人驚嘆的帝國中心的景象”(55)。索爾比先生對阿比斯一家去年夏天返回英國時的情境記憶猶新:阿比斯先生一連幾個星期都在談論回家的事情,包括如何讓女兒回“家”(英國)接受教育和在英國定居等話題。他的兩個女兒也一起驕傲地炫耀著即將到來的英國之行。他們言談之中最常使用的詞就是“家”。當沃爾什問索爾比先生為何不將昆蟲標本放到玻璃瓶里時,索爾比先生回答說幻想有一天它們能在閃電刺激下奇跡般地起死回生,然后統統逃離。索爾比先生仿佛他制作的昆蟲標本一樣成為英國殖民體制下“困死”異國他鄉的“殖民者的活體標本”,死后的逃離是索爾比先生自欺欺人的精神寄托。
年輕的沃爾什因無法理解父親送自己回英國上學的良苦用心而懊惱,但更為父親在印度殖民地的繁重工作鳴不平。他批評父親作為帝國建設者的“大公無私、無知、愚昧和對所謂團隊精神的令人厭煩的盲從”(159-160)。盡管如此,父親慈祥的身影時常閃現于沃爾什的睡夢之中。辛勤工作中的父親不幸遇難的夢魘揭示了沃爾什對父親的愛與掛念。現實生活應驗了沃爾什的夢魘,父親的離世使姑侄兩人回到英國后原本拮據的生活更加艱難,父親留下的微薄遺產無法支付沃爾什的學費,17歲的沃爾什因此輟學,每周三英鎊的遺產無法滿足沃爾什的日常生活所需。以沃爾什父子為縮影的帝國建設者及其子女的凄慘生活赫然在目,這也是達雷爾在該小說中殖民批判的最后一擊。
像查爾斯·狄更斯和T. S.艾略特等作家一樣,達雷爾在《戀人們的吹笛手》也充分運用黑夜與倫敦霧等自然現象來揭示主人公沃爾什的內心世界,預示了沃爾什父親死后前途渺茫的生活:
搖搖晃晃、叮當作響的列車將沃爾什拉向遠方的黑暗,拉向倫敦。行李搬運工問他是否需要搬運行李。在地獄般混亂、嘈雜的聲音中,那人的聲音好似在耳邊的低語。[……]夜里的霧跌倒在空蕩蕩的街道上,又無聲無息地爬上一排排數不清的房子,試圖努力洗刷掉那些房子無盡的相似之處[……]他感到霧就在嗓子眼里,像一雙雙充滿敵意的手緊緊壓迫著他的肺。(173)
父親的死不僅切斷了沃爾什的經濟來源,還切斷了他對印度“家園”的情感牽掛。在這種情況下,沃爾什自然會有一種被壓的喘不上來氣的感覺。
《戀人們的吹笛手》為讀者們呈現了一組生活在大英帝國殖民體系底層殖民者們的畫像,這一群體像是對維多利亞時期流行于英國文壇的荷馬史詩般宏大殖民敘事的反諷。奧德賽征服異邦的敘事模式給擁護帝國殖民的作家,如哈葛德(Sir H. Rider Haggard, 1856-1925)和吉卜林(Rudyard Kipling, 1865-1936)等提供了創作靈感。與上述作家不同,達雷爾站在英國殖民地建設者及其后代的立場上,批判了英國殖民主義政治給“帝國之子”造成的有家難回的生活困境。
二、“不能接觸的人”與種族歧視
沃爾什站在駛向英國的輪船的甲板上,目睹人們激動的表情,聽到人們看到多佛海灘的峭壁(Dover Cliffs)時發出的“白色終歸是白色”(Durrell 110)的感嘆。沃爾什與“白色終歸是白色”的多弗海峽峭壁之間的心理距離暗示了他對自己“混血兒”身份的認知產生的自卑情結。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英國社會充斥著種族歧視思想,以英印混血兒身份來到英國的沃爾什被視為“不能接觸的人”(the untouchables),從而被英國社會邊緣化。達雷爾闡釋了英國本土生人施加于來自殖民地移民身上的“我尊你卑”的倫理關系,這與沃爾什一家在印度享有的英國殖民者的優勢地位形成強烈反差。回到英國,沃爾什非但未得到“帝國之子”應有的禮遇,反而被降格為二等公民。沃爾什的暴力行動和自我流放可被視為化解自我倫理身份危機的策略。
沃爾什對“家”(英國)的冷淡態度與索爾比先生和阿比斯先生對“家”的渴望形成鮮明反差。在沃爾什心中印度才是“家”,這不僅是因為母親是印度人,更是出于沃爾什對印度大自然生活的熱愛。與無憂無慮的印度童年生活相比,沃爾什“返回”英國后的生活著實令他沮喪。敏感的沃爾什已經覺察出自己的與眾不同,如沃爾什的姑媽所說白色皮膚、金黃色頭發的沃爾什從相貌上看幾乎與土生土長的英國孩子沒有區別,只是那雙黑眼睛卻能讓人看出沃爾什“非本土生人”(non-patrial),而是來自殖民地的“混血兒”。也正是有關“非本土生人”的移民政策在1968年將達雷爾認定為“非本土生人”,從而拒絕了達雷爾加入英國國籍成為英國公民的申請①。借《戀人們的吹笛手》達雷爾再現了作家本人12歲時在父親安排下返回英國的那段心酸的記憶:
似乎無法準確描述他[沃爾什]站在輪船甲板上,看著如珍珠般潔白的懸崖在淡淡的海嵐中迂回綿延,失望之情油然而生。[……]這比他想象中的要小的多![……]高聲叫喊、指指點點和慷慨激昂的人畢竟是少數。大多數人都靜靜地站著,緊抓圍欄,體驗著那份在流放過程中偶爾會涌上心頭的愛國情懷。(109)
而這種思想在著名現代主義小說家弗吉尼亞·伍爾夫的作品《出航》(The Voyage Out 1915)和《達洛維夫人》(Mrs. Dalloway 1925)中已有所體現。“伍爾夫不加掩飾地譴責了異族通婚和文化雜合現象,這反映了帝國主義者的優生論(eugenism)主張” (Acheraiou 97)。《達洛維夫人》中,英國上層階級的貴婦達洛維夫人對剛從印度回國的彼得·沃爾什(Peter Walsh)充滿期待,不僅是因為沃爾什是達洛維夫人年輕時的追求者,更重要的是沃爾什先生是達洛維夫人回憶自己年輕時期的重要線索,是當晚帝國晚宴上不可或缺的一道異國風景線。在《達洛維夫人》中,彼得·沃爾什對五年來倫敦的巨大變化、人們生活水平的顯著提高感到驚奇,然而“印度之后”(after India)(Woolf 78)這一時間表述的重復使用讓人自然而然地聯想到英國在以東印度公司的建立為標志的殖民主義經濟掠奪。
與伍爾夫筆下能夠進入英國上流社會的彼得·沃爾什不同,達雷爾筆下的沃爾什·克利夫頓是帝國底層殖民者的后代,血統的不純使沃爾什·克利夫頓成為遭帝國冷落的“不能接觸的人”。回國后的沃爾什和姑媽布倫達遭到英國人的種族歧視。在火車站布倫達請搬運工給他們運送行李,雖然搬運工聽命行事,(正如英國人察覺出對方的下等人身份時的通常反應那樣)對姑媽卻非常粗魯。詹姆斯·吉福德教授在注釋中評論道:沃爾什和姑媽之所以會受到此番冷遇,“很有可能是因為布倫達的英印口音,再加上她對社會下層人的恭順態度,讓人一眼就看出她是說英語的外國人”(Gifford 261)。達雷爾清楚無誤地指出,融入英國社會生活對沃爾什和姑媽布倫達來說是件異常痛苦的事情。
姑侄兩人強顏歡笑,對在倫敦迷失自我的失落感隱忍不發。姑侄兩人的心理反應恰好應和了薩義德(Edward Said)對流放者心態的描述“[流放者]在試圖將流放理解為‘對我們有好處時卻緘默無語”(174)。幾個星期以來,他們只有在房地產經銷商那里才享受到久違了的禮遇;然而即便這種禮遇也是虛假的,因為它是建立在經濟利益基礎上的。布倫達在房屋中介的推薦下決定購買一棟名為“綠籬”的房子。中介人是個“有二十年從業經驗的冷漠且經驗老道的惡棍”,而他所服務的機構“是為滿足‘回家的殖民者們(the colonial who comes “home”)的需求專門設立的”(Durrell 115)。由此可見,殖民者從英國海外殖民地的回歸已然成為拉動當時英國本土經濟內需的一個重要環節。歸國殖民者與英國本土居民間的首次“情感”交流也僅限于此。
薩義德指出“民族主義與對某地的歸屬感緊密相連,是對人群和遺產的認同。它確定了由語言、文學和習俗等核心要素所構成的我們稱之為‘家園的社區....[民族主義]可以用來抵抗流放,消減流放帶來的危害”(Said 176)。在父親和姑媽的安排下,少不更事的沃爾什從出生地印度被動地流放至英國。由于年紀、閱歷、語言和文化知識所限,沃爾什尚不具備對英國民族主義認知與習得的能力。英國民族情感的缺乏使童年時期的沃爾什在流放過程中患上了無法言說自我和無法與外界良好溝通的失語癥。進入英國學校后,沃爾什帶有暴力色彩的行為,如與同學打架和酷愛拳擊運動等則是沃爾什流放初期失語癥狀態下言說自我的極端方式。之后,沃爾什沉溺于文學閱讀和音樂演奏之中;文學和音樂成為沃爾什精神層面上自我安慰與言說的主要方式。
薩義德認為:“在特殊情況下,流放者可養成對流放的戀物癖,而斷絕所有的聯系并放棄所有的責任”(183)。小說中,沃爾什違背學校的要求自行終止了拳擊訓練,變得憤世嫉俗、疏遠他人并沉浸于文學閱讀和對音樂的喜愛之中;父親去世后沃爾什離家(姑媽在倫敦購置的新家)出走,這些都可被視為薩義德所說的“流放戀物癖”的表現。就面臨倫理身份危機,充滿焦慮和手足無措的沃爾什來說,這種“流放戀物癖”卻有著較為積極的作用。沃爾什的主動流放是自我心理防御機制的體現,涉及主人公本人與外部世界(自我與他者)、與陌生環境和人物間相互關系的調節,目的在于建立內部精神世界與外部物質世界之間的動態平衡,以期達到化解倫理身份危機的功效。
三、20世紀20、30年代英國文化的道德焦慮
達雷爾在《戀人們的吹笛手》的創作中雖繼承了現代主義前輩探索主人公內在心理世界的寫作技巧,但并沒有因此而忽視對現實世界的指涉,②主要表現在該小說對英國20世紀20、30年代諸多文化現象及由此而引發的道德焦慮的描述與批判中;批判本身內含主人公沃爾什試圖理解并融入“家園”(英國)文化的渴望。
“健壯”和“效率”是二十世紀初英國社會文化現象探討中頻繁出現的關鍵詞。“帝國中心潛伏著不健壯的癌瘤”③的焦慮普遍存在,這一焦慮的影響甚至延續至20世紀20、30年代的英國社會。在“健壯至上”的文化大背景下,身材魁梧高大的沃爾什因擅長拳擊而被老師看中。為了能讓他在拳擊比賽中取得更好成績,校長決定改善他的學習和生活環境,讓他從公共休息室搬到兩人一間的房間中去。其實沃爾什并不喜歡拳擊運動,他之所以從事拳擊運動是因為沒有其它運動能幫助他釋放逐漸發育的身體里蘊藏著的動物般的“野性的呼喚”。放棄拳擊運動的沃爾什被同學們戲稱為“書呆子”。由于沃爾什酷愛彈鋼琴和文學閱讀,所以沒人愿跟他交朋友,因為在同學們眼中沃爾什的喜好是缺乏男子漢陽剛氣的表現。沃爾什在學校的受歡迎程度也因此而大打折扣,并逐漸被同學和老師所冷落。沃爾什的室友特恩布爾不無諷刺地譴責了學校重體輕文和師資力量薄弱的現狀。“圖書館簡直就是個悲哀。校長幾乎閹割了所有值得一讀的作家。就連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也被視為不潔而慘遭清洗。圖書館里連完整的佩皮斯(Pepys)④日記都沒有”(Durrell 153)。沃爾什列舉了所在學校文化教育的種種弊病,如:校長對他進行性教育時的含糊其辭、拉丁語老師的知識匱乏、理科老師和法語課老師授課時的頻繁跑題以及一天兩次的無聊和搞笑的禮拜儀式。值得慶幸的是英語兼歷史老師濱胡克引導沃爾什養成了對文學的熱愛;然而令人遺憾的是盡管濱胡克知識淵博,知道哪些書是好書,卻苦于囊中羞澀無力買書供沃爾什和特恩布爾閱讀。
沃爾什與特恩布爾之間的交流是沃爾什學校生活的唯一亮點。他們一起學習和討論人文領域里的新思想,如: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人權和馬爾薩斯主義等。沃爾什的黑色筆記本記錄了自己一年以來從未間斷、但缺乏系統性的閱讀收獲和與特恩布爾之間的辯論內容。沃爾什在筆記中肯定特恩布爾聰明才智的同時,間接批判了英國社會的道德觀與價值觀:“這個完美的人[特恩布爾](從心靈層面上講)并沒被教養強加到他身上的價值取向、愛恨情感和愛國主義等觀念所動搖。受它們牽制是脆弱的表現”( Durrell 160)。雖然沃爾什在筆記中提及與英國主流文化妥協的意向,但反社會才是他青春叛逆期的主導思想。
沃爾什所處的時代也是英國“聰明年輕人”(或“光彩年華”Bright Young Things)的時代。“聰明年輕人”是通俗小報給20世紀20年代英國倫敦過著波西米亞式生活的年輕貴族和上流社會人士起的綽號。他們經常舉辦奇裝異服的晚會,在夜晚的倫敦探尋寶藏;他們酗酒成性,吸毒成癮。雖然在對這一時期自上而下的社會頹廢文化現象的揭示與批判方面達雷爾的《戀人們的吹笛手》不如諾埃爾·考沃德(Noel Coward, 1899-1973)的戲劇《漩渦》(The Vortex, 1924–1925)來的那么直接和尖銳,但“性、毒品和跳舞音樂——這一時代的符碼和獸欲漩渦中的元素”(Lucas 117)在《戀人們的吹笛手》中皆有體現。
第一次世界大戰后移居英國倫敦工作的美國心理學家霍默·萊恩(Homer Lane, 1875-1925)是“身體自由”的倡導者,他提出“徹底的行為只有——完全自我表達——毫無疑問會是至善的結果”(轉引自Lucas 120)。萊恩的病人約翰·萊亞德(John Layard)在繼承萊恩主張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上帝真正的意義在于我們身體的欲望,欲望才是我們本性的內在法則,[……]我們應不惜一切代價阻止對欲望有意識的控制。不服從欲望之神才是罪惡的”(轉引自Lucas 120)。20世紀早期著名心理學家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和果代克(George Groddeck)等人的心理分析理論以及勞倫斯(D. H. Lawrence)和奧登(W. H. Auden)等知名作家的作品成為20世紀20、30年代英國年輕人追求自由的學理依據。他們認為已經找到了自我解放的“科學”解釋,并將壓抑自我視為不幸和疾病的癥結之所在。
因父親去世無力支付學費而被迫輟學的沃爾什在特恩布爾的介紹下前往倫敦投奔名叫羅賓·埃姆斯的年輕專欄作家。沃爾什發現以梵高和高更兩位后印象派畫家的生平為素材創作了《梵高》和《野獸之美》的著名女小說家斯沃普就住在羅賓·埃姆斯的樓下。沃爾什在火車上偶遇的資深新聞記者對斯沃普作品的評價卻是“徹底違背了倫理道德”(Durrell 191)。這一插曲為沃爾什此后與埃姆斯、拉塞爾和伊莎貝爾等人在一起的波西米亞式的生活經歷做了鋪墊;也正是這段生活經歷激起了沃爾什對享樂主義文化的反思與道德譴責。
演員康羅伊舉辦的公寓派對讓沃爾什意識到英國社會所面臨的道德危機。前往派對的路上,羅賓對沃爾什解釋說:“康羅伊是個蹩腳的演員,錢多的都不知道怎么花。他有個錯誤的想法,他認為波西米亞主義才是生活的本質”(218)。沃爾什對派對上人們酒后亂性和吸食毒品后的瘋狂舉動表示不解。
伊莎貝爾認出了跳舞的兩個女青年是“明妮和凱特”,于是生氣地說:“真見鬼,她們為什么非要在公共場合這樣跳舞。實在是有傷風化”(218)。⑤專欄作家出身的羅賓見多識廣,對此并不驚奇,他評論道:“還有什么是符合道德的呢?存在即是合理”。沃爾什希望“人性不要淪喪到臭氣難聞的地步”(219)。作為那一特定時期文化代言人的英國著名詩人奧登在1929年的一篇日記中如實記錄了英國20、30年代的倫理價值取向:“‘行善能帶來幸福是一個危險的倒置。‘幸福、開心即是善這才是真理”(Auden 300)。然而達雷爾并不認同前輩作家奧登的觀點,在《戀人們的吹笛手》中強烈批評了英國當時享樂至上的主流文化思想。
沃爾什與英國當時文化的妥協與讓步主要體現在他的音樂創作上。羅賓·埃姆斯發現了沃爾什創作抒情民謠歌曲的才能,并將沃爾什推薦給了有錢的音樂制作人加蘭。雖然沃爾什對加蘭給他的面試感到失望,但這一經歷對沃爾什來說還是有一定啟發意義的。加蘭在他的工作室里用鋼琴彈奏著令人作嘔、拖沓粘人的華爾茲。他對沃爾什說:“你肯定認為我在糟踐藝術”。“但如果你能給我帶來類似這樣的作品,”加蘭重復說:“那你將永不會受窮挨餓”(235)。起初沃爾什對爵士樂不屑一顧,認為爵士樂過于低俗登不上大雅之堂。加蘭讓沃爾什將此前彈奏的抒情民謠改成爵士樂的形式演奏,并給沃爾什寫了一張50英鎊的支票買下了修改后的作品。雖然沃爾什對加蘭“串改音樂”、“輕賤音樂”的作法怒氣未消,但在勞埃德銀行把那張50英鎊的支票兌換成現金時的興奮已經改變了沃爾什的音樂創作思想。達雷爾運用類似意識流的寫作手法,真實反映了沃爾什此時此刻的思想斗爭與轉變:“讓加蘭隨便從曲子里選取爵士樂里可用的旋律是不是顯得自己太懦弱了?是不是像他這樣的業余曲作家的愚鈍讓他自感屈辱?但無論如何,這一經歷至少讓他看到寫爵士樂是能掙錢的,這才是值得慶祝的事情;再不濟他也能寫點兒賣錢的小曲兒。爵士樂并不難寫”(237)。
經濟上的獨立和精神上歸屬感的建立讓長期在兩個“家”(印度和英國)的夾縫中生存著的沃爾什終于有了回“家”的感覺。沃爾什在倫敦街道上偶遇幾年前在夜晚海灘上邂逅的神秘女子露絲。為了幫助露絲實現去瑞士的心愿,沃爾什決定給加蘭寫爵士樂。從露絲的朋友那里得知露絲患有心臟瓣膜病,將不久于人世的消息后,沃爾什更加堅定了與露絲生活在一起的決心。這種對列維納斯所說的他者(露絲)責任感的形成是沃爾什精神上“回家”的關鍵一環。沃爾什已擔當起了照顧露絲的“丈夫”的角色。在肩負責任的同時,沃爾什也獲得了自我解放:“從某種意義上講,這個光禿禿的、蜿蜒曲折的國家[英國]解放了我,雖然我說不清楚從什么方面以及如何解放了我。我曾在某個地方有過這樣的經歷。我感覺已被囚禁許久。而現在我再次感受到腳下的大地....”(252)。小說以沃爾什給好友特恩布爾的信結束。這封信應被視為沃爾什精神頓悟后的內心獨白。曾經囚禁沃爾什的是游離于印、英兩個“家”之外,孰是孰非的“家園”情節,而最終解放沃爾什的并非是英國,而是自建“精神家園”的沃爾什本人。
綜上所述,英國是沃爾什不得不回又無法回歸的“母親國”(英國),然而英國殖民政治下的經濟與道德束縛、盛行于20世紀20、30年代英國社會中的種族歧視思想和沃爾什本人與當時英國社會文化的格格不入是導致“帝國之子”沃爾什有“家”難回的主要原因。在對以上三個方面進行倫理道德批判的基礎上,達雷爾完成了對英國(“帝國之子”夢寐以求的大英帝國的中心)的去魅化闡釋,意在指出“帝國之子”“回家”的過程與他們被“家園”(英國)邊緣化的過程并行不悖。密德薩斯大學(University of Middlesex)文化研究學家喬納森·盧瑟福寫道:“家園是我們發出聲音的地方”(Home is where we speak from.)(Rutherford 24)。就被邊緣化的沃爾什而言,家園與其說是單純的物理存在,毋寧說是一種精神歸屬;音樂創作與對露絲純真的愛情最終成為沃爾什抒發自我之聲的精神家園。沃爾什以“精神家園”論替代英國“家園”論的做法是因“有家難回”而采取的尋求心理安慰和與外部世界暫時妥協的無奈之舉。小說結尾,達雷爾意在通過對沃爾什此種自欺欺人的家園心理機制的描述進一步凸顯了“帝國之子”的孤苦境地,深化了對英國殖民政治與社會文化的倫理批判。
注釋【Notes】
①《衛報》記者伊扎德曾就達雷爾的國籍問題進行了專門報道:“勞倫斯·達雷爾,二十世紀末最著名、其作品最暢銷的作家之一,在名氣如日中天之際,其加入英國國籍的申請卻遭到拒絕。1966年,《亞歷山大四重奏》的作者達雷爾因議會法案的限制無法入籍英國,該法案旨在減少來自印度、巴基斯坦和西印度國家的移民數量。[……]持英國護照的作家[達雷爾]每次回國時都不得不提交入境申請。”參見John Ezard, “Durrell Fell Foul of Migrant Law,” The Guardian, April 29, 2002. February 02, 2018. 〈http://www.theguardian.com/uk/2002/apr/29/books.booksnews. 〉
②布盧姆(Clive Bloom)認為英國現代主義小說“敘事向內探索心理力量而拒絕探討外在(社會)現實。在拒絕探討政治問題的同時,現代主義者僅關注家庭和性等相關問題(二者都被作為精神創傷加以對待)”。參見Clive Bloom, “Introduction,” Literature and Culture in Modern Britain, Volume One: 1900-1929, ed. Clive Bloom(London and New York: Longman, 1993): 27。
③格林斯萊德(William Greenslade)以1905年6月28日英國議會刊發的以“國民健康”(Health of the People)為題的一則廣告和1908年羅伯特·鮑威爾爵士(Sir Robert Baden-Powell)為宣傳童子軍“強壯健康的男孩”形象而作的漫畫為例說明了當時英國社會對身體健康程度的高度重視。參見William Greenslade, Degeneration, Culture and the Novel 1880-194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186。
④塞繆爾·皮普斯(Samuel Pepys, 1633-1703)英國托利黨政治家,歷任海軍部首席秘書、下議院議員和皇家學會主席,但他最為后人熟知的身份是日記作家。皮普斯寫于1660至1669年之間的日記常被視為文學典范。
⑤吉福德教授在《戀人們的吹笛手》的注釋中寫道“達雷爾描寫的出現于派對中的同性戀現象和苦艾酒在當時都是不合法的”。參見James Gifford, “Notes,” Pied Piper of Lovers, by Lawrence Durrell(Victoria: University of Victoria, 2008): 255-267。
引用文獻【Works Cited】
Acheraiou, Amar. Rethinking Postcolonialism Colonialist Discourse in Modern Literatures and the Legacy of Classical Writers.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08.
Auden, W. H. The English Auden Poems, Essays and Dramatic Writings 1927-1939. Ed. Edward Mendelson.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77.
Durrell, Lawrence. Pied Piper of Lovers. Victoria: University of Victoria, 2008.
Gifford, James, “Notes.” Pied Piper of Lovers. Lawrence Durrell. Victoria: University of Victoria, 2008. 255-267.
Lucas, John. The Radical Twenties. Nottingham: Five Leaves Publications, 1997.
Rutherford, Jonathan. “A Place Called Home: Identity and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Difference.” Identity: Community, Culture, Difference. Ed. Jonathan Rutherford.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1990. 9-27.
Said, Edward. Reflections on Exile and Other Essay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P, 2000.
Woolf, Virginia. Mrs. Dalloway. London: Penguin Books, 1992.
責任編輯:劉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