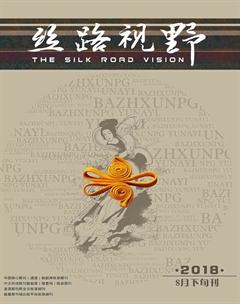言語(yǔ)交際視角下的調(diào)戲與反調(diào)戲
劉睿璿 曹小雪
【摘要】本文基于《紅樓夢(mèng)》中第十一回和第十二回以及《溫莎的風(fēng)流娘們》兩個(gè)文本,以其中男性的調(diào)戲行為和女性做出的反調(diào)戲回應(yīng)為例,從言語(yǔ)交際的視角解讀男性和女性性別差異的體現(xiàn)以及不同命運(yùn)的深層次的文化原因。
【關(guān)鍵詞】調(diào)戲與反調(diào)戲;性別差異;言語(yǔ)交際
一、引言
文學(xué)巨匠曹雪芹的《紅樓夢(mèng)》和莎士比亞的《溫莎的風(fēng)流娘們》,在國(guó)內(nèi)外享有盛譽(yù)。國(guó)內(nèi)外學(xué)者從不同的視角對(duì)上述兩個(gè)文本分別進(jìn)行過(guò)研究,其成果頗豐。但通過(guò)言語(yǔ)交際視角,將二者在相應(yīng)章節(jié)的男女之間的調(diào)戲與反調(diào)戲進(jìn)行跨文化對(duì)比研究卻幾乎沒(méi)有。兩大經(jīng)典著作中,男女之間調(diào)戲與反調(diào)戲中的言語(yǔ)交際里所呈現(xiàn)相似性和差異性與文中所處的歷史背景、社會(huì)現(xiàn)實(shí)、個(gè)人地位和期許以及作者的愿景息息相關(guān)。通過(guò)跨文化對(duì)比研究,兩部作品中男性調(diào)戲和女性反調(diào)戲在言語(yǔ)交際方面的相似性和差異性皆一一展現(xiàn)。
二、《紅樓夢(mèng)》中的調(diào)戲與反調(diào)戲
在《紅樓夢(mèng)》第十二回“王熙鳳毒設(shè)相思局 賈天祥正照風(fēng)月鑒”中賈瑞調(diào)戲王熙鳳,直白露骨,男性言語(yǔ)的侵略性以及霸權(quán)特征一覽無(wú)余;而王熙鳳不正面回應(yīng),說(shuō)話綿里藏針,采取以退為進(jìn)的策略,曖昧地變著法折磨賈瑞。賈瑞作為賈家的旁支子弟,從小生活在祖父賈代儒高壓嚴(yán)苛的管教下,因此在外行事則是走了另外一個(gè)極端,其人格具有典型的雙重性。賈瑞“是個(gè)圖便宜沒(méi)行止的人”,“反助紂為虐討好兒”替薛蟠幫腔無(wú)理索要錢(qián)財(cái),趁祖父不注意就“非飲即賭,嫖娼宿妓”,形成了一種欺軟怕硬、趨炎附勢(shì)的性格,做人做事心術(shù)不正。也正是因?yàn)檫@種性格,才會(huì)輕易中陷阱,遭受宰割精盡人亡。
而王熙鳳從小接受得是男孩子一般的教育,“自幼假充男兒教養(yǎng)的,學(xué)名王熙鳳。”王熙鳳出身于外交家庭,其祖父是外交官,其叔父王子騰開(kāi)始是節(jié)度使,后升至內(nèi)閣大學(xué)士。從小的生活環(huán)境就讓她與外界交流更多,有著不同一般女子的見(jiàn)識(shí)和風(fēng)度。其名字具有男性化色彩,“熙”寓意著光明,“鳳”本為雄性鳥(niǎo),古代以鳳喻男兒,王熙鳳在賈府里被稱作“鳳哥兒”“辣子”“潑皮破落戶”等,足以體現(xiàn)其男子行事風(fēng)格和氣度,具備了雌雄同體的雙性氣質(zhì)特征,兼有強(qiáng)悍和溫柔、果斷與細(xì)致等性格,能靈活應(yīng)對(duì)不同場(chǎng)合,印證了波伏娃的“女人并不是天生的,而是被塑造成的”這一觀點(diǎn)。
在賈瑞與王熙鳳相遇之時(shí),“這是瑞大爺不是”“不是不認(rèn)得,猛然一見(jiàn),不想到是大爺?shù)竭@里來(lái)。”王熙鳳說(shuō)話字斟句酌、禮貌謙卑,給足了賈瑞的面子,采取了順應(yīng)性和以退為進(jìn)的言語(yǔ)策略。但賈瑞蹬鼻子上臉“也該是合該與嫂子有緣”,明顯在調(diào)戲鳳姐,凸顯了男性在言語(yǔ)中對(duì)女性的侵略性和壓迫性。鳳姐這個(gè)明眼人也知道是“癩蛤蟆想吃天鵝肉”,然后開(kāi)始主動(dòng)“調(diào)戲”賈瑞,引誘賈瑞上鉤,“聽(tīng)你說(shuō)這幾句話兒,就知道你是聰明和氣的人啦”。后來(lái)賈瑞見(jiàn)鳳姐的時(shí)候,“我如今見(jiàn)嫂子,最是有說(shuō)有笑,極疼人的,我怎么不來(lái)?——死了我也愿意”。賈瑞露骨的言語(yǔ)體現(xiàn)其好色到癡迷于其中,鳳姐為了整賈瑞則極力彰顯自己的女性氣質(zhì),說(shuō)話更間接隱晦“放尊重著,別叫丫頭們看見(jiàn)笑話。”由此可見(jiàn),表面上看似是賈瑞在露骨地調(diào)戲鳳姐,展示自己的男性主導(dǎo)地位,實(shí)質(zhì)上卻是性格強(qiáng)勢(shì)的鳳姐利用賈瑞的饞性,使用模糊曖昧的順應(yīng)式的言語(yǔ)反調(diào)戲賈瑞。在上述交際中,王熙鳳把對(duì)話作為一種維護(hù)和諧關(guān)系的重要手段,言語(yǔ)婉轉(zhuǎn)隱晦,過(guò)渡自然,展現(xiàn)出女性的隱忍以及對(duì)自我尊嚴(yán)的維護(hù);而賈瑞則通過(guò)開(kāi)門(mén)見(jiàn)山的提問(wèn)方式獲取實(shí)質(zhì)性的信息,言語(yǔ)上具有優(yōu)越感和霸權(quán)般的占有欲。
在兩人分別時(shí),鳳姐心里暗忖道“幾時(shí)叫他死在我手里,他才知道我的手段!”鳳姐擁有其男性性格中的心狠手辣。她把賈瑞當(dāng)成禽獸不如的人,其潛意識(shí)里的傳統(tǒng)女性倫理觀念可窺見(jiàn)一斑。她的行為是一種自衛(wèi)性質(zhì),她守護(hù)自己的貞操,守護(hù)男權(quán)社會(huì)下封建禮教所賦予女性“三從四德”的規(guī)矩。“在中國(guó)古代的男權(quán)社會(huì),性別價(jià)值觀是男性用來(lái)賦予女性的武器,是社會(huì)用來(lái)定義‘女性的手段,社會(huì)所定義的‘女性都是她們必須接受的生存方式”。因此男權(quán)社會(huì)中的王熙鳳,一方面,有對(duì)男性權(quán)力的渴望和訴求,另一方面,也有對(duì)女性地位的不滿和反抗。
三、《溫莎的風(fēng)流娘們》中的調(diào)戲與反調(diào)戲
《溫莎的風(fēng)流娘們》主要是講得是培琪大娘和福德大娘面對(duì)沒(méi)落貴族福斯塔夫的調(diào)戲所做出的反調(diào)戲應(yīng)答。福斯塔夫其貌不揚(yáng),作為落魄的騎士貴族,為了維持生活,調(diào)戲有夫之?huà)D,但并未成功,遭到反調(diào)戲時(shí)痞氣十足且自我感覺(jué)良好,“說(shuō)得干脆些,我想去吊福德老婆的膀子。”莫爾根對(duì)福斯塔夫有一段評(píng)論“他既容易受騙,又富有機(jī)智;原則上軟弱,而本性上果斷”看似相互矛盾,其實(shí)和諧統(tǒng)一。“我要去接管她們兩人的全部富源,她們兩人便是我的兩個(gè)國(guó)庫(kù);她們一個(gè)是東印度,一個(gè)是西印度,我就在這兩地之間開(kāi)辟我的生財(cái)大道。你給我去把這信送給培琪大娘;你給我去把這信送給福德大娘。”他的兩封情書(shū)內(nèi)容相同只是收信人不同,愛(ài)的理由也是大家都風(fēng)流,他只是把調(diào)情當(dāng)作獲取財(cái)富的手段。福斯塔夫具有典型的雙重人格,其主體自我和客體自我不和諧,甚至矛盾。他的主體自我把自己看作尊貴的貴族、勇敢的騎士,而客體自我被認(rèn)為是荒唐的小丑、懦弱的懶漢,兩種認(rèn)識(shí)相互沖突。鄉(xiāng)村法官說(shuō)道要去法院告發(fā)福斯塔夫,因?yàn)楦K顾虼蛄怂业钠腿耍瑲⒘怂业穆梗K顾虿灰樥f(shuō):“可是沒(méi)有吻過(guò)你家看門(mén)人女兒的臉吧?”他的流氓無(wú)賴性格在此一覽無(wú)余。車(chē)爾尼雪夫斯基評(píng)價(jià)道“福斯塔夫這個(gè)人深知自己身上的一切卑鄙、無(wú)恥和下賤之處,但是他在其中是浸染得這樣臟,他覺(jué)得他已經(jīng)是對(duì)的。他嘲笑了這些放蕩行為,通過(guò)嘲笑自己以及別人的放蕩行為,就和這些放蕩行為保持和解。”大娘們決定將計(jì)就計(jì),“決定捉弄這個(gè)壞東西”。福斯塔夫和大娘相約家中,第一次被塞進(jìn)臟衣簍里丟進(jìn)泰晤士河里爛泥溝里,“像一車(chē)屠夫切下來(lái)的肉骨肉屑一樣”“差不多死了三次”,第二次經(jīng)過(guò)快嘴桂嫂的勸誘被打扮妖婦,被前來(lái)的福德打了出去。第三次在林子里被扮成精靈模樣的培琪家女兒捉弄,然后承認(rèn)錯(cuò)誤。在懲惡揚(yáng)善、激濁揚(yáng)清方面,風(fēng)流娘們極盡風(fēng)流;在愛(ài)情婚姻方面,十分忠貞。
在收到福斯塔夫的信之后,培琪大娘不快說(shuō)道,“這個(gè)酒鬼究竟從我的談話里抓到了什么出言不檢的地方,竟敢用這種話來(lái)試探我?”言語(yǔ)之間體現(xiàn)了她們性貞潔觀念以及當(dāng)時(shí)女人的地位,認(rèn)為受到騷擾是女性自己的原因。福德大娘抱怨福德“那股醋勁兒才大呢”,不過(guò)“培琪是從來(lái)不吃醋的”。的確,福德也認(rèn)為“他要是真想勾搭我的妻子,我可以假作癡聾,給他一個(gè)下手的機(jī)會(huì)”。福德不僅敵視福斯塔夫,而且也懷疑自己的老婆,有著強(qiáng)烈的妒忌心,認(rèn)為女人是男人的附屬品,福德僅僅認(rèn)為婚姻和愛(ài)情是一種維護(hù)社會(huì)地位和面子的“工具”。他先化裝成白洛克去調(diào)查試探福斯塔夫,給他“誘餌”,鼓勵(lì)福斯塔夫去追求自己的妻子,把自己誘導(dǎo)產(chǎn)生的結(jié)果當(dāng)成大娘和福斯塔夫自然達(dá)成的結(jié)果。可見(jiàn),一般當(dāng)男性發(fā)現(xiàn)女性不忠于自己的時(shí)候會(huì)吃醋,而女性受到異性騷擾會(huì)反省自己。德國(guó)哲學(xué)家卡西爾曾提出觀點(diǎn)“符號(hào)化的思維和符號(hào)化的行為是人類(lèi)行為中最富于代表性的特征”,社會(huì)對(duì)女性“符號(hào)化”的認(rèn)知讓人潛移默化里的思維和行為趨向“符號(hào)化”,對(duì)女性的認(rèn)知也是如此。雖然莎翁筆下的女性有了一定的自我意識(shí),但離自我解放還相差甚遠(yuǎn)。
四、兩個(gè)文本中調(diào)戲與反調(diào)戲的異同
16世紀(jì)至17世紀(jì)的中西方男權(quán)社會(huì)中,男性毫無(wú)疑問(wèn)占據(jù)言語(yǔ)中的主導(dǎo)性地位。男性因本能欲望開(kāi)始明目張膽地調(diào)戲,而女性面對(duì)這種輕視和侮辱則進(jìn)行著委婉機(jī)智的反調(diào)戲,甚至還會(huì)主動(dòng)反省和檢點(diǎn)自己的行為是否會(huì)引起男性的誤解。從《紅樓夢(mèng)》以及《溫莎的風(fēng)流娘們》這兩部作品中可以看到女性對(duì)自我期許符合男權(quán)社會(huì)對(duì)女性的整體要求,比如中式“賢良淑德”“三重四德”以及西式的貞潔觀。在兩性關(guān)系上,兩部作品中的女性貌似處于弱勢(shì),但通過(guò)隱晦的言語(yǔ)、手段以及雙性氣質(zhì)的隱約展現(xiàn),女性對(duì)男性進(jìn)行了比較委婉的反調(diào)戲。女性對(duì)自我尊嚴(yán)、貞潔的維護(hù),是一種比較樸素的女性主義。其反調(diào)戲雖展現(xiàn)了那個(gè)時(shí)代中女性意識(shí)的初步萌芽,但也沒(méi)跳出男權(quán)社會(huì)對(duì)女性角色的約定俗成和女性在規(guī)約下的自覺(jué)尊崇。另外,曹雪芹和莎翁兩位偉大的作家,通過(guò)在其各自的作品中對(duì)女性反調(diào)戲這一行為的描述,凸顯了他們揚(yáng)善制惡的共同期許。
但兩部文本,結(jié)局大相徑庭。賈瑞照風(fēng)月寶鑒遺精死亡,福斯塔夫清醒了就當(dāng)面認(rèn)錯(cuò)。一個(gè)悲劇,一個(gè)喜劇。另外,在言語(yǔ)風(fēng)格方面,《紅樓夢(mèng)》中“毒設(shè)相思局”中的調(diào)戲與反調(diào)戲言語(yǔ)風(fēng)格壓抑陰沉,言外之意頗多。從被壓抑到扭曲的賈瑞再到心狠手辣無(wú)所不用其極的鳳姐,都有非常生動(dòng)的言語(yǔ)和心理活動(dòng)展現(xiàn)。而《溫莎的風(fēng)流娘們》里人物插科打諢,言語(yǔ)幽默輕松。二者之差異在于時(shí)代大背景的不同。曹雪芹所寫(xiě)得是從鼎盛清朝權(quán)貴,隱約顯現(xiàn)著沒(méi)落之相;而莎翁所寫(xiě)則是文藝復(fù)興時(shí)期人文主義發(fā)展所帶來(lái)的異彩紛呈的萬(wàn)象,沒(méi)落的權(quán)貴、市民階層的女性言語(yǔ)以及行為的直白都展現(xiàn)出女性主義萌芽的良性勢(shì)態(tài)。
從男性調(diào)戲的言語(yǔ)呈現(xiàn)來(lái)看,賈瑞弱冠之年,初出茅廬,從小到大受到祖父嚴(yán)格的管教,思想和精神上都受到了很大的壓抑,心理負(fù)擔(dān)重,見(jiàn)到自認(rèn)為可以調(diào)戲的對(duì)象時(shí)言語(yǔ)張狂而挑釁;而福斯塔夫五六十歲,社會(huì)經(jīng)驗(yàn)豐富,油嘴滑舌,很會(huì)為自己解嘲,富有喜劇精神。從調(diào)戲目的來(lái)看,賈瑞主要為了實(shí)現(xiàn)他內(nèi)心幻想出來(lái)的情愛(ài),而福斯塔夫則主要是謀取兩位大娘的家產(chǎn)。在女性反調(diào)戲方面,王熙鳳的雌雄同體以其男性般的狠毒為其內(nèi)在特征,以女性的八面玲瓏為其表象,以致人于死地為其目的,其整體的反調(diào)戲言語(yǔ)具有高語(yǔ)境的文化特征;而培琪大娘的反調(diào)戲則是以市民階層性格中的直白以及輕快為特征,言語(yǔ)表現(xiàn)符合人物個(gè)性設(shè)定,內(nèi)外一致,以作弄和教訓(xùn)為目的,其整體的反調(diào)戲言語(yǔ)具有低語(yǔ)境的文化特征。因此,盡管兩部作品中的男性都參與了調(diào)戲,女性都參與了反調(diào)戲,但由于兩個(gè)故事發(fā)生的歷史、文化背景以及個(gè)性差異,在言語(yǔ)出現(xiàn)中表現(xiàn)了各自不同的特征。
五、結(jié)語(yǔ)
在16至17世紀(jì)的東西方男權(quán)社會(huì)中,男性掌控話語(yǔ)權(quán),調(diào)戲女性的言語(yǔ)更顯赤裸,呈狩獵者態(tài)勢(shì);而女性言語(yǔ)委婉,明順暗反,處于一種被窺視和被狩獵的警惕狀態(tài)。在曹雪芹和莎翁的筆下,前者以小說(shuō)描寫(xiě)的方式,后者以戲劇對(duì)白的方式把被壓迫女性的抗?fàn)幰庾R(shí)用反調(diào)戲的方式一一展現(xiàn)。兩部作品,無(wú)宏大敘事,卻在男女日常的言語(yǔ)交際中展現(xiàn)了作者對(duì)所設(shè)定的女性角色的同情和幫助,也展現(xiàn)了兩位文學(xué)巨匠朦朧的女性主義意識(shí),與所處的時(shí)代則具有積極的意義。
參考文獻(xiàn)
[1]曹雪芹.紅樓夢(mèng)[M].長(zhǎng)春:時(shí)代文藝出版社,1996.
[2]陸鳴.沉睡的鳳凰——王熙鳳命運(yùn)的女性學(xué)分析與悲劇意義[J].社科縱橫,2007(02).
[3]莎士比亞.溫莎的風(fēng)流娘們[M].北京:中國(guó)青年出版社,2013.
[4]楊周翰.《莎士比亞評(píng)論匯編》(上)[M].北京:中國(guó)社會(huì)科學(xué)出版社,1979.
作者簡(jiǎn)介:劉睿璿(1997—),女,江漢大學(xué)外國(guó)語(yǔ)學(xué)院,學(xué)生;曹小雪(1976—),女,江漢大學(xué)外國(guó)語(yǔ)學(xué)院,講師,研究方向:英美文學(xué)、跨文化交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