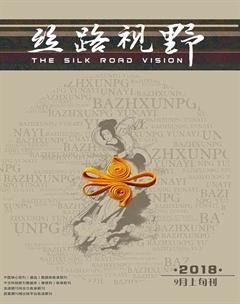愛子心無盡 情暖天山依
薛廣鵬
【摘要】歌舞劇《情暖天山》是根據2009年感動中國十大人物,青河縣72歲的維吾爾族老人阿尼帕·阿力馬洪的真實故事改編而成。作為該歌舞劇的執行導演,筆者與主創團隊在本劇籌備前期一同前去阿尼帕媽媽家中探望老人,深度了解了她與子女們的生活,以便以藝術的眼光更好、更真實地在舞臺上呈現這部歌舞劇。
【關鍵詞】歌舞劇;歌舞劇《情暖天山》;創作談
一、冬日暖情
雖然早在采風前,我們早已被她的故事有所感動,而當見到阿尼帕老媽媽本人,尤其是她用慈祥和藹、始終面帶安詳的笑容望著我們,娓娓為我們講述著往事時,筆者更覺得感動由心而生,同時阿尼帕媽媽的舞臺形象也更加清晰地在腦海中勾勒出來了……阿尼帕老媽媽收養孩子的故事要追溯到20世紀60年代,她不忍看父母雙亡的孤兒們忍饑挨餓,在物質條件極端匱乏的環境下毅然收養了幾個孩子,就此拉開了這段橫跨一生的感人故事的帷幕。20世紀70年代,阿尼帕老媽媽收養了漢族孩子王淑珍兄妹四人(王淑珍就是《情暖天山》中王小珍的人物原型)。至今令王淑珍難忘的是阿尼帕媽媽收養自己的那個寒冷冬日,她的頭上長滿凍瘡和癬,不再生發。阿尼帕帶著她求醫問藥,在媽媽的悉心呵護和治療下,她的頭發兩個月后又重新長出來了。王淑珍至今留著烏黑的長發,把它當做是媽媽給她的最寶貴禮物禮物……最令筆者動容的是阿尼帕媽媽聊到過去的艱苦歲月時告訴我們,哪怕是在寒冷的冬天,她仍然早早起床,在天山腳下將封凍的河面敲碎,赤手用冰冷刺骨的冷水清洗羊腸子等拿去賣,以此貼補家用以及供孩子們吃穿和上學;在缺衣短食的歲月,衣服從大孩子到小孩子依次傳著穿,補補貼貼直到破舊不堪而丟棄;在不大的破土平房內,十幾個孩子們擠在一張以麥草為墊,以舊氈做褥的大炕上;然而,最讓阿尼帕媽媽發愁的還是一家人的“糧食問題”。她專門買來的1.2米的大鐵鍋可以為一家人做飯,但這口被孩子們溫暖地稱為“團圓鍋”的大鍋里的飯,卻也總是分著分著就見了底兒……
筆者被這些往事深深感動著,它們看似為波瀾不驚的生活瑣事,但卻串聯起了一個不屈不撓、始終如一的偉大母親的形象。然而筆者更覺這種“愛”早已經超過通常意義的“母愛”范疇了,它是超越民族的所傳遞的人間至愛和溫暖善良的人性。阿尼帕老媽媽的19個孩子中,只有9個為親生兒女,另外10個均是她收養的孤兒,并涵蓋了6個民族。阿尼帕媽媽是靠著怎么樣的堅毅樂觀和大愛無邊的品格,才能讓這些孩子們有衣穿、有飯吃?正是有這樣的好媽媽,孤兒的心里永遠找到了庇護港和依靠。這些故事在“小家”的“小愛”中,卻完成了民族和諧共榮的偉大事業。這樣的精神才是這部歌舞劇的靈魂,筆者希望能通過演職人員的共同努力,把真情傳遞給全國觀眾,把新疆各民族互幫互助、團結友愛的精神面貌傳遞給全國。當然,好的故事和劇本也需要好的演員來詮釋,我們的演出的陣容也十分強大:有世界著名花腔女高音歌唱家迪里拜爾、西域情歌王子艾爾肯·阿不都拉、中國東方演藝集團青年演員喻越越等。除此之外,還有新疆藝術劇院歌劇團、新疆藝術劇院歌舞團、新疆木卡姆藝術團、新疆藝術學院以及晨報藝術團的眾多專業和敬業的演員們聯袂演出。
二、時空交錯
歌舞劇《情暖天山》中,以阿尼帕媽媽為原型的人物,在劇中叫做帕麗達。劇中帕麗達共有7位兒女。其中重點刻畫了三位人物:母親帕麗達、大兒子吐爾洪(帕麗達的親生骨肉)、老七王小珍。除這三位人物外,老六艾克拜爾的形象設置比較有特點,他扮演著吟游詩人般的角色———自由地游離于劇情內外,通過吉他彈唱吟誦母親與幾個孩子之間的濃濃親情,從而加深該劇的抒情性。劇中擇取的情節看似平淡無奇,卻處處充滿著暖暖的真情,以“小愛”彰顯“大愛”是我們的主要構思。筆者力求在100分鐘的舞臺表演中,以不同人物的視角豐富總體的視野,也力求為觀眾打開更多的視覺窗口。所以在該劇整體的結構設置中,我們選擇以一明一暗、時空交錯的兩條線索共同構筑《情暖天山》的敘事技巧。該劇的形式和內容結合緊密:在形式上推進了情節的轉變與發展,而在內容上則升華了“家”的主旨立意。兩條時空線索中,一條線是長大成人的“當下”,通過母親得病為線索作為故事開始的契機;另一條線是孩童時期的“曾經”,以7個孩子回憶的視角不斷地深入敘事。筆者認為《情暖天山》最具有創造性的結構方式是在其中某些場景的表現上,打破了傳統的時空觀,將“過去”與“當下”同時表現舞臺上。作為劇,必然涉及戲劇沖突,但這部歌舞劇的特別之處就在于,劇中種種矛盾的沖突最終全部消融在“愛”的崇高中了。首先,故事發生的背景就與現實存在著巨大的“矛盾”:在物質條件極其匱乏與不斷地收養孩子之間的矛盾中,舞劇所有的矛盾都在這個大的矛盾背景中得以展示。其次,在家庭中存在著處處矛盾,正是這些矛盾,烘托出“愛”的偉大。接下來我以幾處具體的情節為例來解釋如何將“矛盾在愛的升華中消融”:
在“當下”這條線索中矛盾沖突是:帕麗達媽媽患病,孩子們都趕回家中,希望自己的血液可以匹配成功使媽媽得救。化解矛盾的方式是,最后大兒子的血匹配成功,媽媽獲救。我們虛構出這一矛盾沖突,便是為了給“過去”這一條線索的故事情節以邏輯的合理性———七個孩子在等待學院結果匹配的時候,回憶起了與母親的點點滴滴。在時間軸“過去”的線索(同時也是這部歌舞劇的主要線索)中,我們選取了幾段最為感人肺腑的故事進行改編和表現。如上文提到的作為本劇核心的沖突之一是老大吐爾洪和老七王小珍同時拿到錄取通知書。媽媽選擇老七外出上學,意味著失信于丈夫臨終前的囑托;而讓老大出去,又辜負了自己對老七的承諾。在這樣的矛盾中,帕麗達還是選擇了讓養女上學、讓親生兒子在家牧羊的艱難抉擇。隨后,老大因不解而將矛盾沖突推向高潮———吐爾洪被圍困在暴風雪來襲的天山。最后,帕麗達不顧安危冒著生命危險找回兒子……以及上文提到老七回憶起帕麗達收養自己的那一個冬夜的故事等等……不難看出,所有矛盾沖突的化解最終全部是以媽媽“溫暖的親情”為手段,從而升華了母愛的偉大,這便是這部舞劇在結構上的最大特點矛盾。當然,矛盾最終能夠升華為愛,實質上需要一個層層遞進的漫長過程,在歌舞劇呈現的100分鐘內,能以人物間共同的命運、不同的立場和由此所形成的共同的愛來構造是極具難度的。我們通過情節和人物的深入刻畫,使得人物性格和行為的矛盾逐漸形成,從而也就造成了故事情節的張力。母親在暴雪中尋找兒子的急迫,兒子長大后理解媽媽的大愛無私,養女婚禮前母親的萬般叮囑和不舍……當這一切在時空交錯中展現于舞臺時,將該劇的力度彰顯出來。我們不難感受到,在經歷了困苦艱難后,該劇內在的氣氛卻依然溫情平緩。之所以這種張弛有度的敘述能夠互相契合,正是因為矛盾沖突一經出現,就立即自然而然轉換為平靜溫情的狀態。矛盾之所以轉換,其一是因為母愛的升華,其二是新疆音樂舞蹈在劇中的凈化人心的作用。在愛的升華和音樂舞蹈凈化的表達中,矛盾的出現和轉化在解決中產生了張力,同時也讓故事緊湊且富有節奏感,情感層層遞進。
三、豐富多彩,燦若明珠
載歌載舞的新疆,其歌舞劇自然也要求在敘述故事的同時盡可能多地尋找“可舞性”和增加“視聽效果”。首先,本劇的舞臺設置是一大亮點。我們將舞臺的地面設計成為寬25米、高11米、傾斜7度的巨型地毯,這個地毯時而是掀起的地毯一角,從這一角向遠方不斷延伸著,與背景的“天空”融為一體。地毯不僅具有新疆的地域特色同時也利用它的視覺效果體現出新疆幅員遼闊的美好風光。正如邢導所說:“地毯”是整部劇的視覺核心,用燈光投影在白色地毯上勾勒出各種圖案,這些就變成了新疆各族群眾日常生活中最常見的元素。”隨著場景的不斷轉換,地毯時而是宴會廳的中央的巨大地毯,花團錦簇,賓客迎來送往;時而是平坦的賽馬場,駿馬奔騰,英姿颯爽;時而又是雪域高原的壯美天山,疾風驟雪,茫茫無邊。就“可舞性”而言,筆者進行舞蹈編排時力求使舞蹈場景與故事情節融為一體,同時為了突出這個大家庭的多民族性,所以在音樂于舞蹈的創作上,也建立在新疆多元文化基礎上,并不限定于新疆某個民族或地區的特定舞蹈、音樂語言,而強調了新疆整體的藝術特性。
在尋找“可舞性”的故事情節中,《情暖天山》著重選擇了以下幾個舞段來營造氛圍:開場熱鬧的木卡姆歌舞和結尾歡快的維吾爾族婚禮歌舞、圍著鍋爐和夜晚睡覺的生活片段舞、婀娜多姿的辮子舞、氣勢磅礴的賽馬舞以及具有象征寓意的暴風雪舞等,它們都與劇情緊密結合。如圍著鍋爐和夜晚睡覺的這段日常生活舞蹈,在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生活舞蹈表達中,筆者力圖傳遞真摯得不能再真摯的暖暖親情。當蒙著眼睛玩做游戲的孩子們笑得天真無邪,媽媽的一聲“吃飯啦”讓孩子們都迫不及待地沖進屋中,孩子們圍著那口直徑1.2米的“團圓鍋”,一個個舉起碗,排好隊等著媽媽盛飯。物質的極端匱乏,精神的高度飽滿是通過吃完飯的孩子們又一個個舔干凈碗;老大回來飯不夠加點水湊合吃等細節展現出來。孩子們吃完飯把碗頂在頭上玩耍,吃完飯很自然地銜接夜晚睡覺的片段,7個孩子擠在一張大床上的舞蹈。我利用了一個大棉被將7個人牽連在一起,7人站在床上藏在被子后面以小碎步圍成一個圈,被子中裹著的7個人樂作一團……生活雖然萬分艱難和貧寒,穿著破衣爛衫、永遠吃不飽的飯和擁擠的炕……這等等一切的生活艱苦卻在歡聲笑語中變成十分寶貴的財富,直到現在這些溫馨的場面依舊是阿尼帕老媽媽樂此不疲想要去分享給我們的往事。
劇中的哈薩克“賽馬舞”表現了大哥勇猛果敢和新疆的游牧民族銳不可擋的生命力。在這段舞蹈中,為了表現老大在賽馬過程中的颯爽英姿,筆者運用哈薩克族賽馬舞種“黑走馬”的典型姿態,配合以哈薩克族舞蹈音樂“黑走馬”的節奏特征,進行變化和發展。舞者身體重心下降,上身保持直立的同時,讓雙腿前后交叉并曲膝,隨著馬的馳騁,舞者變化著身體的姿態。舞者舉著皮鞭,運用前后動肩和扭臂的姿勢,表現賽馬時的奔騰狀態。在舞蹈的高潮處,適當地增加了技巧性動作表現賽馬的激烈,并且把歌舞劇帶向了一個小高潮。舞者像斜跨在馬背上的青年一樣,前胸直挺、雙肩大幅扭動、翻腕用勁,描寫出少數民族慶祝節日一派歡騰、熱烈的氣氛。而到了表現吐爾洪和母親因為上學的事情而產生意見而發生矛盾這一劇情時,筆者以“擬人化”的舞蹈作為表現手法來表現天山的暴風雪。眾男舞者們身著白衣,腳穿銀靴,圍著白色的大披風,首先從形態上模擬“風雪”。同時,男性充滿力量感的動作強化了暴風雪的兇猛,身上的白色披風在男舞者們有力的舞動過程中遇風而鼓起,在視覺上延擴了舞者體積,如同一股股裹挾著冰碴的漫天風雪。一次烘托出惡劣的環境下,大兒子暈倒在雪中的危在旦夕,以及阿尼帕媽媽不顧安危,保護兒子的感人場景。在這樣的鋪陳中,當阿尼帕媽媽的歌聲“我的兒子啊/從小那樣懂事/小小的雙手分擔家的重擔/我的兒子啊/你是那樣堅強/小小的肩膀承擔起家的重擔”響起,無人不會落下眼淚來……再例如當王小珍被媽媽領養,并且通過帕麗達媽媽的悉心關照,她的頭發又長出來了。伴隨著小珍高興地說:“媽媽,你看!我的長辮子”時,緊接著一群靚麗的維吾爾族少女留著一頭長長的辮子舞起《辮子舞》,與劇情銜接自然。一群身穿天藍色艾德萊絲長裙的維吾爾族姑娘,和著悠揚的歌聲,婀娜多姿地款款上臺。她們頭上又黑又長的大辮子,如一道靚麗的風景線,淺淺微笑,楚楚動人,優雅漫步形成的長長列隊,維吾爾族女子舞蹈原本就深受觀眾喜愛,此時加入這一情節后,不僅與劇情貼近,也彰顯了地域風俗。舞蹈主要的動作設計是姑娘們輕輕撫摸和拎著心愛美麗的辮子,昂首優雅地轉身,身后飄蕩烏黑發亮的長發裝著她們心中美好的回憶和甜美情愫。一切藝術形式都是為情感服務,結構為情所思,人物為情所塑,故事為情而立,最終達到契合,從而讓觀眾感動和震憾。
除舞蹈外,劇中的老六艾克拜爾的彈唱也是本舞劇特點之一。他主要彈唱四段樂曲分別是:《我們的家好大》《走過歲月》《苦澀》《歲月是流淌的河》。第一首是《我們的家好大》,在歌詞“我們家好大/眼睛有黑有藍/也有黃啊/我們家好大/張張嘴/說出不一樣的話”中,介紹了帕麗達收養不同民族的孩子的背景;第二首《家園》,至此拉開了主線“倒敘”的帷幕;第三首是在大哥和老七回憶起媽媽艱難的上學抉擇時,艾克拜爾唱了一首《苦澀》以彈唱的抒情手段來深化媽媽的兩難和心痛:“……選擇是苦澀的痛/大哥妹妹都希望踏進命運的大門……愛的媽媽需要吞下太多的苦痛/媽媽親愛的媽媽你讓誰擁抱希望……”最后一首是在第三幕,他彈唱了一首《歲月是條流淌的河》,開啟王小珍的回憶……西域情歌王子艾爾肯·阿布都拉的聲音曠遠清冽,深情悠長,且極具地域風格,歌聲似穿越時空將我們帶回遙遠的過去。由于前文所述的多時空交錯結構,《情暖天山》的音樂也配合劇情設置而貫通古今。它并不是過去傳統意義的歌舞劇,它包含著傳統的十二木卡姆同時卻也融合著流行的吉他彈唱。在傳統民間音樂與現代流行音樂的結合中,音樂更加多元,配器在突出新疆民族器樂風格的同時要“交響化”、“時尚化”,也從中體現出新疆逐漸的變化和發展,具有時代性。同時在人物角色的聲音選擇上,也有所區分和不同,不僅體現了多元,也體現出了人物與聲音的匹配。母親選用美聲唱法,突出端莊高貴的感覺;女兒王小珍是通俗歌曲風格,流行時尚、旋律動聽而深情;老六艾克拜爾則是民謠風格,以通俗歌手的方式演繹新疆風格歌曲,并且將《情暖天山》的音樂融合于戲劇發展的情境之中。
四、結語
《情暖天山》的主創團隊希望不論是從藝術形式抑或是思想內涵等方面都承載著藝術創作的“新意”。就藝術形式方面,結合上文所言,這部歌舞劇對于新疆多民族具有深厚歷史的音樂和舞蹈進行了集成式的創新。傳統十二木卡姆基礎上結合了現代音樂,同時在傳統舞蹈的基礎上進行了具有現代性的編創,這些都淋漓盡致地展現了善良淳樸、熱情好客的新疆各族人民的文化藝術。《情暖天山》的音樂和舞蹈創作在于立足于國際化的視野。在交響樂與合唱為主要配器的方式下,結合故事情節對傳統舞蹈進行改編創作。在不同唱段、舞段中,根據場景、情節的不同需要運用現代性的音樂、舞蹈創作,展示出了新疆的新面貌。
就思想內涵方面而言,該劇也力求有所創新。在突出對人的心靈美、人性美的弘揚中,在生活困境和矛盾沖突中,體現“愛”的宏大敘事。2012年11月習近平總書記首次闡釋“中國夢”的概念。這部歌舞劇作品的內容故事正是“中國夢”的詮釋方式之一。在舞臺人物形象的構思中,帕麗達媽媽樂觀堅強、充滿活力和希望的形象通過子女的視角,以及具體故事一層層地展現出來。帕麗達堅毅而又樂觀地對待生活中的困難與不幸,正是向觀眾們表達了一種正確的人生態度,也契合了“中國夢”的思想。尤其是帕麗達媽媽收養了多名孤兒,犧牲和奉獻了自己的一生。她構筑的6個民族的小家庭,正是中國56個民族是一家的縮影。我們所塑造的這位熱愛家庭、熱愛祖國的帕麗達媽媽與我們一直所強調的“中國夢”精神是具有統一性的。國家之富強、民族之振興以及人民之幸福,離不開像歌舞劇的原型帕麗達媽媽一樣的愛國主義者和民族團結的典范。她用高尚的精神鼓舞了觀眾們的愛國主義精神,重塑了關于“國家”與“人生”的價值觀!
參考文獻
[1]趙大鳴.“大歌舞”時代的舞劇創作[J].舞蹈,2001(4):13~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