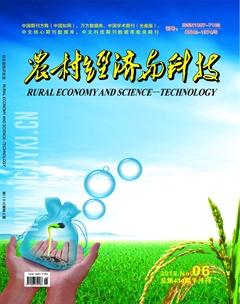重慶市產業結構合理化、高度化與城鎮化關系分析
李星林
[摘 要]文章選取1997-2015年重慶市數據,對產業結構與城鎮化的關系進行實證檢驗。結果顯示:重慶市產業結構合理化、高度化與城鎮化之間存在長期穩定關系;城鎮化是產業結構合理化和高度化的格蘭杰原因,但城鎮化對產業結構合理化存在一定的滯后抑制作用,對產業結構高度化具有一定滯后推動作用;產業結構合理化和高度化不是城鎮化的格蘭杰原因。由此說明產業結構合理化和高度化沒有與城鎮化之間建立良好促進作用;城鎮化發展對產業結構合理化在短期過程中具有一定的反向作用,在長期反向作用并不明顯;城鎮化對產業結構高度化在長期過程中有穩定推動作用。基于研究結論,最后提出了促進產業結構合理化、高度化與城鎮化協調發展的對策建議。
[關鍵詞]產業結構合理化;產業結構高度化;城鎮化
[中圖分類號]F121.3 [文獻標識碼]A
1 引言
產業結構優化和城鎮化發展都是我國發展戰略中要努力實現的主要目標。重慶市作為長江上游經濟中心、西部重要增長極、城鄉統籌直轄市、國家中心城市、“一帶一路”發展中心樞紐,從1997年直轄至2015年底,地區生產總值快速增加,三次產業結構由“二、三、一”發展成“三、二、一”,城鎮化水平也快速提升,在產業結構和城鎮化方面均有顯著發展。因此,本文以重慶市為例,研究產業結構合理化、高度化與城鎮化之間的關系,科學合理地看待產業結構與城鎮化之間的相互關系,為重慶市及其他地區未來產業結構調整、城鎮化發展提供科學參考依據。
2 實證分析
2.1 指標選取和數據來源
本文以于春暉教授(2009)所用方法來量化產業結構合理化,反映三大產業的協調性和耦合質量,用X1表示;以學術界常用的第三、第二產業增加值比值量化產業結構高度化,反映經濟結構中服務化傾向水平,用X2表示;以常住人口城鎮化率解釋城鎮化發展水平,用CZH表示。其中產業結構合理化和高度化指標計算公式如下:
上述公式中,t表示年份,Y j/Y表示第j產業增加值比重,L j/L表示第j產業就業人員比重,Y3t/Y2t表示第t年的第三產業增加值與第二產業增加值比重。X1t表示第t年的產業結構合理化程度,產業結構合理化指數越小,合理化程度越高,反之亦然;X2t表示第t年的產業結構高級化程度,指數越大,高級化程度越高。本文數據來源于《重慶市統計年鑒2015》和Excel計算所得。
2.2 單位根檢驗
為了避免非平穩數據直接回歸造成“偽回歸”出現,先對變量進行平穩性檢驗。對時間序列指標CZH(城鎮化率水平)、X1(產業結構合理化水平)、X2(產業結構高度化水平)進行單位根檢驗,檢驗結果顯示,CZH、X1、X2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通過檢驗,均為1階單整平穩序列。
2.3 協整檢驗
CZH、X1、X2時間序列是平穩序列,滿足協整檢驗要求。因此本文分別對CZH和X1、CZH和X2進行Johamson協整檢驗。在檢驗之前,基于協整檢驗要求,本文首先建立CZH和X1、CZH和X2的VAR模型。模型建立如下:
公式(3)、(4)為VAR方程,式中aijn(n=1,2,3,4,5,…,p)、bijn(n=1,2,3,4,5,…,p)為方程系數,p為滯后階數,ξt、μt、γt、ωt為方程的殘差項。建立好VAR模型后,利用赤池信息準則(SIC)、施瓦茨(SC)、似然比檢驗統計量(LR)等指標確定VAR模型合適的滯后階數P。通過eview檢驗計算得出CZH和X1的VAR模型的合適滯后階數為2,即建立VAR(2)模型;CZH和X2的VAR模型的合適滯后階數4,即建立VAR(4)模型。當自回歸模型VAR是穩定的,模型所得結論才有效,因此本文對CZH和X1建立的VAR(2)進行穩定性檢驗,對CZH和X2建立的VAR(4)進行穩定性檢驗。檢驗結果顯示,AR單位根倒數的模均小于1,說明模型VAR(2)和VAR(4)是穩定的,可進行協整檢驗。
基于上述分析,對CZH和X1、CZH和X2分別進行Johamson協整檢驗。檢驗結果顯示:一方面,CZH和X1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存在協整關系,表明重慶市城鎮化與產業結構合理化之間存在長期穩定關系;另一方面,CZH和X2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存在協整關系,表明重慶市城鎮化與產業結構高度化之間存在長期穩定關系。
2.4 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
CZH與RAT、CZH與X2存在協整關系,滿足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通過Eviews軟件進行格蘭杰因果檢驗,其檢驗結果顯示:CZH是X1的格蘭杰原因,而X1不是CZH的格蘭杰原因(如表1所示);CZH是X2的格蘭杰原因,而X2不是CZH的格蘭杰原因(如表2所示)。檢驗結果表明:城鎮化對產業結構合理化和產業結構高度化存在滯后作用,反之則不成立。
2.5 脈沖響應分析
為了更好地了解重慶市CZH對X1和X2的滯后作用的影響方向和作用效果,本文將利用脈沖響應函數來分析CZH的一個沖擊對X1和X2影響的方向和效果。
圖1表示在施加CZH單位標準差沖擊下,X1的變化情況。其中,橫軸表示沖擊作用的滯后期間數,縱軸表示單位沖擊引起X1的變化率(引起產業結構合理化的變化率),實線代表脈沖響應函數,虛線代表正負兩倍標準差偏離帶。從圖1顯示結果可知,CZH(城鎮水平)對X1(產業結構合理化水平)的沖擊具有反向作用,并且圖中實線和虛線顯示CZH沖擊對X1滯后第1期與第2期之間的反向作用最大,滯后期在第1.5年時CZH對X1的沖擊抑制作用最大,約為-0.007單位,隨后這種抑制作用開始減弱,到滯后第5期時CZH對X1的抑制作用變化逐漸穩定并趨于0。由分析可知,從短期來看,重慶城鎮化化水平的提高對產業結構合理化水平的提高并沒有產生推動作用,相反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產業結構合理化水平的降低。
圖2表示在施加CZH單位標準差沖擊下,X2的變化情況。其中,橫軸表示沖擊作用的滯后期間數,縱軸表示單位沖擊引起的X2的變化率(引起的產業結構高度化的變化率),實線代表脈沖響應函數,虛線代表正負兩倍標準差偏離帶。從圖中顯示結果可知,CZH(城鎮化水平)對X2(產業結構高度化水平)在滯后期前4期內是抑制作用,并且在第3期時,這種抑制作用達到最大,從第5期開始具有促進作用,在第7期時促進作用達到最大,滯后第9期時CZH對X2具有穩定的推動作用。因此,從短期來看,城鎮化水平的提高并沒有促進產業結構高度化水平的提高;但是從長期來看,城鎮化水平的提高對產業結構高度化水平的提高具有促進作用并且隨著時間的延長趨于穩定。
3 研究結論
第一,重慶市城鎮化水平與產業結構合理化、高度化水平之間存在著長期穩定關系。從VAR模型檢驗可知,重慶市城鎮化與產業結構之間在短期并不穩定,但在不同滯后期的協整檢驗結果來看,兩者在長期存在穩定關系。本文認為,存在這種關系的原因是:在短期,城鎮常住人口快速增加,會不斷刺激消費,但就業卻并不能及時得到全部解決,超前消費嚴重,資本要素積累減少,“城市病”涌現,不能給產業結構發展帶來直接貢獻,反而因為這種提前消耗積累且存在滯后效應的城鎮化發展阻礙著產業結構的合理化、高度化提升;在長期,城鎮化水平提高所帶來的城鎮勞動力增加,以及城鎮基礎設施優化、規模效應和集聚效應增強等正效應凸顯,推動城鎮二、三產業發展,促進產業結構向更高水平的合理化、高度化邁進,進一步提升產業結構優化程度。
第二,重慶市城鎮化水平與產業結構合理化、高度化之間是單向的格蘭杰因果關系。從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結果可知,在滯后2期時,重慶市城鎮化發展是產業結構合理化的原因;在滯后4期時,重慶市城鎮化發展是產業結構高度化的原因,反過來則兩者均不成立。這表明,在重慶市快速發展進程中,城鎮化的發展是單方面直接或間接影響產業結構合理化和高度化的發展,這與經濟發展理論中產業結構和城鎮化相互促進觀點相悖。本文認為,出現這種結果的原因是:一方面,重慶市直轄后快速發展,鼓勵農民轉戶進城,擴張城市,招商引資,大力發展三大產業,創造就業機會,提供就業培訓,鼓勵自主創業,不斷吸收轉戶人口,這一系列鼓勵措施不僅促進了重慶市城鎮化水平的提高,也通過城鎮化水平的提高推動了產業結構的發展;另一方面重慶市近年來城市發展迅速,來重慶就業的市內、市外農民工數量不斷增加,大量從事建筑業、服務業、工業等,產業結構變化明顯,但受傳統城鄉二元結構的戶籍制度、土地制度、城鄉社保制度、城市生活成本、城市落戶門檻等限制,農民工中真正轉戶為城鎮人口的并不多,這就導致產業結構雖然發生變化,就業人口不斷增加,但其對城鎮化的影響卻被屏蔽,表現并不明顯。重慶市城鎮化發展與產業結構之間還未形成良性互動關系,有待改善。
第三,重慶市城鎮化對產業結構合理化無明顯推動作用,對產業結構高度化在長期過程中有穩定推動作用。本文認為,存在這種情況的原因為:重慶市以前是以重工業為主的城市,但是近年來在第三產業、房地產等方面發展迅速,重工業(如重慶鋼鐵)發展每況日下,產業發展傾斜,所以在城鎮化水平不斷提高時也未能及時推動產業結構合理化水平的提高,但因城鎮化發展在長期中促進第三、二產業發展和重慶產業發展傾斜,推動著重慶市產業結構高度化水平在長期中得到提升。
4 政策建議
基于實證和結論分析,本文對重慶市未來城鎮化和產業結構發展提出以下建議:第一,城鎮化是產業結構合理化和高度化的原因,因此重慶市應充分運用好這一關系,不斷推進城鎮化發展。但是,重慶市在提升城鎮化發展水平時,要改變傳統的量變特征,進一步實現質變,即從單純的擴增城鎮人口數量和擴張城市規模,向實現農業人口“能轉戶、搬得出、穩得住”邁進,將轉戶人口吸收到產業發展中,尤其是第二、三產業,強化城鎮化發展對產業結構的作用,促進產業結構調整。第二,招商引資,引進先進技術,加快三大產業現代化、信息化發展步伐,大力發展二、三產業,創造更多就業機會,給予就業者尤其是大學畢業生、農民工等更多的職業技能培訓,提升就業率,進一步改善重慶市產業結構,同時改善城鎮基礎設施和居住環境,吸引更多外來人口留在重慶,促進產業結構提升與城鎮化發展之間形成良性互動。第三,打破城鄉二元結構的限制,改革農村土地制度、城鄉戶籍制度、城鄉社保制度,促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推進城鄉統籌、產城融合發展進程,在實現重慶市城鎮化與產業結構協調發展的同時,最終實現重慶市整體社會經濟健康、和諧、可持續發展。
[參考文獻]
[1] 徐傳諶,謝地.等.產業經濟學[M].北京:科學出版社,2007.
[2] 山田浩之.城市經濟學[M].大連:東北財經大學出版社,1991.
[3] 孫葉飛,夏青,周敏.新型城鎮化發展與產業結構變遷的經濟增長效應[J].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16(11).
[4] 李長亮.中國省域新型城鎮化影響因素的空間計量分析[J].經濟問題,2015(05).
[5] 李鐵立,李誠固.區域產業結構演變的城市化響應及反饋機制[J].城市問題,2003(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