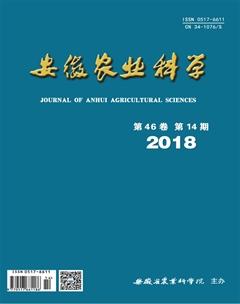羊肚菌種屬鑒定及活性成分保健功效研究進展
敬華英
摘要 羊肚菌是一種美味食用菌,同時也是一種珍稀藥用菌。世界范圍內對羊肚菌的系統發育、人工栽培及功效研究較多。從羊肚菌種屬鑒定和保健功效入手,對新近的研究成果進行了綜述,總結了羊肚菌研究中取得的主要成績,并對存在的問題及應用前景進行了探討。
關鍵詞 羊肚菌;種屬鑒定;保健功效
中圖分類號 S646.7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517-6611(2018)14-0034-03
The Research Progress of Species Identification of Morels and Health Efficacy of Active Ingredients
JING Huaying (Agricultural and Pastoral Bureau of Xichong County,Sichuan Province,Xichong,Sichuan 637200)
Abstract Morels (Morchella spp., Ascomycota) are a highly desired group of edible fungi with a worldwide distribution. They were appreciated for their flavour, medicinal and nutritional properties. There were extensive studies on the phylogeny, artificial cultivation and efficacy of morels in the world. We reviewed recent research progresses of species identification and health efficacy of the fungi, also discussed the potential issues remaining in the current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prospects.
Key words Morels;Species identification;Health efficacy
羊肚菌(Morchella spp.),俗稱苞谷菌、羊肚菜、陽雀菌,隸屬子囊菌門(Ascomycota)、盤菌亞門(Pezizomycotina)、盤菌綱(Pezizomycetes)、盤菌目(Pezizales)、羊肚菌科(Morchellaceae),其菌蓋多有褶皺,似羊肚狀凹陷,故名羊肚菌[1]。羊肚菌味道鮮美,營養豐富,是享譽世界的美味食用菌和珍稀藥用菌。我國對羊肚菌的記載最早見于《本草綱目》[2],其菜部蘑菰蕈綱目記載:一種狀如羊肚,有蜂窠眼者,名羊肚菜。道家文化巨獻《道藏》、明代菌物專著《廣菌譜》、清末民初的烹飪專著《素食說略》等文獻皆載羊肚菌食藥用功效,現代本草專著《中華本草》[3]及《新華本草綱要》對羊肚菌藥理作用有詳細論述。
上百年來,人們從記載、采食羊肚菌逐步深入到研究其地理分布、系統發育、人工栽培、化學成分及保健功效等方面,取得了突破性進展。同時,作為一種子囊菌,有關羊肚菌的許多科學問題都有待進一步研究。其中,準確的種屬鑒定,多種保健功效的作用機制等問題,既具有相當的科學價值,又能為進一步利用羊肚菌做出貢獻。筆者擬從羊肚菌的種屬鑒定及保健功效研究2方面進行綜述,為羊肚菌的深入研究提供資料。
1 羊肚菌種屬鑒定
1.1 羊肚菌形態分類
真菌索引數據庫 (http://www.indexfungorum.org/Names/Names.asp) 中,有關羊肚菌的記錄并分類定名共有332條,其中既包含了早期通過形態學完成的分類,也包括基于分子生物學的現代分類命名。美國國家生物技術信息中心(National Center of Biotechnology Information, NCBI)中,有關羊肚菌ITS (internal transcribed spacer)序列的記錄共有4 453條。羊肚菌多基因序列模標數據庫Morchella MLST (Multilocus Sequence Typing,http://www.cbs.knaw.nl/morchella/) 中系統地記錄了羊肚菌屬真菌ITS、LSU、EF1-α、RPB1及RPB2的詳盡序列,涉及多基因系譜一致性系統發育種識別法 (genealogical concordance phylogenetic speciesrecognition, GCPSR) 所需要的全部相關序列。由此可見,羊肚菌的系統發育研究較為深入,在全世界范圍內都是一個熱點問題。
根據羊肚菌菌蓋顏色,棱紋走向,菌蓋凹陷大小及形狀,菌蓋近中部與菌柄是否分離等特征,將羊肚菌分為黑色羊肚菌類 (Black Morel Group)、黃色羊肚菌類 (Yellow Morel Group)、變紅羊肚菌類 (Redbrown Morel Group) 及半開羊肚菌類群 (Halffree Morel Group)共4個形態分類單元[4]。《中國蕈菌》中記載我國已知的羊肚菌屬菌物有10個種,即尖頂羊肚菌(Morchella conlca Boudier)、肋脈羊肚菌(M. costata Pers.)、黑脈羊肚菌(M. angusticeps Boudier)、褐赭色羊肚菌(M. umbrina Boud.)、高羊肚菌(M. elata Boudier)、羊肚菌(M. esculenta Pers.)、粗柄羊肚菌(M. crassipes Boudier)、小羊肚菌(M. Deliciosa Jet)、開裂羊肚菌(M. diatans Boudier)和寬圓羊肚菌(M. robusta Pers.)。吳興亮等[5]在《中國藥用真菌》中描述了我國的7種羊肚菌,即黑脈羊肚菌、尖頂羊肚菌、粗柄羊肚菌、羊肚菌、庭院羊肚菌(M. hortensis Boudier)、高羊肚菌、普通羊肚菌(M.vulgaris Boudier),其中庭院羊肚菌和普通羊肚菌為新增種類。
隨著研究深入,相關學者引入了更多的分類指標,完善了羊肚菌的形態分類。作為一種子囊菌,羊肚菌子囊呈豆莢狀,1個子囊中包含8個子囊孢子,子囊孢子卵圓形。同時,羊肚菌基內菌絲與氣生菌絲形態,孢子印顏色,菌核形成時間及形態等,都可以輔助進行羊肚菌的形態學分類。
1.2 羊肚菌分子鑒定
1.2.1 DNA序列分析技術。隨著分子生物學的發展,相關學者開發出一種基于測序技術的分子標記技術,稱為DNA序列分析技術。真菌間的遺傳及親緣關系能夠在DNA序列上獲得更直接、客觀的反映,基于此,DNA序列分析技術成為現階段真菌分類鑒定中最常用的方法之一[6]。
現在的研究結果顯示,羊肚菌的ITS序列可以分為2類,一類ITS序列較長 (1 098~1 172 bp),包括普通羊肚菌和粗柄羊肚菌等;另一類ITS序列較短 (698~702 bp),包括黑脈羊肚菌和肋脈羊肚菌等。這2類羊肚菌依次對應形態學分類中的黃色羊肚菌類及黑色羊肚菌類[7]。通過ITS序列分析不同羊肚菌種的遺傳距離,發現變紅羊肚菌距黃色羊肚菌類及黑色羊肚菌類遺傳距離較近,而半開羊肚菌具有較遠的遺傳距離。進一步研究發現,在形態學上的黑色羊肚菌和黃色羊肚菌雖然可以通過ITS序列準確區分,但它們之間存在過渡類群。形態分類中的變紅羊肚菌和半開羊肚菌依舊需要進一步區分。由于PCR反應具有一定的偏好性,加之試驗方法的差異導致結果存在誤差,因此測序結果對序列真實性的反映有限[8-9]。此外,同種真菌其ITS允許多大的差異有待研究,這就使得基于ITS序列完成的羊肚菌系統發育研究的認可度不高[10-12]。
1.2.2 多基因聯合分析技術。羊肚菌起源較早,經歷的地質條件的改變較多,因此,聚集在某一區域的羊肚菌,種間的差異并不大,可供利用的分子標記位點也不多。相關學者在分子生物學上進行了大量試驗研究,但是仍然存在較多的問題。NCBI中有關羊肚菌ITS序列的定名錯誤率達66%,同物異名、異物同名現象非常嚴重[13-14]。因此,菌物學家通過整合多個位點的DNA片段獲得更多的遺傳信息,從而有效減少單一位點的隨機性變化,開發出多基因聯合矩陣的方法,應用該方法,羊肚菌屬真菌的系統發育得到了更系統、更準確的研究。
ODonnell等[15]應用多基因聯合分析技術對收集自全球范圍的約600個羊肚菌樣品進行系統發育分析。研究發現,試驗樣品能夠聚集在單系群,進一步發現羊肚菌屬包括黑色羊肚菌類群 (Elata Clade) 和黃色羊肚菌類群 (Esculenta Clade),其中黃色羊肚菌類群包括15種,黑色羊肚菌類群包括13種,全球總計共28種羊肚菌。ODonnell等[7]基于LSU、EFl-a、RPB1和RPB2共4個基因片段進行多基因聯合矩陣分析,研究發現羊肚菌屬真菌可劃分為黑色羊肚菌支系、黃色羊肚菌支系和變紅羊肚菌支系 (Rufobrunnea Clade),分別包括32、16和1個物種。基于形態學界定的“半開羊肚菌類”隸屬于黑色羊肚菌支系,以此解釋了形態鑒定和ITS序列分析中存在爭議的“半開羊肚菌類”的隸屬問題。進一步完成了系統發育識別種和基于形態鑒定種的對應問題,其中黑色羊肚菌類群對應形態鑒定種的Black Morel Group,黃色羊肚菌類群對應形態鑒定種的Yellow Morel Group,變紅羊肚菌支系 (Rufobrunnea Clade) 則對應Redbrown Morel Group,但是支系內的種對應關系仍需要進一步研究。Du等[16]在ODonnell的研究基礎上引入ITS序列,采用ITS、LSU、EF1-a、RPB1和RPB2共5個基因片段進行多基因聯合分析,共采集159份標本 (我國70份,北半球89份),研究發現,羊肚菌屬真菌共包括61個物種,其中屬于黑色羊肚菌支系的有33個 (其中13個在我國有分布),黃色羊肚菌支系27個 (17個目前僅分布在我國) 及羊肚菌屬真菌的基礎支系,變紅羊肚菌支系。基于多基因聯合分析技術能夠進一步分析羊肚菌屬真菌的演化歷史,系統地解釋其起源、演化及擴散機制,分析羊肚菌現代多樣性世界分布格局。
2 羊肚菌的保健功效
羊肚菌營養豐富,子實體和菌絲體發酵產物皆有極佳的保健作用。《本草綱目》中記載羊肚菌“甘寒無毒,化痰理氣,益腸胃”[2, 17]。現代研究表明,羊肚菌具有優良的抗氧化、抗腫瘤及保肝保腎的功效[18-19]。
2.1 羊肚菌的營養及功效成分
羊肚菌營養豐富,據測定每100 g羊肚菌干品中含蛋白質24.5 g、脂肪2.6 g、碳水化合物39.7 g、粗纖維7.7 g、煙酸82.0 mg、核黃素24.6 mg、泛酸8.7 mg、吡哆酸5.8 mg、硫胺素3.92 mg、生物素0.75 mg,此外還發現8種人體必需氨基酸[20]。
羊肚菌含有游離的稀有氨基酸,如a-氨基異丁酸,順-3-氨基-L-脯氨酸及2,4-二氨基異丁酸。油酸、亞油酸、硬脂酸和軟脂酸4種脂肪酸構成了羊肚菌的粗脂肪。其中,油酸可以降低膽固醇含量,對中風、心肌梗塞、肥胖及腎功能不全等病癥具有一定的預防作用。作為最有代表性的一種不飽和脂肪酸,亞油酸能夠有效降低膽固醇濃度,進而對動脈硬化具有一定的預防作用。亞油酸還能夠促進副腎上腺皮質激素等人體激素的分泌,能夠有效提高人體的應急能力。由此可知,羊肚菌具有較高藥用保健價值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不飽和脂肪酸含量較多。羊肚菌子實體產量有限,很多學者研究了羊肚菌菌絲體及其發酵產物。研究確認,羊肚菌菌絲體營養物質較為豐富,同樣具有優良的保健作用。羊肚菌菌絲體蛋白質含量為39.5%,包括19種氨基酸,人體必需的氨基酸含量高達44.14%。據測定,每100 g菌絲中含維生素B1 2.55 mg、維生素B2 5.97 mg[21]。可見,羊肚菌的子實體和菌絲體都具有很高的開發利用價值。
2.1.1 多糖類。多糖是一類由10個以上單糖組成,通過糖苷鍵連接的天然大分子化合物。多糖廣泛存在于植物、動物、微生物中,是生物體的重要組成和功能成分,會影響生物體的多項生理功能。多糖能夠有效促進動物體免疫器官生長發育和免疫細胞的增殖,同時提高動物體脾臟、法氏囊、胸腺及腸系膜淋巴結等主要免疫器官的質量,還能夠拮抗因免疫抑制劑造成的免疫器官萎縮,提高各類免疫細胞的功能,通過以上機制發揮重要的免疫增強功能[22-24]。多糖類是羊肚菌主要的活性成分,羊肚菌菌絲體多糖可分為胞內多糖和胞外多糖兩大類,從菌絲體能提取獲得胞內多糖,而胞外多糖是從發酵液中獲得。常用的發酵液多糖提取分離條件為旋轉蒸發濃縮發酵液后,保持-4 ℃沉淀有效成分,添加4倍體積的95%乙醇過夜沉淀,最終獲得發酵液多糖。菌絲體胞內多糖的提取分離條件為料液比40 ∶1,熱水浸提,提取溫度90 ℃,時間120 min,重復操作2次,浸提液旋轉蒸發濃縮,乙醇沉淀,即可獲得胞內多糖。孫玉軍等[25]采用液體深層培養獲得羊肚菌菌絲體,提取菌絲體胞內多糖,經DEAE-Sepharose F洗脫,進一步采用超濾濃縮脫鹽并冷凍干燥獲得羊肚菌胞內多糖MEP-I和MEP-Ⅱ。其中MEP-Ⅱ的含量更豐富,結構測定后發現MEP-Ⅱ是一種均一的酸性雜多糖蛋白復合物 (糖與蛋白質的比例為10.42 ∶1,以O-型糖肽鍵相連)。半乳糖 (Gal)、鼠李糖 (Rha)、甘露糖 (Man) 及葡萄糖 (Gle) 這4種單糖組成MEP-Ⅱ,MEP-Ⅱ的相對分子質量為28 000 Da,其結構中存在1→3、l→6連接鍵型,同時可能含有1→2或1→4連接鍵。魏蕓等[26]從羊肚菌發酵液中得到MEP-SP多糖,采用DEAE-纖維離子交換柱和SepharoseCL-6B純化分離得到2種成分MEP-SP2和MEP-SP3。通過高效液相色譜法測定MEP-SP2的分子量為23 000 Da,MEP-SP3的分子量為44 000 Da。進一步通過氣相色譜法分析其組成,結果發現,MEP-SP2單糖組成為葡萄糖、甘露糖、阿拉伯糖和半乳糖,含量為4.13 ∶1.75 ∶0.71 ∶0.68。MEP-SP3單糖組成為甘露糖、木糖、葡萄糖、果糖、阿拉伯糖和半乳糖,含量為3.85 ∶3.58 ∶1.77 ∶14.9 ∶51.3 ∶0.53。通過紅外光譜并結合核磁共振結果分析,發現羊肚菌多糖是一種具有α-吡喃糖苷鍵的雜多糖。
2.1.2 酚類。
通過發酵培養羊肚菌,從羊肚菌菌絲體中提取酚類物質。康宗利等[27]通過種子培養基完成羊肚菌菌絲體發酵并通過試驗獲得最佳酚類物質提取條件,即50%的乙醇溶液按1 ∶25的料液比,在70 ℃的水浴中浸提2.5 h,在此條件下羊肚菌菌絲體酚類物質提取率可達3.14 mg/g。通過菌絲體發酵獲得的羊肚菌酚類物質具有較強的超氧陰離子自由基及羥自由基清除能力,羊肚菌酚類物質能高效清除羥基自由基,清除率達64%;對超氧陰離子自由基也有較好的清除效果,清除率達63%。基于以上研究,確定羊肚菌菌絲體酚類物質具有優良的抗氧化能力,在抗氧化、抗衰老、美容保健方面具有良好的應用前景。盧可可等[28]提取褐赭色羊肚菌多酚,并驗證其對HepG2細胞的增殖具有抑制作用。試驗提取褐赭色羊肚菌中的游離酚和結合酚,采用HPLC對褐赭色羊肚菌多酚組分進行鑒定,測定多酚抗氧化能力指數,以人肝癌細胞HepG2為模型,測定多酚細胞抗氧化活性 (CAA值) 及抗增殖活性 (EC50值),結果顯示原兒茶酸、兒茶素、沒食子酸、對羥基苯甲酸及綠原酸組成了褐赭色羊肚菌的游離酚,而綠原酸、原兒茶酸及沒食子酸組成了結合酚,確定酚酸類是褐赭色羊肚菌多酚主要組分。同時,褐赭色羊肚菌多酚顯示出優良的抗氧化活性,能夠有效抑制HepG2細胞的增殖。
2.2 抗腫瘤作用
羊肚菌多糖具有優良的抗腫瘤功效。作為一種免疫調節劑,羊肚菌多糖能夠激活B、T淋巴細胞、自然殺傷細胞(NK)和巨噬細胞等免疫細胞。此外,多糖還具有活化補體功能,能夠有效促進細胞因子的分泌,進一步通過多個層面及多條途徑對免疫系統發揮調節作用。
陳彥等[29]以羊肚菌為原料,提取胞外多糖并驗證了抗腫瘤活性。羊肚菌胞外多糖灌胃荷瘤小鼠,濃度設定為200、400 mg/kg,觀測記錄的指標包括腹水瘤抑制率、小鼠存活期和免疫功能等,結果顯示羊肚菌胞外多糖具備直接殺傷腫瘤細胞的活性,并且存在劑量依賴關系。同時,該多糖能提高巨噬細胞的吞噬能力。以上研究表明,羊肚菌胞外多糖具有免疫調節和殺傷腫瘤的雙重活性。Hu等[30]通過羊肚菌菌絲體發酵提取到1種胞外多糖MEP-Ⅱ,該多糖能有效抑制HepG2 增殖,具有抗腫瘤的效果,其作用機制是增強細胞內活性氧 (ROS) 活性,通過一系列級聯反應誘導腫瘤細胞的程序性凋亡。
2.3 抗氧化作用
羊肚菌提取物具有優良的抗氧化功效,其主要的功效成分可能為多糖。Fu等[31]以羊肚菌菌絲體為原料,評估了其菌絲體胞外多糖的抗氧化活性,結果表明羊肚菌菌絲體胞外多糖能夠有效地清除自由基,表現出較強的抗氧化活性,進一步的動物試驗發現,該多糖具有一定的免疫調節作用。Kalyoncu等[32]選擇了10種常見的可食用真菌,采用乙醇提取法獲得其菌絲體提取物,之后比較了其抗氧化作用,結果表明高羊肚菌菌絲乙醇提取物具有較強的羥基自由基清除能力,表現出優良的抗氧化活性。Kim等[33]發現羊肚菌提取物在結腸癌細胞HT-29中可以抑制轉錄因子NF-κB的激活,具有抗氧化及抗腫瘤的活性。潘志福等[34]研究了尖頂羊肚菌胞外多糖的抗氧化活性,結果發現尖頂羊肚菌胞外多糖提取物具有較好的羥基自由基、超氧陰離子自由基及ABTS自由基的清除活性。此外,該多糖提取物能顯著提高小鼠腦組織SOD活性,降低MDA和LF的含量。試驗說明尖頂羊肚菌胞外多糖提取物具有優良的抗氧化活性,并且能夠延緩衰老。
3 展望
從形態學鑒定到DNA序列分析,從單純的種屬分類到基于多基因聯合分析的起源演化研究,羊肚菌的系統發育研究進展迅速且已經較為完善。但是,基于傳統形態學分類定名的羊肚菌種和基于多基因聯合分析給出的羊肚菌系統發育識別種之間的對應關系亟需明確。同時,我國的羊肚菌資源豐富,但許多珍貴的羊肚菌資源處于野生狀態,由于環境破壞和人類滅絕式的采集,野生羊肚菌資源日益減少,遺傳多樣性正在逐步喪失。隨著分子技術的進步,有必要加快羊肚菌系統發育學研究,運用更先進的技術(全基因組測序、重測序等),完善羊肚菌的系統發育知識,保護這一珍貴的真菌資源。
基于以上分析,有關羊肚菌屬真菌系統發育學研究的重點是收集資源與明確系統發育關系。通過廣泛收集我國羊肚菌資源并進行生境調查,探索羊肚菌遺傳多樣性及其與環境之間的關系;通過對資源的種屬鑒定,明確新舊命名系統的對應關系,有利于科學利用羊肚菌種質資源,是羊肚菌應用及產業發展基本且重要的前提。
古籍的記載和現代研究的佐證與開發都說明羊肚菌具有優良的保健作用,涵蓋了抗氧化、抗腫瘤、調節免疫、降三高等方面,是一種理想的保健食品,作為功能食品或輔助藥品開發具有一定的應用價值。同時,現有的報道大多集中在羊肚菌的功效開發與評價上,真正深入其保健機理的探索很少,定位于功能食品或輔助藥品的開發還需要大量的試驗支 撐,之后應借助細胞生物學、分子生物學等,對其功效機理進行探索,為更深入地利用羊肚菌積累數據。基于以上分析,羊肚菌功效研究的重點是相關機理的探索。明確羊肚菌作用功效的機制,有利于更高效地開展羊肚菌功效研究,更科學地利用羊肚菌資源。
參考文獻
[1]
楊芳,王新鳳,李剛,等.不同碳、氮源對羊肚菌生長與胞內多糖的影響[J].食品科學, 2007,28(11):396-400.
[2] 李時珍.本草綱目[M].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99:1718-1982.
[3] 國家中醫藥管理局《中華本草》編委會.中華本草[M].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1998.
[4] 趙永昌,柴紅梅,張小雷.我國羊肚菌產業化的困境和前景[J].食藥用菌,2016,24(3):133-139,154.
[5] 吳興亮,卯曉嵐,圖力古爾,等.中國藥用真菌[M].北京:科學出版社,2013.
[6] 李黎.中國木耳栽培種質資源的遺傳多樣性研究[D].武漢:華中農業大學,2011.
[7] ODONNELL K,ROONEY A P,MILLS G L,et al.Phylogeny and historical biogeography of true morels (Morchella) reveals an early Cretaceous origin and high continental endemism and provincialism in the Holarctic [J].Fungal Genet Biolo,2011,48(3):252-265.
[8] BELLEMAIN E,CARLSEN T,BROCHMANN C,et al.ITS as an environmental DNA barcode for fungi:An in silico approach reveals potential PCR biases[J].BMC Microbiol,2010,10(1):189.
[9] NILSSON R H,KRISTIANSSON E,RYBERG M,et al.Intraspecific ITS variability in the kingdom fungi as expressed in the international sequence databases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molecular species identification [J].Evolutionary biomformaiics,2008,4:193-201.
[10] ODONNELL K,CIGELNIK E,NIRENBERG H I.Molecular systematics and phylogeography of the Gibberella fujikuroi species complex[J].Mycologia,1998,90(3):465-493.
[11] ODONNELL K,CIGELNIK E,WEBER N S,et al.Phylogenetic relationships among ascomycetous truffles and the true and false morels inferred from 18S and 28S ribosomal DNA sequence analysis[J].Mycologia,1997,89(1):48-65.
[12] TAYLOR J W,JACOBSON D J,KROKEN S,et al.Phylogenetic species recognition and species concepts in fungi [J].Fungal Genet Biolo,2000,31(1):21-32.
[13] MORTIMER P E,KARUNARATHNA S C,LI Q H,et al.Prized edible Asian mushrooms:Ecology, conservation and sustainability[J].Fungal Divers,2012,56(1):31-47.
[14] 楊祝良.基因組學時代的真菌分類學:機遇與挑戰[J].菌物學報,2013,32(6):931-946.
[15] ODONNELL K,WEBER N S,REHNER S,et al.Phylogeny and biogeography of Morchella[C]//The 22nd Fungal genetic conference.Kallsas City,MO:Fungal Genetic Stock Cenicr. Fungal Genetic Newsletter, 2003.
[16] DU X H,ZHAO Q,ODONNELL K,et al.Multigene molecular phylogenetics reveals true morels (Morchella) are especially species rich in China[J].Fungal Genet Biolo, 2012,49(6):455-469.
[17] PFISTER D H,YING J,MAO X,et al.Icones of medicinal fungi from China[J]. Mycologia,1990,82(2):285.
[18] ELMASTAS M,ISILDAK O,TURKEKUL I,et al.Determination of antioxidant activity and antioxidant compounds in wild edible mushrooms[J].J Food Compos Anal,2007,20(3/4):337-345.
[19] WONG J Y,CHYE F Y.Antioxidant properties of selected tropical wild edible mushrooms[J].J Food Compos Anal,2009,22(4):269-277.
[20] 張廣倫,肖正春.羊肚菌營養飲料的研究[J].中國野生植物資源,1994(2):1-2.
[21] 賈建會,徐寶梁,宋淑敏,等.羊肚菌發酵制品保健機理初探[J].食用菌,1996,18(4):40-42.
[22] 孫設宗,盧娟,官守濤,等.云芝多糖對試驗性肝損傷抗氧化酶、自由基及一氧化氮含量的影響[J].時珍國醫國藥,2008,19(6):1439-1440.
[23] 張嫚,張蘭.靈芝多糖的分離純化和藥理活性及在功能食品中的應用[J].食品研究與開發,2005,26(1):118-120.
[24] DI LUZINO N R.Update on the immunomodulating activities of glucans[J].Springer Semin Immunopathol,1985,8(4):387-400.
[25] 孫玉軍,陳彥,周正義,等.羊肚菌胞內多糖對小鼠急性肝損傷的影響[J].中國食用菌, 2008, 27(2):41-42,45.
[26] 魏蕓,張天佑,張姝,等.羊肚菌多糖MEPSP1分離純化及性質鑒定[J].食用菌學報,1999,6(3):13-16.
[27] 康宗利,徐萍,楊玉紅.羊肚菌發酵菌絲體酚類物質的提取及抗氧化活性的研究[J].食品科技,2014, 39(7):219-224.
[28] 盧可可,譚玉榮,鄭少杰,等.基于HepG2細胞模型的褐赭色羊肚菌多酚抗氧化及抗增殖活性研究[J].現代食品科技,2015,31(12):6-13.
[29] 陳彥,潘見,周麗偉,等.羊肚菌胞外多糖抗腫瘤作用的研究[J].食品科學,2008, 29(9):553-556.
[30] HU M L,CHEN Y,WANG C,et al.Induction of apoptosis in HepG2 cells by polysaccharide MEPII from the fermentation broth of Morchella esculenta[J].Biotechnol Lett,2013,35:1-10.
[31] FU L H,WANG Y P,WANG J J,et al.Evaluation of the antioxidant activity of extracellular polysaccharides from Morchella esculenta[J]. Food & Funct,2013,10(4):1-28.
[32] KALYONCU F,OSKAY M,SAG ˇ LAM H et al.Antimicrobial and antioxidant activities of mycelia of 10 wild mushroom species[J].J Med Food,2010,13(2):415-419.
[33] KIM J A,LAU E,TAY D,et al.Antioxidant and NFκB inhibitory constituents isolated from Morchella esculenta[J].Nat Prod Res,2011,25(15):1412-1417.
[34] 潘志福,蘭瑛,張松.尖頂羊肚菌胞外多糖提取物抗氧化作用的研究[J].華南師范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2011(2):124-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