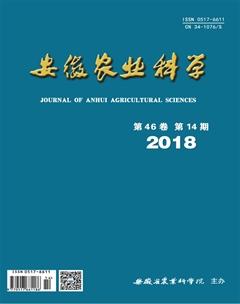內蒙古荒漠草原承載力綜合評價
宋向陽 邢啟明 常書娟 鄭淑華 楊勇 李蘭花
摘要 [目的]明確內蒙古荒漠草原生態系統的結構和功能的變化情況。[方法]選定達茂旗為研究對象,運用3S技術,對草地植被覆蓋度、草地生產力和載畜量30多年的變化進行了研究。[結果]達茂旗草地植被覆蓋度相比2000年初期升高了2百分點;達茂旗草地生產力由南向北呈遞減趨勢,相比2003年有所升高;達茂旗草地載畜量相比20世紀80年代和2000年初期整體水平有所升高。[結論]該研究結果為內蒙古制定生態管理決策提供了理論依據。
關鍵詞 荒漠草原;草地覆蓋度;草地生產力;草地載畜量
中圖分類號 S181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517-6611(2018)14-0093-04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on Bearing Capacity of Desert Steppe in Inner Mongolia
SONG Xiangyang1, XING Qiming2, CHANG Shujuan1 et al (1.Institute of Grassland Survey and Planning of Inner Mongolia, Hohhot, Inner Mongolia 010051; 2. Inner Mongolia Meteorological Administration, Hohhot, Inner Mongolia 010051)
Abstract [Objective] The aim was to accurately and truly reflect the changes in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the desert steppe ecosystem in Inner Mongolia. [Method] The desert steppe in Damao Banner was taken as the object of study, the change of vegetation coverage, grassland productivity and carrying capacity in recent more than 30 years was studied by using 3S technology. [Result] The coverage of grassland vegetation in Damao Banner was increased by 2% compared with in the initial period of 2000; the productivity of grassland in Damao Banner decreased from south to north, which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2003; the carrying capacity of Damao Banner grassland was increasing compared with the 1980s and in the initial period of 2000. [Conclusion] The result provides theoretical basis for Inner Mongolia to make up ecological management decision.
Key words Desert steppe;Grassland coverage;Grassland productivity;Carrying capacity of grassland
荒漠草原是草原向荒漠過渡的生態邊界帶,生態穩定性較差,氣候與人類活動的干擾作用容易使該生態系統產生波動。生態過渡帶獨有的特點及植被逆向演替的髙風險性使荒漠草原成為生態學關注的重要區域之一[1]。放牧是內蒙古荒漠草原的主要生產方式,然而,20世紀80年代實行了牲畜承包制后,由于牧民盲目擴增牲畜數量,草畜矛盾加重,荒漠草原植被出現較為嚴重的退化趨勢[2]。超載過牧是草原退化的主要原因[3-4],如何防止草原退化,保持畜牧業經濟的發展,調整生態與經濟平衡,關鍵問題是尋求草原合理的載畜率[5]。內蒙古荒漠草原的生產力低,卻是內蒙古中西部重要的畜牧業基地,因此,適宜載畜量的確定成為草原可持續發展的重中之重[6]。
達茂旗草原屬于典型的荒漠草原區,建國以來,達茂旗草原與生態環境總體呈現退化趨勢。具體表現為:地表水體萎縮,地下水位下降,土壤侵蝕加重,草場退化,土地沙化和鹽堿化面積擴大,進而導致該區生物多樣性減少、土地生產力降低、草地載畜量下降、農牧民生活貧困等現象[7-10]。鑒于達茂旗嚴峻的草原與生態惡化態勢,中央與地方政府實施了一系列的生態建設與恢復工程。為了從本質上掌握該地區各類生態管理與生態建設工程的效應,筆者以達茂旗作為研究示范區,運用3S技術手段,分析近30年來該地區草原與生態系統宏觀結構和服務功能的演變態勢,科學評價了各類生態建設工程的實際成效及其穩定性,提煉面向區域主體功能的生態管理優化模式,為地方政府的生態管理決策提供依據。
1 材料與方法
1.1 研究區概況
研究區位于內蒙古自治區中部包頭市境內,陰山北麓的烏蘭察布高平原。地處109°16′~111°25′E、41°20′~42°40′N,東與四子王旗毗鄰,西靠巴彥淖爾市烏拉特中旗,南連武川、固陽兩縣,北和蒙古人民共和國接壤,國境線在本旗綿延88.6 km。達茂旗地形特征南部高,北部低,由南向北傾斜,其間丘陵、低山、丘間盆地、波狀高平原交錯分布。平均海拔1 376 m,東西跨度150 km,南北縱深160 km,總土地面積最新數據為17 913.41 km2。
降水量從南往北遞減,分布不均。年平均降水量230~260 mm,南北相差近110 mm。同時季節分配和年際變化懸殊,保證率低。6—9月降水量占全年降水量的80%以上。春季降水量過少,常常出現春旱,影響牧草返青和農作物播種。
達茂旗是包頭市唯一的純牧業旗縣,擁有草原總面積16 498.27 km2,占國土面積的92.1%,是烏蘭察布草原的重要組成部分。主要草原類型有典型草原、荒漠草原和低平地草甸類,其中荒漠草原面積最大,占草原總面積的48.64%。達茂旗屬于北方干旱氣候條件,生態條件嚴酷,環境脆弱,再加上人為因素干擾和長期超載過牧影響,導致草原生態系統發生了逆向演替,生態環境逐步惡化,沙塵暴天氣肆虐,嚴重影響了牧民的生產和生活。
1.2 試驗設計 利用20世紀80年代和2000年初期草地資源狀況為本底,和2017年進行比較,根據不同草原類型的生產力、植被蓋度和承載力的對比,運用3S技術監測長時間序列不同載畜率水平的草 地植被變化,通過分析,揭示荒漠草原承載能力以及放牧對草原的影響作用,可為草-畜平衡管理及生態保護提供有效、直觀的數據支持,有助于科學地調控草-畜平衡,對提高牧場經濟與生態平衡具有科學指導作用。
1.3 調查方法
草原植被蓋度采用像元二分模型計算得出,像元二分模型是假設像元是由土壤與植被兩部分組成,即傳感器所觀測到的像元信息可表達為由綠色植被成分所貢獻的信息與由土壤成分所貢獻的信息之和。對于上述混合像元,其中植被所占比例可用模型表達如下:
C=(S-S0)/(Sg-S0) (1)
式中,Sg為純植被覆蓋像元的遙感信息量;S0為純土壤覆蓋像元的遙感信息量;C為植被蓋度。因為NDVI在植被的長勢、覆蓋度等方面被廣泛應用,所以在該模型的基礎上,運用NDVI來估測覆蓋度。將NDVI代入公式(1),得到基于NDVI的像元二分模型:
C=(NDVI-NDVIsoil)/(NDVIveg-NDVIsoil) (2)
式中,NDVIsoil為完全是裸土或者無植被覆蓋區域的NDVI;NDVIveg則代表完全被植被覆蓋像元的NDVI值。
草原植被生產力采用CASA模型計算得出。CASA模型是一個充分考慮環境條件和植被本身特征的光能利用率模型。該模型主要由植被吸收的光合有效輻射和光能轉化率2個變量確定。公式如下:
NPP(x,t)=APAR(x,t)×ε(x,t) (3)
式中,APAR為光合有效輻射,ε為光能利用率,x表示空間位置;t表示時間。由太陽總輻射中的光合有效輻射和植被對光合有效輻射的吸收比例(FPAR)決定,FPAR利用NDVI和植被類型表示,ε是植被把吸收的光合有效輻射(FPAR)轉換為有機碳的效率,主要受溫度和降水的影響。
1.4 計算方法 運用Arcgis和ENVI等遙感軟件對影像進行校正和配準處理,投影采用阿爾伯斯投影,投影區域面積保持與實地相等;草地載畜量采用農業行業標準《天然草地合理載畜量的計算》來計算。
2 結果與分析
2.1 達茂旗草原植被覆蓋度現狀與變化
用20世紀初期草地資源狀況為本底進行比較,運用3S技術,通過對2003和2017年達茂旗草原植被蓋度建立像元二分模型,比較分析得出2003年達茂旗草原平均蓋度為24%,2017年草原平均蓋度為26%,平均升高了2百分點(圖1)。達茂旗降水量從南向北遞減,蒸發量則由南到北遞增,由于受水熱條件的影響,草原植被蓋度也呈現出由南向北遞減的局勢,在南部希拉穆仁鎮、石寶鎮、烏克忽洞鎮、明安鎮的覆蓋度分別有不同程度的增加,百靈廟鎮的北部和巴音花鎮的南部從2003年的20%左右增加到2017年的30%左右,在達茂旗的北部滿都拉鎮,植被覆蓋度基本無變化,而在達爾罕蘇木中部的植被覆蓋度有降低的趨勢,這可能與季節性降水分布不均勻有關。
2.2 達茂旗草地生產力現狀評價
運用3S技術,通過對達茂旗溫度、降水、日照等綜合參數建立CASA模型,通過模型分別計算2003和2017年的地上生物量,監測結果顯示,2017年達茂旗天然草地生產力呈現出南高北低的趨勢,北部草原相對較差,這里主要分布荒漠草原類和草原化荒漠類。而在南部主要分布有溫性草原類(圖2),南部的希拉穆仁鎮產量最高,有個別的地方干草產量在800 kg/hm2以上,烏克忽洞鎮、石寶鎮的干草產量在600 kg/hm2左右,相比2003年,北部滿都拉鎮較差的草原在減少,南部較好的草原變得更好,這與工程項目的實施是分不開的。
由表1可知,2017年達茂旗天然草原牧草平均產干草304.01 kg/hm2,相比2003年和20世紀80年代分別提高了3.53%和2.13%,其中溫性草原化荒漠類提高幅度最大,相比2003年和20世紀80年代分別提高了23.26%和29.55%,這主要由于20世紀80年代初期人為活動頻繁,草場長期超載過牧,破壞嚴重,直到2002年以后開始實施休牧,2008年全面實施禁牧,嚴格執行舍飼圈養政策,以前破壞較嚴重的地區得到了有效控制,天然草原正在逐步恢復。
2.3 達茂旗草地載畜量現狀評價
天然草地載畜量根據天然草地產草量的多少,按牲畜日食量計算出天然草地實際可飼養的牲畜頭數。由表2可知,2017年達茂旗天然草原全年可飼養218.24萬頭綿羊單位,而2003年和20世紀80年代全養178.27萬頭和207.84萬頭羊單位,2017年載畜能力整體水平在升高,與2003年和20世紀80年代相比分別提高了22.42百分點和5.0百分點,其中溫性草原類載畜能力水平提高幅度最大,2017年溫性草原類全年可飼養79.69萬頭羊單位,與2003年和20世紀80年代草地載畜能力相比分別提高了64.28百分點和12.61百分點,溫性荒漠是達茂旗草原的主體,2017年其全年可飼養92.98萬頭羊單位,與2003年相比提高了7.2百分點。草地載畜能力的提高主要同達茂旗近年來實施草原生態治理工程、移民項目、封育草場有關。
3 結論與討論
該研究表明,達茂旗草地植被覆蓋度相比2003年升高了2百分點;在全旗由南向北呈遞減趨勢,這主要是受水熱條件影響;達茂旗草地生產力由南向北呈遞減趨勢,相比2003年有所升高,這與工程項目的實施是分不開的;
達茂旗草地載畜量相比20世紀80年代和2000年初期整體水平有所升高,這主要與近年來實施草原生態治理工程、移民項目、封育草場有關。
根據達茂旗草原生產力南高北低的局勢,制定利用方案。北部滿都拉鎮和蒙古國接壤,常年受蒙古高原高氣壓影響,是該區域生態環境最惡劣的地區,根據遙感監測,平均蓋度不到25%,平均產量每公頃產200 kg左右干草,針對該區域實施休牧措施,對于重度沙化的地區要采取補播,重度退化的地區要實施禁牧,同時當地并不適合飼養小畜,由于小畜行走消耗與采食積累的能量幾乎相同,所以適合可遠距離放牧并能適合荒漠草原環境的駱駝[11]。
對于南部草原平均蓋度在50%左右,有個別區域的干草產量達800 kg/hm2,是該地區發展草原畜牧業潛力最大的區域,這一區域地勢相對平坦,交通方便,應逐步壓縮以至取消放牧山羊,而以放牧或半舍飼綿羊為主,同時加強人工草場的建設,種植優良牧草,增加飼草料的供應[12]。
草原超載過牧是造成草原退化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13],草原超載過牧嚴重,使草原得不到休養生息的機會,造成草原生產力下降和草原生態環境不斷惡化[14]。同時,由于草原退化,草原承載能力進一步下降,加劇了草畜矛盾,形成一個惡性循環。實現草畜平衡是促進草原生態系統良性循環,實現草原畜牧業持續發展的基礎[15]。
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達茂旗人口不斷增加,帶動了牲畜頭數不斷增長,致使草原出現超載現象。隨著人們對草原生態保護的認識,牲畜頭數逐年降低,直到2003年基本達到草畜平衡,后來隨著禁牧圍封措施的實施,生態移民政策也開始實施,牧區牲畜頭數不斷降低,到2010年達到草大于畜。針對達茂旗草畜平衡問題,并非簡單地降低家畜頭數或者載畜量,還牽涉到復雜的社會問題,特別是牧民的生活和增收,牧民要維持生活水平,就必然要增加牲畜頭數,因此,草畜平衡實質上是“人-畜-草”的平衡問題[16]。
參考文獻
[1]
王薩仁娜.3S技術支持下的荒漠草原不同載畜率水平植被變化研究[D].呼和浩特:內蒙古農業大學,2016.
[2] 張立中.中國草原畜牧業發展模式研究[M].北京:中國農業出版社,2004.
[3] 賽勝寶.內蒙古北部荒漠草原帶的嚴重荒漠化及其治理[J].干旱區資源與環境,2001,15(4):34-39.
[4] 肖力宏,寶音陶格濤,劉海林.草地退化的原因及退化草地改良的研究[J].科學管理研究, 2004,22(2):27-29.
[5] 李博.中國北方草地畜牧業動態監測研究[M].北京:中國農業科技出版社,1993.
[6] 馬林.內蒙古可持續發展論:內蒙古人口·資源·環境與經濟可持續發展研究[M].呼和浩特:內蒙古大學出版社,1999.
[7] 霍擎.包頭市達茂旗土地退化評價研究[J].陰山學刊,2004,18(1):20-23.
[8] 昝成功,武侃強.達茂旗草原生態環境受損問題[J].內蒙古環境保護,1999(2):37-39.
[9] 呂子君,盧欣石,辛曉平.中國北方草原沙化現狀與趨勢[J].草地學報,2005,13(S1):24-27.
[10] 董光榮,吳波,慈龍駿,等.我國荒漠化現狀、成因與防治對策[J].中國沙漠,1999,19(4):318-332.
[11] 買小虎,張玉娟,張英俊,等.季節性放牧調控對草地植被的影響[J].西化農業學報,2014,23(3):24-30.
[12] 滕星.羊草草地放牧綿羊的采食與踐踏作用研究[D].長春:東北師范大學,2010.
[13] 陳靈芝,陳偉烈.中國退化生態系統研究[M].北京: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1995.
[14] 王宏,李曉兵,李霞,等.中國北方草原對氣候干旱的響應[J].生態學報,2008,28(1):172-182.
[15] 楊智明.不同放牧強度對荒漠草原植被影響的研究[D].銀川:寧夏大學,2004.
[16] 謝雙紅.北方牧區草畜平衡與草原管理研究[D].北京:中國農業科學院,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