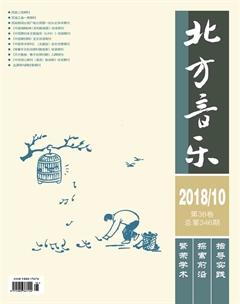20世紀中國“新音樂”概念梳理
汪妮
【摘要】專業術語不同于日常用語,是某學科得以建立的基礎,必須明確其內涵。查中國近現代音樂史各學術專著和論文中,“新音樂”這一專有術語,自1903年曾志忞第一次提出到2015年的百余年里仍有學者在解讀該術語,各類論文、專著和詞典中賦予該術語不同的含義,有的追隨政治概念進行定義,有的從歌詞內容進行分類,有的從音樂本體進行解釋,導致各種誤解。本文旨在對該專業術語內涵流變做一梳理,并在此基礎上對“新音樂”研究的思路進行總結。
【關鍵詞】新音樂;學堂樂歌;國樂;歌詠運動
【中圖分類號】J605 【文獻標識碼】A
在引進外來文化的過程中,西方文化思想與中國文化思想發生矛盾,在思想、文化上對“新”和“舊”的討論貫穿整個中國近現代史,同時也陷進了“變”與“不變”,“變多少”“怎么變”的掙扎中。在中國近現代音樂史上,怎樣處理好西方音樂(或“西樂”)與中國傳統音樂(或“國樂”)的關系,“土洋之爭”等幾乎成了所有音樂論爭都會涉及的話題,“新音樂”正是在這樣的思考與論爭中產生、發展,對“新音樂”的研究貫穿了整個20世紀中國音樂史。通過對“新音樂”概念演變的梳理,探索20世紀“新音樂”研究的線索和思路。
一、西方“新音樂”概念分析
在中國近現代音樂史上,曾經有很多學者在介紹西方音樂的時候,對西方某個階段使音樂以“新音樂”來形容,如《音樂界的新運動》《法蘭西新音樂的領導:霍列(Gabirel Faure 1845-1924)》《新音樂運動在美國》等。所以,在研究中國近現代“新音樂”的同時,有必要對西方的“新音樂”概念進行梳理。“新音樂”(New music;德,Neue Musik;意,Nuove musiche)在西方音樂史上有很多不同的概念。《牛津簡明音樂詞典》《音樂百科詞典》《大陸音樂辭典》對“新音樂(new music)”的界定都是泛指西方音樂史上每隔一段時期反復出現的概念。
二、“新音樂”概念在中國的提出和發展
“新音樂”在中國近現代音樂史上曾多次被提出,在近代許多論文、專著、詞典中“新音樂”被賦予了不同的含義。下面筆者按照“新音樂”定義中所指時間范圍的順序,對不同定義進行分條陳述:
認為“新音樂”是從19世紀末20世紀初開始的,作曲家運用中國的音樂素材,學習和借鑒西方的音樂技術語言而創作的音樂,以區別于中國古代音樂、中國傳統音樂,從學堂樂歌開始。曾志忞于1903年第一次提出“新音樂”:“為中國造一新音樂,然則音樂之有利于國也。”其認為“新音樂”的基礎是音樂理論:“音樂之入門曰樂理,或曰樂典,非此不足言音樂。”也就是其《樂典》當中所涉及的基本樂理知識。
劉靖之在《新音樂的萌芽期》中提到中國近代史里的三大音樂活動影響中國近代“新音樂”的發展,分別是太平天國的宗教音樂活動及其流傳下來的歌曲、袁世凱引進歐洲銅管樂和軍樂、學堂樂歌。特別是學堂樂歌的興起,從20世紀初開始至李叔同1918年出家結束,它是中國近代音樂教育的開始,也是中國“新音樂”發展的萌芽,并為20世紀20年代的發展奠定了基礎,中國“新音樂”的先驅是曾志忞、沈心工、李叔同。
“新音樂”應包括“五四”運動(1919年)以來一切愛國的、民主的、反帝反封建的、具有進步意義的音樂。直到“五四”之后民國九年蔡元培先生創辦北京大學音樂傳習所,中國新興音樂才算正式奠基。目前中國先進的音樂教育者和演奏家們都是那個時代的學生。持這種說法的人一般認為此時期內開始系統地、正規地引進、學習西方音樂理論,這才是“新音樂”的萌芽。
后至20世紀30年代,“新音樂”指當時以抗日救亡為主要內容、運用民族形式創作的音樂。1931年,須勍吾提出了創造中國“新音樂”的目標:
我們所要創造的那種新音樂,絕對不是復古,不是守舊,也不是剽竊,不是販賣、轉運,更不是特殊式,貴族式,階級式的;我們務須建立在民眾身上,以全民為立場。換言之,就是要適合于現代中國的民族,并且可以代表整個民族的特性,喚發民眾的美德,倡導民族的情感。所謂“民族之聲”,用這種音樂來熏陶民眾,鼓勵民眾,激發民眾,團結民眾,使全民意志上有了這樣的鍛煉。
更具體的論述是,“新音樂”由1934年的電影《大路》公映開始。雁君在《中國的新音樂》中說到:“由進步的電影如大路,漁光曲等興起,隨著帶來了新音樂,所以可以說新音樂并不是自己生長起來的,但是在最近好像已能單獨生存下去了,因為它已經有了大量的群眾。”持這種說法的還有章枚在《1936年新音樂發展的檢討(附歌曲)》中說:“大路歌的作者聶耳氏是這種新音樂的開發者……聶耳的貢獻與其說是為我們創作了些什么歌曲,不如說是為我們開開了一條新的路徑。”李凌在綠永《論新音樂的民族形式(附歌曲)》中說:(聶耳)“開始第一人發見利用存在大眾現實生活中的新鮮活潑的旋律,為新音樂寫下一頁新的偉大的歷史,把新音樂劃成了兩個時代。”
以上三類是從“新音樂”含義中所指時間的順序進行分條陳述。同時,在這個所指時間范圍內,“新音樂”也有著如下幾種不同的具體內涵或體現方式。
(一)認為“國樂”或者“國樂改進”屬于“新音樂”的范疇
王光祈在《歐洲音樂進化論》當中對“國樂”進行了定義:
什么叫作“國樂”?就是一種音樂,足以發揚光大該民族的向上精神,而其價值又同時為國際之間所公認。因此之故,凡是“國樂”須備具下列三個條件:(一)代表民族特性。(二)發揮民族美德。(三)暢舒民族感情。
之后蕭友梅也在《國立音樂專科學校實施復興國樂報告》中用一句話對“國樂”進行概括:
何為國樂,能表現現代中國人應有之時代精神、思想與情感者,便是中國國樂。
吳贛伯在《新音樂與國樂改進》中談到:“長期以來,我們的大多數音樂理論家和作曲家們總是把聲樂和西洋管弦樂等形式的作品作為闡述新音樂的主要對象或僅有對象,而輕視或無視將國樂和國樂的改進放到整個新音樂的范疇來研究。這我們可以從近幾百年來許多人的音樂思想和音樂教育中找出因果關系,但無論如何,這一研究是不完整、不全面的”。
(二)認為“國防音樂”是當時“新音樂”的主要表現形式
柳青在《論新音樂運動》說:“國防音樂運動是整個新音樂運動的開端”。趙沨在《中國新音樂運動史的考察》中說:“‘一二·九運動以后……‘國防音樂的提出,這表面上的沉寂正式新的開展之前的醞釀。”
(三)認為“歌詠運動”或者“歌曲”是當時“新音樂”或者“新音樂運動”的主題
天風在《“‘救亡歌曲之外”》認為歌曲是當時“新音樂”的主題。
賀綠汀在《新中國音樂啟蒙時期歌詠運動》中認為,歌詠運動是當時“新音樂”的主流。
但是,“新音樂”所包含內容不僅僅局限于以上固定的時間內所限定的音樂,隨著社會的發展,對“新音樂”也有不同的定義和要求。
三、結語
綜上對“新音樂”含義的不同說法可以看出,不管是哪種定義,20世紀中國“新音樂”的研究總是蘊含著兩條線索:其一,對其音樂本體的研究,包括曾志忞所提的“新音樂”的基礎音樂理論、樂典等、“五四”時期學校所教授的音樂知識、抗戰時期創作的歌詠等;其二,通過“新音樂”達到某種目的的“新音樂”功能的研究,包括學堂樂歌時期“利于國”的音樂、“五四”時期的具有“反帝反封建”和抗戰時期的“救亡歌曲”等。從“新音樂”的概念出發,可以看出20世紀“新音樂”研究的兩條線索和思路。
參考文獻
[1]幼雄.音樂界的新運動[J].東方雜志,1921(11):71-73.
[2]李樹化.法蘭西新音樂的領導:霍列(Gabirel Faure 1845-1924)[J].亞波羅,193(12):69-72.
[3]編輯部.新音樂運動在美國[J].娛樂(上海1935,雙周刊),1921(25):605.
[4]康謳.大陸音樂辭典[K].大陸書店印刷廠,1980,4 (20):801,805,820.
[5](英)肯尼迪,(英)布爾恩.牛津簡明音樂詞典(第四版)[K].唐其競.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2002(09):815.
[6]廖天瑞主編.音樂百科詞典[K].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1998:673,674,681.
[7]劉靖之.新音樂的萌芽期[C]劉靖之.中國新音樂史論集.香港: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1986:1.
[8]中國藝術研究院音樂研究所編輯部主編.中國音樂詞典[K].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1984:436-437.
[9]中國藝術研究院音樂研究所編輯部主編.中國音樂詞典[K].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1984:436-437.
[10]雁君.中國的新音樂[J].內地青年,1937,(創刊號)9-10.
[11]章枚.1936年新音樂發展的檢討(附歌曲)[J].音樂教育,1937(01):73-86.
[12]李凌.論新音樂的民族形式(附歌曲)[J].新音樂月刊,1940(1-2):2-21.
[13]王光祈.歐洲音樂進化論[M].上海:上海書局,1932:45.
[14]蕭友梅.國立音樂專科學校實施復興國樂報告[J].教育通訊(漢口),1943(21):2,5-7.
[15]吳贛伯.新音樂與國樂改進[C]劉靖之.中國新音樂史論集——回顧與反思.香港: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1992:77-118.
[16]柳青.論新音樂運動[J].新歌,1939,(創刊號)18-22.
[17]趙沨.中國新音樂運動史的考察[J].新音樂月刊,1940 (03):44-51.
[18]天風.“‘救亡歌曲之外”[J].新音樂月刊,1940 (05):4-8.
[19]賀綠汀.新中國音樂啟蒙時期歌詠運動[J].中蘇文化雜志,1939(8-9):35-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