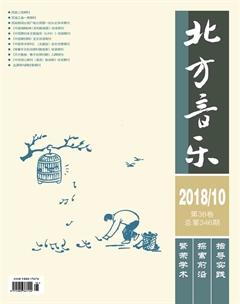短暫甜蜜下永恒的悲哀
徐劍飛
【摘要】人類痛苦的根源是欲望,而人類的欲望是無窮盡,永遠無法得到滿足的,所以人們是“甜蜜”而“悲哀”地度過這一生。
【關鍵詞】《甜蜜的悲哀》;欲望;糖;薩林思;西敏司一
【中圖分類號】C912 【文獻標識碼】A
一、內容玄機
文章的開始部分借鑒了法國詩人夏爾·波德萊爾的《惡之花》,兩者對人生都流露出了“悲哀”的看法,不過這種看法是有界域的,一旦脫離基督教這個標準,也就無法理解其中意味。說到底,這是薩林斯對詩人觀念上的延續,但這種延續卻帶有些“西方文化中心論”的意味。如文章認為“這個世界,包括生物,是從虛無中創造出來的,它本身并不具有任何神圣性。沒有一個要對罪惡負責的上帝,因為在缺乏善時,上帝并沒有制造惡。上帝所創造的是善。”這種“一神論”及“神是絕對的善”思想帶有強烈的基督教色彩,與很多地區的信仰是背道而馳的,如中國是多神論,并且神也有好壞之分,像“沉香救母”故事中,二郎神就是惡神的代表,中國的神有類人性,這與西方的神有著本質上的區別。
二、題目寓意
本文是對西敏司《甜與權力》一書的進一步思考,同時也是對其中隱喻的借用和演繹。《甜與權力》講述了糖是如何從一件奢侈品化身為工業化生產商品的過程,我們可以看到糖是如何經過一個自上而下的復雜文化過程,一步步嵌入到日常生活的肌理之中。在書中西敏司通過研究糖的歷史,指出正是西方社會的本土人論在近代歷史上賦予了糖——甜蜜經濟上的功效。西敏司注意到,茶、咖啡等東西在其原產地是不加糖的,但自從被引入歐洲后,是加糖的,他認為這是西方人試圖使用這種甜味使整個工業革命的痛苦變得可以讓人忍受。而這種方式反映了西方人的人生觀:活著就是一種修行,一種贖罪,只有現世受苦才可以換來死后的甜蜜。
本文是薩林斯對西敏司的批判發展。西敏司關注的是“資本主義現代性的誕生”,而薩林斯關注的地方在于這種資本主義現代性的更古老的淵源,他在文章前言中寫道:我將試圖說明,這種宇宙觀既不起始于啟蒙運動,也不終結于啟蒙運動。它們是歷史悠久的本土文化結構,至今依然占據學院式人類學,并使我們對別的族群的理解產生極為可怕的后果。與西敏司相比,薩林斯所關注的不是斷裂和區別,而是文化觀念的延續和發展。
三、讀后反思
回到文章最開始,文中所說的甜蜜是什么?悲哀是什么?
根據語法來分析“甜蜜的悲哀”,其所真正想要突出的是“悲哀”。所謂的“甜蜜”是指當欲望得到滿足時所獲得的“甜蜜”;而“悲哀”是指人生在世活著只是為了滿足欲望的那種悲傷之感。這種甜蜜是暫時的,是對痛苦暫時的緩解。痛苦無法真正被根治,因為它的根源是人類的欲望,而人類的欲望是無窮盡,永遠無法得到滿足的。文章認為,社會之所以進步是因為人類的需求和欲望,但也正是需求和欲望,使人們不斷的痛苦,因此才需要短暫的甜蜜來掩蓋永恒痛苦的真相。
相比于“甜蜜”的暫時,只有“悲哀”才是永恒的,當人們試圖去獲得快樂并以此來掩飾痛苦之時,這種永恒性就越發的凸顯出來。正如文中所言:“人之有限性乃是一切罪惡的根源。起因和罪行都出于人性:他是在欠缺和需求方面無法完美的生物。懲罰也同樣如此。”人本身就是有缺陷的生物,但卻試圖妄想和上帝一樣完美,因此人類成為自己欲望的奴隸,在不斷滿足自己欲望中痛苦著。只有不幸福的人才會不斷追求幸福,因此不斷追求幸福的人都是不幸的人,該觀點有些中國道家學說中的“無為而治”的味道,什么都不去管理就是最好的管理,一切皆是最好的安排。但是我們知道人是幾乎不可能沒有任何欲望的,但是“神”可以,因此才會有妄想得道成仙的人,這一點在東方和西方的文化中是不謀而合的。但我們是否想過,我們開始是幸福的活著,是偶爾的痛苦掩飾了永久的快樂,也就是“悲哀的甜蜜”而不是“甜蜜的悲哀。”
如果說西方的一切科學都是披在宇宙觀的外面,那么其實質就是人與自然之間的符號學解釋,那么人們眼中所謂的“自然”都有著“人為”的影子。從這個觀點出發,發達國家和原始部落是一樣的,我們沒有理由去認為只有原始人才迷信,只有發達國家的人才懂經濟。這一思想的本質是文化平等觀念,薩林斯實質是抨擊“西方文化中心論”的思想,只有平等才可以更好地理解文化中人與自然的符號學解釋,只有這樣才可以更好地明白和體會民族象征符號。
參考文獻
[1]黃劍波.甜蜜何以是一種悲哀?——閱讀《甜蜜的悲哀》[J].世界宗教文化,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