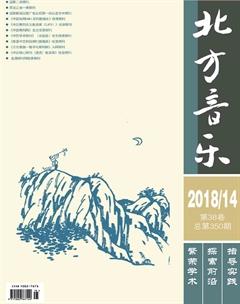哲學詮釋學視野下的音樂作品權利重構研究
王肅
【摘要】目前,音樂作品結構模式中采用的是音樂作品權利結構,著作權人是創作者,領接權人是表演者。隨著哲學解釋學的發展,讀者權利模式得到了有效推廣,對表演者的角色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求能夠充分展現藝術個性與藝術理解,對音樂作品的權利結構進行了重組分析。
【關鍵詞】哲學詮釋學;音樂作品;權利重構;研究
【中圖分類號】J60 【文獻標識碼】A
本文應用了哲學解釋學的方式對音樂作品的權利結構進行了批評性的分析,分析了應用作品的權利結構,并進行了優化重組。在傳統的研究視角下使用的是作者中心論,注重的是作者的表現意圖,表演者的表演活動是對作者創作意圖的重新構建,因此,最基本的理論套路是充分尊重創作者的創作意圖。這是屬于獨斷型的客觀主義權勢方式,將作品的意義進行了固定。隨著哲學解釋學的發展,這種結構模式發生了一定改變,充分尊重了表演者的表演方式。
一、從傳統詮釋學視域下音樂作品權利構成分析
根據傳統詮釋學的分析,在音樂作品的表達過程中非常注重各種樂譜的創作,將其作為音樂作品的本體,看作是音樂創者精神世界的客觀表達,看作是創作者進行精神世界創作的重要形式表現,將表演看作是對創作者精神意圖進行再現的一種方式,屬于對樂譜的再現。本文研究中的表演者也即是讀者,是對音樂作品進行閱讀的讀者,在進行表演過程中要求嚴格按照作者中心論的要求,不能含有自己主觀性的見解,將作品看作了一個固定不變的所在,隨著哲學詮釋學的發展,應當對其進行一定調整。[1]
二、讀者中心論的權利重構
在讀者中心論視域下對傳統進行了優化與重組,表演者不再是對創作者創作意圖的再現,而是能夠在表演過程中充分融合自己的思想,對于音樂作品中的一些空白區域進行有效填補。讀者中心論的權利重構包括了演繹音樂作品,新作品的演繹以及合作作品的創作三個形式,下文分別對此進行分析。
(一)演繹音樂作品
目前,在很多作品演繹過程中,表演者能夠對樂譜進行一些個性化改動,從而充分體現智慧化的作品創作,因此表演的過程已經形成了一門獨立性的作品。根據哲學詮釋學的解釋,樂譜本身屬于沒有完成的作品,表演者的表演過程實質上也是一個能夠體現個性化特征的作品。樂譜屬于一種靜止的視覺化符號,同時,表演綜合了流動的視覺化的聲音等方式。因此,可以將表演過程理解為作品的演繹過程。音樂作品原作者的權利與表演者的權利共同存在于作品演繹過程之中,這在美國的《版權法》中有一定體會。作品演繹的重要特征之一也是權利的共存,表演者不是替代創作者,而是將表演歸結到作品的演繹過程之中,為了實現這一目的,應當把表演者從權利的邊緣位置放置到權利的中心位置之中。表演過程并不是一種簡單的重復,而應當歸結到創作者中來。
(二)新作品的演繹
從哲學詮釋學的角度考慮,音樂作品本身含有表演的性質,草圖式的音樂作品不能構成音樂作品最本質的東西,音樂作品的表現形式必然同時包含著音響與聲音,而不僅僅只是表現在音樂樂譜上。樂譜難以處于表演過程中的核心位置,從某種角度上來說為可有可無的位置,表演是完全獨立于樂譜之上的一個音樂作品,可以完全將表演當作是全新的作品,是基于樂譜之上進行演繹的新的作品與形式,屬于完全與樂譜相獨立的一個新的作品,樂譜構成了其中的一個素材或者是注腳。
(三)合作作品的創作
合作作品指的是將樂譜與表演兩者結合共同構成的一個作品形式,其中樂譜屬于留白的圖畫式的開放化作品,表演者基于樂譜內容之上進行發揮創作完成了最終的音樂作品。根據美國《版權法》中的相關規定,由多位創作人員共同完成了不可分割的相互依存的作品。在一個作品的展現過程中充分融合了創作人與表演者,充分肯定了表演者的地位,但是兩者之間并不是互相獨立產生的,而是應當互相切磋,共同完成音樂作品。合作作品與新作品以及演繹作品相比具有不同點,主要表現在演繹作品與新作品之間處于基礎作品與衍生作品的關系,合作作品則是將兩者進行融合產生一個新的作品。[2]
根據哲學詮釋學的發展,音樂作品的表演不再是對于創作者創作意圖的簡單復制,而是利用表演形式的創作體現出了一個新的作品,充分糅合了表演者的理解,使得表演者參與到了新作品創作、作品演繹以及合作作品創作這樣一個新的過程。
三、結束語
在傳統詮釋學下“作者中心論”中權利結構與音樂本質之間出現了嚴重的錯位現象,以創作者為中心,沒有充分尊重表演者的地位。運用哲學詮釋學的本體論思想,將表演者充分放置到權利的中心位置,是對音樂作品的一種正確解讀。
參考文獻
[1]劉文獻.未完成的作品:哲學詮釋學視野下的音樂作品權利重構[J].廈門大學法律評論,2014(01).
[2]易森林.哲學解釋學視野下的教師權威[J].當代教育科學,2016(19):55-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