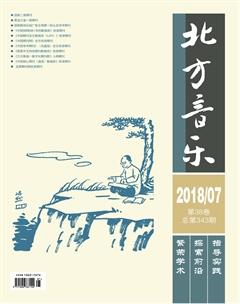城市生態中的社會音樂考察
【摘要】城市作為社會職業音樂人這一群體賴以生存的社會環境,城市現代化的進程促使經濟、文化、社會的交流更加頻繁,城市音樂文化也得到了迅速發展。社會職業音樂人的職業狀態和他們多重的社會角色,以及他們行為所實現的社會音樂文化的多元性和多樣性、音樂的藝術性與大眾性都是城市音樂研究需要關注的重要部分。
【關鍵詞】城市化;城市音樂;社會職業音樂
【中圖分類號】J605 【文獻標識碼】A
音樂的文化藝術作為城市發展的“軟實力”,音樂也用其特殊的方式詮釋著城市的文化內涵。“沒有音樂職業及其從事音樂職業活動的人,音樂將永遠處于人類音樂的原始形態。人類社會的音樂文化之所以發展到了今天,音樂的職業活動是這種發展的直接動力。” 職業音樂人在我國由來已久。夏、商、周時期,據《左轉·昭公十七年》載太史引《夏書》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又《國語·周語》:“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獻詩,瞽獻曲,史獻書,師箴,瞍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相傳黃帝時候有樂師倫,舜時有樂師夔(kui),堯時有樂師質等。大約從夏朝起,就由瞽(盲人)擔任專職樂師。”這一時期出現少量的宮廷專職樂師。秦漢時期,“漢武帝時擴建樂府,吸收大量的民間音樂和民間樂工入宮廷,對音樂的發展和繁榮起到了積極作用。其中涉及地方樂工有:邯鄲鼓員、江南鼓員、巴渝鼓員、楚嚴鼓員、梁皇鼓員、臨淮鼓員、諸族樂人、沛吹鼓員、族歌鼓員、陳吹鼓員、商樂鼓員、東海鼓員、長樂鼓員、蔡謳員、齊謳員等。”與夏、商、周時期相比這一時期樂工的分工更加明確,并且廣招民間樂師。隋、唐五代時期,“與隋唐音樂文化高度發展相適應的是,隋唐時期的音樂機構和音樂家也相當多。隋煬帝時,宮廷樂工已達三萬人。唐代宮廷樂工也達數萬人,《新唐書·禮樂卷》(卷22)曰‘唐之盛時,凡樂人、音聲人、太常雜戶子弟,隸太常及鼓吹署,皆番上,總號音聲人,至數萬人。唐玄宗時期又設有梨園,唐代段安節《樂府雜錄》曰:‘古樂工都計五千余人,內一千五百人俗樂,系梨園新院于此,旋抽入教坊。”古時職業音樂人到隋唐時期其發展已具相當規模,并且在這一時期也涌現出了許多杰出的民間音樂家,例如唐代開元年間的樂工李龜年、彭年、鶴年、何滿子,貞元年間的王芬、曹保保等。
生產資料聚集、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設施完善等諸多因素加快了城市化的進程,以城市生態為依托的社會職業音樂文化現象也越發頻繁。在城市化進程中,由于人口流動、經濟文化交融等產生的文化涵化現象,使城市音樂漸漸趨于大眾化并呈現出一種基于滿足消費需求的多樣性“趨同化”現象,即隨著城市化的進程,使城市生態下的社會音樂這一特殊的文化現象為迎合大眾審美以及商業化、產業化等需要(可能還涉及時政要求)出現某種“繁榮”景象的同時,作為藝術音樂的創作動機、創作意象以及音樂文本等本應所具有的藝術價值也似乎在不斷走向貶值,并從另一角度使城市音樂文化趨于動態的“混亂”局面。但從另一方面看,城市音樂所具有地域特征和民族特色又以典型的文化元素得以傳承而形成獨特的文化景象,從而形成城市生態下的多樣性音樂文化格局,進而促生以音樂為職業的社會職業音樂人。
城市中的音樂創作、音樂分析,以及聽眾和音樂文化的研究等,是音樂事項的構成元素。而音樂事項以人的活動為主體產生、傳播和發展,這些音樂所包含的文化藝術往往具有更深層次的內含,以音樂為媒介反映音樂人群(既包含創作人、表演者、制作人、推廣者、傳播者以及聽眾)的情感表達、精神追求亦或是時下的流行趨勢或是商業需求。這些音樂的創作者和表演者的社會角色和專業領域大相徑庭,從社會角色來看,其中有經過專業音樂教育的人士,也有業余愛好者,有國家專業藝術機構的人員,也有自由職業者;從個人需求來看,有將音樂作為創作或表演當成愛好的,也有將音樂作為謀生技能或以音樂產品獲取商業利益的。盡管他們的社會角色和個人需求各有不同,但他們的音樂行為最終都在生活中得以實現,被大眾所接受,這樣的行為就形成了社會音樂。
隨著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文化交流日益頻繁,音樂作品更種類繁多,音樂產品以及系列的商業活動隨之繁榮,通過社會職業音樂的研究和分析了解社會需求,用音樂的方式對城市文化進行闡釋。通過對社會職業音樂的研究呼吁更多的人關注社會職業音樂,使社會職業音樂的發展更加有序。
參考文獻
[1]曾遂今.音樂社會學[M].上海:上海音樂出版社,2004.
[2]鄭祖囊.中國古代音樂史[M].北京:高等音樂出版社,2008.
作者簡介:孫啟文(1992—),女,西藏大學藝術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