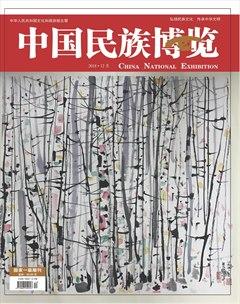談中國肢體戲劇的探索
侯玥
【摘要】肢體詩劇《蓮心不染》是屈軼導演受邀北京電影學院影視戲劇研究所,為表演學院表演系16、17級研究生量身定做的劇目。在基本的臺詞和故事線索中,以大量結合現代舞、戲曲身法步的肢體語言來塑造角色,外化人物內心。該劇是一則關于生命的東方寓言,呈現出“天人合一”的哲學意象。劇中角色名稱是天地眾生的代名詞,表現了當代社會人性被物化、靈魂被物欲奴役后,人類自我走向毀滅的同時,其對宇宙生態的毀滅性破壞;通過宏大敘事的詩劇構作手法,呈現了一系列天界、神界、靈界等大情結、場面,以萬物寂滅重生的起承轉合,期冀在宇宙最后的孤獨中,人性光芒的回歸和照耀——天地人神,和諧共棲。
【關鍵詞】中國肢體戲劇;《蓮心不染》
【中圖分類號】J801 【文獻標識碼】A
肢體劇,其實不是一個劇種,而是一個戲劇表演的流派,一種演劇風格。這種表演強調演員的表演才是舞臺的本質,以大量的肢體語言代替聲音語言來進行表達。但是肢體劇不等于啞劇,它可以沒有語言,也可以加入大段的對白。同時,雖然有不少肢體劇不使用服裝、布景、燈光,但并不代表肢體劇不能運用這類元素,肢體劇只是在整體上追求一種簡約的風格。
我有幸作為執行制作兼演員參與其中,在整個劇目的排演中受到了極大的啟發。該劇是中國現有舞臺表現形式的創新與開拓,以音樂為線索,將多種表演方式貫穿其中,另外,在舞臺上還有畫家的即興創作,與整個舞臺的情節、故事、氛圍融為一體。把看似南轅北轍的音樂風格也做了有機的結合,使音樂與演員的表演做到了無縫連接,使觀眾的代入感更加強烈。
本劇的前期表演訓練也不同于傳統的表演訓練。本劇的表演訓練更側重于內心發掘,并結合《觀呼吸》一書,進行靈性的探索與開拓,從身心冥想開始。宇宙萬物是生命能量的集合與轉換,觀看、照料好自己的呼吸,即身心調和,有利于進入【天人合一】的智性空間,進而洞見自性。相較于傳統教學表演,這是實現表演的最高境界,也是零表演的捷徑。傳統聲臺形表的終極意義是釋放天性,而洞見自性的過程包含但不限于解放天性,接近且超越【釋放靈魂】,類似于不拘泥社會人的屬性,回歸屬于宇宙生命的本我。這是表演創作角色的過程驚人相似。了解自我,放掉自我,融入角色,如何又不被角色吃掉,而能合理搭建與角色之間的關系,做到角色與表演者的高度一元的統一。通過內在觀想,聽見看見自己內在的宇宙空間,并導引出這個空間,讓其在肢體開發、肢體戲劇構作、聽覺表達、臺詞自由表達等一系列環節中得到最大限度的拓展。意隨心動,身隨意動。
另外,肢體部分的訓練也是在前期表演訓練中重要的組成部分。組織行動是表演最基礎也是最高級的技巧,通過這部劇的鍛煉和對于肢體上的開發,我了解了更多肢體的可能性。開始導演為大家賦予了“地、水、火、風”的屬性,讓大家根據自己的屬性找到自己的行為模式以及風格定位。利用音樂作為引導,把內心的情緒外化成肢體動作,并做出符合自己屬性的組織行動。前期冥想的鋪墊,使我們排除了雜念,更好地跟著音樂隨心而動,使肢體開發更加自然流暢。除了不同的個體開發外,我們之間也要互相建立肢體聯系及情感聯系。每個人做出的造型既是獨立成體,大家的整體造型也要成系,在后期的表演中更好把每個人所代表的部分有機結合。因為從本劇的故事角度來講,所有人飾演的角色都是由畫家一個人分化出來的不同情緒,因此建立“羈絆”才能有機地協調與統一,才能真正把人性外化到舞臺上來。
除了肢體方面,導演強調演員只作為本劇中的一個元素出現,這對于我來說是一種很新穎的形式,而且對于所有臺詞的節奏與音調都有很嚴格的要求;同時還要有抽離感,要體現整部劇的意識流,這不僅要求演員的感情充沛,還要求演員基本功的扎實,在規定的節奏(氣息是非常重要的)和音調中是否還能有充足的內心情感調動。我們知道,話劇表演不表現即不存在的基本特點,導演要求情緒精準把握,這也就要求了肢體外化的準確性。整臺演出如同一場演奏會,每個人都是一個聲部,每個人的配合都必須嚴絲合縫,演出之前導演還會讓臺上的演員一起調整呼吸,讓大家連結起來,這樣才會有更好的配合,并且為激情的調動創造環境。
本劇的音樂對于本劇的表演起了很大的引導性作用,本劇的所有表演節奏是與音樂節奏緊扣的,必須跟隨音樂節奏在規定的時間內完成表演。本劇的音樂風格多樣,有流行音樂、民謠彈唱、交響樂以及大鼓、京戲等各種元素,種類雖多,搭配起來卻并不違合,反而有一種舒服的協調性,統一感很強。不同的音樂配以不同的舞蹈形式與肢體表現形式,更好地詮釋出了本劇的東方魔幻主義色彩。
本劇分為四幕。第一幕講述了宇宙洪荒,生命伊始;第二幕講述了人世間的眾生相;第三幕講述了人性自身的糾結與掙扎;第四幕講述了時間寂滅,宇宙開始新一輪的輪回。
在劇中,我主要參演的是第二幕,飾演的角色是女人和佛僧。因為兩個角色同在第二幕,要迅速地進入角色與抽離角色。要會轉變聲調、狀態和肢體動作,不斷的角色間的過渡對于我的信念感也有很高的要求。
首先,我飾演的女人的角色是受到情感傷害女人的縮影,對于拋棄自己的畫家充滿了怨憤。臺詞傾向于控訴與宣泄,因此情緒比較激動,整個人處在失控的邊緣。可是這一場戲又是群戲,我只是幾個女人中的一個,是千千萬萬受傷女人的縮影,因此不能過分突出自己,要與整體的規定情景契合。因此,導演在此處的處理方法是按照個人不同的音色來安排不同的臺詞,一人一句,并把所有的臺詞串聯起來。所有女人們的臺詞就變得更有律動性與詩性,甚至是與交響樂有異曲同工之妙。既表現出了不同女人的不同性格與作用,也把一幅女人的眾生相呈現在舞臺上,尤其是最后眾女人圍著畫家一起高呼“愛情多么讓人盲目“,配合著一聲清冷的镲聲,將第二幕的氣氛推到了高潮,對于觀眾的的感官也產生了強烈的刺激,讓人不寒而栗。而在后面我飾演的佛僧就完全不同,此處的佛僧是一個冷眼觀看世間輪回的外星能量體。他不受時間空間的約束,我需要完成從人性到神性的迅速轉化。另外,佛僧的飾演者為兩個人。我是屬于形象上外化的佛僧,而另一位演員則是用肢體行動外化出“我“(即佛僧)的內心行動。因此,在舞臺形式展現上,我作為佛僧的外部軀殼是完全不能動的,包括說臺詞的時候。在燈光的配合下我站在幕布后面,打出三道長長的剪影,一個剪影在幕布上,另外兩個分別打在觀眾席兩側的墻上,給觀眾營造出脫離的空間感及緊張的氛圍。由于是剪影,稍微有些動作就會表現的特別明顯。因此,之前的呼吸訓練就起了很大的作用。調節呼吸使身心沉穩,冥想使自己排除雜念,給自己增加了更強的舞臺信念感。激烈情緒的臺詞跟另一位演員的舞蹈動作相結合,真正做到了我即是她,她即是我。體現了本劇“天人合一“的思想。此種表現手段也是導演對肢體戲劇的探索與嘗試,對于我們而言在表演技巧與能力上也有了一次質的飛躍與突破,開發了作為演員的更多可能性。
本劇作為肢體戲劇,對于舞臺也是有一定要求的。舞臺需要大而空曠才能夠更好地把肢體行動展現出來,另外,更重要的一點是聲音設計。本劇融入了京劇念白、大鼓等元素,又是現場演奏,只有符合條件的舞臺才能更好地把本劇的靈魂和精髓展現在觀眾面前。
還有本劇最為有特色的部分即為畫家現場作畫,畫家老師也是舞臺的一部分,雖然自己為獨立的板塊,卻也能有機地跟舞臺上的所有元素結合。另外,本劇男一號也是畫家,使觀眾在現實與夢幻中切換給人一種“莊周夢蝶,蝶夢莊周之感”。被物欲奴化,趨之若鶩的虛無追求讓生命失去靈魂,執著的藝術者在掙扎中徘徊在初心與墜落之間,愛的純粹與幻滅,境的邊界與亙遠,初始的瘋狂崇拜,末法的嘔人厭膩,信仰的淋血搏斗,靈魂的扼腕救贖。不瘋魔不成活,敢于質問命運的人才能掌握命運,敢于深陷泥潭的人才有拔靴自持的機會,回首一生便是窮極一生所念的那多一塵不染的蓮心。這就是《蓮心不染》給大家展現出的畫卷。
其實,肢體劇在歐洲當代已經發展成為非常普遍的一種表演藝術門類及表演藝術。英國著名戲劇家Peter brook在自己的著作《空的空間》中提到,舞臺在當代的創作意識中不應僅僅是服務于表演的載體,而應被視為一個環境空間,對于這個空間的再創造,解構與重構,會產生不可預知的無數可能性與自由度,這是當下真正能吸引觀眾第一視角的實有。
對于空間化舞臺的掌控與駕馭能力,在當代中國還是一個比較新鮮的藝術語匯。中國戲劇創作的新生代以及熱愛探索的前輩,他們創作的這類戲劇并不少,但是成功搬上舞臺,并有一定觀眾基礎的,十分罕見。一則源于大環境;二則,在我們的教學表演中,長期缺乏對肢體的深度開發,更談不上肢體戲劇的系統化訓練,更不要說創作、呈現一臺具有本土化語境的肢體戲劇作品了。因此,屈軼導演的《蓮心不染》也是一次探索和突破,希望我們新生代有更多的探索和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