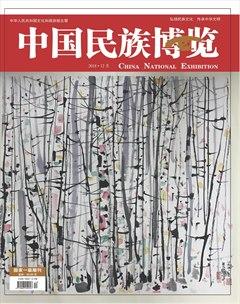視聽藝術下文牧野短片的現實主義
【摘要】文牧野是我國青年導演,曾拍攝短片《石頭》《金蘭桂芹》《BATTLE》和《安魂曲》,以及電影《我不是藥神》,并斬獲了多個獎項。他的作品十分關注社會小人物和特定群體,反映殘酷的社會現實中透露出樸素動人的溫情,無論拍攝手法還是鏡頭的處理運用都力圖更近距離地展現人物生活常態,在音樂和色彩這類輔助視聽敘事的功能運用上也有他自己可圈可點的特色。
【關鍵詞】文牧野;現實主義;社會群體
【中圖分類號】J905 【文獻標識碼】A
現實主義的本體性在于它在長期的歷史實踐中日漸積淀的規定性,即它的真實性、典型性和作為與其經濟基礎相適應的意識形態性。“真實性”是其原則,“典型化”是其方法,“意識形態性”則是其應有的功能,現實主義正是依靠這些本體性的顯現來實現它自身的審美價值。①電影本身自帶現實主義,電影可以直觀地展現影片人物的生活狀態,反映一定社會背景下的社會現實,以此揭示社會矛盾,引發大眾思考。本文將從視聽語言的角度分析文牧野短片作品的現實主義風格。
一、運用晃動鏡頭和密集剪輯貼近生活
剪輯方法通過對場面的分解,使觀眾在單場戲內注意到有戲劇意義的細節,從而刻畫出場景氣氛和人物細膩的心理。②而導演運用何種剪輯手法講述某一情節,甚至整體故事,并賦予其鮮活的現實質感,傳遞影片思想和引發社會意義價值討論,這在表現現實主義層面是很值得推敲的。
文牧野的前兩部短片《石頭》和《金蘭桂芹》主要是人情的塑造,在鏡頭處理上沒有使用太多的技法,但就是在這樣簡單的鏡頭畫面和敘事中更讓人體會到空巢老人生活的平淡和無奈,產生“由此及彼”的思考。《金蘭桂芹》開頭密集剪輯的生活鏡頭表現了兩個空巢老人彼此相依為命、互相照顧的狀態,以及穿插全片的大量略微晃動的手持鏡頭和特寫鏡頭都意在拉近觀眾與老人的距離,試圖以消除這種鏡頭距離的方式帶領觀眾貼近空巢老人的日常生活,貼近他們孤獨的內心。經過兩部小情節短片的歷練后,文牧野的第三部短片《BATTLE》在視聽和敘事方面更加精進了。《BATTLE》探討的是自由、信仰以及個體掙扎,在技術和主題上都比前兩部更有銳氣。該短片也獲得了第七屆FIRST青年電影展評委會特別獎和2013年度FIRST青年電影展拍片季優秀影片獎。《BATTLE》最大的特點就是文牧野第一次嘗試現實環境取景下的手持晃動攝影與快速剪輯。短片開頭便用了一連串的鏡頭展現主人公維族青年阿迪力的生活和工作日常,緊接著便用了長達八秒的抽煙鏡頭,從全景切到阿迪力迷茫焦躁的眼神特寫,揭示了阿迪力的“困境”:每天好似按部就班的工作,但其實內心是焦慮的,不知道自己的歸宿在哪里。在短片后半段阿迪力與兩個警察大打出手的場景,文牧野依然使用了手持拍攝,略微晃動的鏡頭將打斗的混亂感和緊張感十分真實地傳遞出來,最后定格的幾秒,阿迪力被制服的特寫鏡頭更是在鏡頭略微的晃動下將他所面臨的焦慮和無所依附的狀態極致地展現出來。
二、巧用音樂弱化劇情高潮,準確把控觀眾情緒
通常來講,現實主義題材中影視音樂的聽覺形象應與畫面的視覺形象相配合,以貼合影片整體風格,配合劇情所表達的情緒,盡量帶動觀眾回歸現實場景時的感情狀態。但是,文牧野反其道而行,沒有使用應景的音樂烘托畫面,而是試圖借助音樂使之冷靜化、客觀化,帶觀眾“脫離”劇情,只靜靜地觀看故事的進程。
文牧野的第四部短片《安魂曲》獲得了第12屆全球華語大學生影視獎、最佳劇情片和最佳創意獎以及第12屆亞洲國際短片電影節國際短片大獎,文牧野本人也憑借該片獲得了第6屆澳門國際電影節微電影大學生組澳天龍微電影導演大獎。也正是在他的這部畢業作品中,文牧野大膽地嘗試了悲情畫面和吉他音樂的組合。《安魂曲》講述的是本土化的故事:一家三口遭遇車禍,妻子當場死亡卻因無錢出殯無奈在太平間停放了一周,小女兒又因嚴重腦損傷急需進行手術,主人公自己也身受重傷瘸了一條腿。主人公為了能在一周內給女兒湊夠12萬元手術費,走投無路的他聽從了太平間管理員的建議,將妻子的遺體賣到農村,與一個剛剛死去的年輕人結成陰婚。在出殯那場戲,文牧野大膽地使用了吉他音樂,這與類似影片的傳統套路完全不同,在現實中也不符合大眾邏輯,但是短片題材本身的詭異性容許了這種反常搭配。畫面是交叉剪輯的:慢節奏的出殯隊伍、快節奏的送小女兒手術、慢節奏的主人公等待,再到慢節奏的出殯場。文牧野有意將這場高潮戲弱處理,出人意料的吉他音樂并沒有將觀眾的情緒推向高漲,反而使之冷靜、客觀。吉他音樂的運用很好地幫助了文牧野在盡情渲染悲情凄迷畫面的同時做到不挑撥、不刺激觀眾的聽覺神經,以至于觀眾的情感沒有得到一個情緒點從而爆發出來,使觀眾可以旁觀式的觀看這一過程。這也是導演的用心所在:讓觀眾看到并接受主人公從無奈和猶豫到最后平靜下來的精神過程,以及在生活的殘酷巨變中人物心態的慢慢變化。
三、采用慢鏡頭深化人物內心
在影視藝術中,時間是可以延長和縮短的。慢鏡頭的實質就是延長現實中的時間、延長實際運動的過程。在表現現實主義方面,慢鏡頭可以在放慢的節奏中引起人們的深思,創造抒情和深邃的藝術意境。文牧野的作品中出現慢鏡頭的次數雖不多,但也能看到他的獨到之處。
從文牧野早期短片中隱約能看到他運用慢鏡頭表現人物內心抉擇的意識。短片《石頭》中,在慢鏡頭敘述人狗睡同一張床墊時,雖然畫面是靜謐的,但表現的人物內心是糾結掙扎的:石頭因為尿道炎已經變的很虛弱了,主人公卻無錢再醫治它,最終決定將石頭送回鄉下。慢鏡頭在這里創造了表意抒情:在一人一狗的互相陪伴中,在時間的緩慢逝去中,主人公要對石頭的去留做出選擇。在《我不是藥神》中徐崢飾演的程勇第二次回到印度,從藥房出來看到漫天灑滿了迷霧,兩尊佛像被人運送著從他身邊走過,和時不時傳來的一陣鈴聲。渾濁不清的畫面里給了佛像多視角的仰拍和特寫,以及程勇茫然的看著眼前這一切的正反打鏡頭。慢鏡頭在這里放慢了此情此景下程勇內心的些許茫然和他最終決定賣藥救人的心理過程。而這種茫然蒼涼的場景也和《安魂曲》中被薄霧籠罩的出殯場景類似,慢鏡頭放慢了畫面節奏,但放大了人物內心搖擺不定的艱難選擇,慢鏡頭在這里抒發的其實是最強烈的內心情感,引發觀眾思考。
四、通過主題色彩彰顯主題
說到色彩不得不提到張藝謀導演,他曾說:“我認為在電影的視覺元素中,色彩是最能喚起人的情感波動的因素……我自己認為,從生理上說色彩是第一性的,能馬上喚起人的情緒波動”。③色彩確實是最具有感染力的語言,色彩可以巧妙地體現影視創作者的個人思考和情感傾向,具有獨特的象征意義。文牧野在色彩的使用上并不花哨,常常是采用一種主題色調貫穿全片。
《石頭》和《金蘭桂芹》通片都是暖色調的主題色彩。短片《石頭》雖然講的是小人物對故土復雜的情感,現代社會對底層人的擠壓以及由此引發的情感冷漠,但主人公因為有石頭這條狗的陪伴而不至于形單影只。暖黃色調更使得短片溫情滿滿,帶有治愈力量。《金蘭桂芹》更是如此,以喜劇的方式描繪出兩個空巢老人抱團取暖,主題色彩也是陽光照射下的暖黃色。兩個人一起去給電視繳費,以固定鏡頭全景拍攝兩個老人的背影,兩人左右并行前進,陽光灑在他們身上,灑滿整個畫面,色彩將此時的情感直觀地外化出來,讓人心生感動。在所有色彩中明度最低的是黑色,這類灰暗性的主題色被運用在《BATTLE》和《安魂曲》中。《BATTLE》講的是信仰與自我的歸宿,《安魂曲》是“以死換生”的靈魂掙扎。《BATTLE》的環境大多是陰暗潮濕的,主人公家里也是擁擠逼仄,短片整體氛圍是壓抑的,焦躁的,因此主題色也是陰郁昏暗,契合了主人公憂慮不安的內心。即使是父親到來,對話的背景色也是黑暗的,打光也是小范圍,外化了主人公內心自我的自由與信仰的無處安放。《安魂曲》中也是如此,文牧野在這部短片中使用了色彩對比來深化主題,短片從一開始就是灰暗色調,主人公的內心也是充滿著絕望:無錢安葬妻子、無錢給女兒做手術。全片唯一一次出現暖黃色是在主人公已去世的妻子“出現”在他眼前時的場景中,他對妻子做出承諾:“放心吧,我接彤彤”,并最終決定將妻子的遺體賣到農村。這種短暫的對比也說明了妻子和女兒是他生命里的光,即使生活遭遇重創,小人物也依然懷有希望。
五、追蹤現實的流動性引發思考
追蹤現實的變遷是現實主義電影的一個首要的美學特征。追蹤現實的變遷就要求創作主體能準確把握歷史階段性特征、有針對性地將時代的精神呈現出來,但是現實主義電影追蹤現實的流動性并不僅僅就當下問題而言,也可以是對某個歷史時期的審視。④文牧野在這方面做得很流暢,它的四部短片都在講述一定階段社會背景下小人物的生活狀態,引發觀眾對不同社會群體的關注和思考。《石頭》的主人公因拆遷進城又因狗狗生病回鄉,在這兩個進程中自然地進行時代發展下鄉村與城市兩種空間環境的對比,表現出主人公雖奮力打拼自己的未來,內心卻不知道歸宿的茫然,引發觀眾思考。《金蘭桂芹》通過兩個老人在給電視繳費路上的絮叨引出一個時代飛速發展背景下的空巢老人問題:老人得不到切實的照顧,她們該如何安度晚年?現實主義+人文關懷,再加入一種單純的、瞬間的觸動與思考,是《金蘭桂芹》和《石頭》的亮點所在。第三部的《BATTLE》用維族青年在北京打拼的故事揭示當代青年的焦慮:信仰與自我自由之間的迷茫。他想做點自己想做的事,在背上紋身,可父親卻告訴他:“這簡直是天大的褻瀆,安拉會詛咒你的。”《安魂曲》主人公突遭變故,在殘酷的現實面前,面對“以死換生”的不二抉擇,主人公的靈魂受到巨大折磨。這些都是文牧野綜合一系列人物的特征而創造出的某一種典型,它在劇情上追求“合情合理”,主人公心態的轉變和做出的選擇是由現實環境催生的。除了典型人物的刻畫,文牧野在作品中也融入了我們的“典型”文化。《安魂曲》讓我們看到了“冥婚”這樣的一種儀式的存在,《我不是藥神》中呂受益妻子敬程勇的一杯酒以及黃毛買的回家火車票等這些情節都有我們的文化在里面,這種通過對外部世界藝術的客觀描繪來填充細節的真實感也是文牧野的成功所在。
綜上所述,文牧野的現實主義是殘酷的,他在選擇故事視點上穩又狠。但他的人文關懷是溫情的,他可以生動地敘述人物的生活遭遇,讓人看到鮮活的個體和群體在社會現實中的傷口,卻不去聲討不去譴責,只是客觀地展現人間百態中的某一種生活情形。通過一個個故事去觸發觀眾思考:當我們在看遍了世態炎涼的時候,是否還愿意相信這個世界是好的。正如馬伯庸先生所說:“一部好的電影不一定解決一個問題,也可以是提出一個問題”。⑤而這些,文牧野都做到了。
注釋:
①于忠民.現實主義電影美學的現代性建構——讀沈義貞《現實主義電影美學研究》[J].藝術百家,2015(02):242.
②張菁,關玲.影視視聽語言(第2版)[M].北京: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 2014:117.
③孫中田.張藝謀的電影藝術謀略[J].東北師大學報,2000(01):35.
④李伊博.張楊電影的現實主義風格研究[D].長春:吉林大學,2015:28.
⑤曲展.“自我較勁”成就《我不是藥神》[J].綜藝報,2018(13):12.
參考文獻:
[1]趙芳.慢鏡頭的功用和作用[J].科教導刊(中旬刊),2011(2):166-167.
[2]張德林.關于現實主義創作美學特征的思考[J].文學評論,1988(6):87-96.
[3]沈義貞.現實主義電影美學研究[M].南京: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2(8).
[4]沈國芳,蔣俊,伏蓉.影視視聽語言[M].北京:國防工業出版社,2012.
作者簡介:賈賀鳴(1997-),女,河南鶴壁人,湖南科技學院2015級廣播電視編導學生,研究方向:視聽語言。
本文指導老師:龍運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