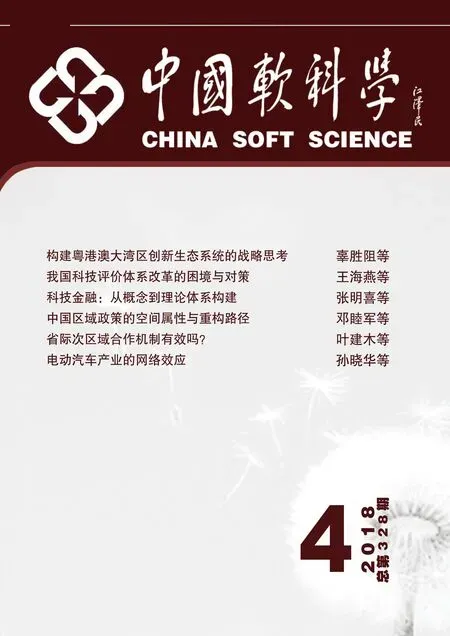心理授權對工程項目團隊不道德親組織行為的影響研究
——基于組織慣例的調節作用
孫春玲,姬 玉,許芝衛
(天津理工大學 管理學院,天津 300384)
一、引言
隨著我國建筑企業的快速持續發展以及團隊工作形態的日益成熟,組織和團隊成員之間良好的團隊合作意識和良好的倫理行為準則逐漸成為項目成功和組織績效提高的重要保障。鳳凰縣沱江大橋垮塌、西安地鐵施工塌方,甚至包括汶川地震很多校舍的坍塌等工程事故,表面上看是工程質量或管理問題,但究其根本是隱藏在“背后”的道德和倫理問題[1]。在建設過程中,承建單位收受賄賂擅自變更原設計施工方案,施工單位偷工減料、違反施工標準、盲目趕工期,監理及質監部門玩忽職守、權錢交易等等,從“直接表現”來看,可以把這些問題的出現歸結為技術問題、管理問題,或者是經濟問題等等,但是我們必須注意到在所有這些問題的“背后”都存在著“內在”的倫理問題,注意到這些問題產生的倫理本質是從根本上解決這些問題的有效方法[2]。
然而隨著建筑業競爭壓力的加劇以及受到傳統的“外延式、粗放式”發展方式的影響,工程項目外部環境的不確定性以及內部合約的不完備性使得施工單位常常面臨自然災害、工程變更等突發狀況,加之在工程建設中相對于業主所處的劣勢地位以及信息的不對稱性,這就迫使施工單位項目團隊成員更傾向于表現出一種不道德親組織行為(unethical pro-organization behavior,UPB)。UPB由于其隱蔽性往往給企業帶來無法預料的更為嚴重的傷害。UPB給組織帶來的收益具有短期性和表面性[3],工程項目團隊成員往往會出于維護組織當前利益、促進組織有效運作的動機而做出可能會暫時讓企業獲利的行為,但由于這種行為違背了倫理標準因而必然不具備可持續性,同時由于這種行為隱蔽和無法預計,最終會對項目造成不可控的巨大損失。
心理授權是團隊成員內隱行為的指引和潛在的工作動機[4],是親組織行為產生的基本來源。較高程度的心理授權會引發團隊成員較為強烈的內在動機,甚至會使團隊成員忽視了倫理標準而產生偏頗的親組織行為。組織慣例是實現組織柔性的主要因素,是位于組織制度之上的一種行為規范和內在認知,對于組織結構化和制度化起到約束作用,并且具有背景依賴性、嵌入性和特定性。在工程項目情境下,眾多項目參與方不僅需要履行合同中的權責利,還要遵守游離于正式制度之外的慣例,即在一定范圍內項目參與方經常采用的具有約束力的,能對不明確的合同條款進行補充的關系規范或習慣做法[5]。在建設項目組織中,這種慣例通過互利互惠的柔性約束形成一種延遲的、有道德約束的社會交換,激勵眾多項目參與方共同完成項目目標[6]。
對工程項目團隊成員UPB的研究可以幫助承包商認清此類行為及其危害,而對其驅動因素和調控因素的研究可以幫助承包商采取措施避免此類行為。目前,國內外學者對其影響因素和形成機制已進行了相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個體和領導層面[7-9],認為一些對組織有益的因素可導致UPB的產生,然而鮮有研究探討這些因素背后的心理根源。基于此,本文選擇了心理授權作為切入點,研究其對工程項目團隊成員UPB的影響機制,探究工程項目團隊組織慣例在其間發揮的作用,以期為承包商解決施工過程中項目團隊成員的道德約束問題提供借鑒。
二、文獻回顧與研究假設
(一)概念界定
(1)心理授權。本文認為心理授權是個體的心理感知或心理認知,是個體對自身所從事的工作價值感、影響力、責任感以及在組織中的重要性的心理狀態,包括能力、信念和工作等方面的感受,是一種非正式的內在激勵。工程項目團隊時常面對處于動態變化的不可控的復雜外部環境,應對劇烈變化的項目環境和靈活的工作流程需要團隊成員自主權,因此,工程管理領域這種動態變化的工作環境需要團隊成員擁有充分的授權感知才能更好地實現項目目標。較高程度的心理授權能夠增強工程項目團隊成員對組織的依附感和認同感,激發角色外親組織行為,但也可能迫使團隊成員忽視道德標準,從而采取不道德親組織行為。
(2)工程項目團隊成員不道德親組織行為界定。既有組織中有關自利的不道德行為的相關研究表明,員工的工作場所不道德行為廣泛存在于各級各類社會組織中,覆蓋商業組織、政府組織、學術組織等多種組織,并對組織的長期績效和持續發展產生不可估量的危害[10]。Umphress等學者首次將UPB從整體意義上的非倫理行為的概念中剝離出來,并進一步將其定義為那些意圖促進組織或其成員有效性但是違背社會核心價值、道德習俗、法律或合理行為標準的行為[11]。
工程項目團隊是為完成某一項目,由來自不同專業背景、技術特長的知識型員工所組建的臨時性的協同工作團隊,是承包商在項目上的施工管理團隊。根據Umphress等學者的定義,本文認為工程項目團隊成員UPB是基于項目外部環境不可控性、內部合約不完備性以及承包商所處的劣勢地位的特征影響下,團隊成員旨在維護組織利益、促進組織有效運作而有意識的自發行為。工程項目團隊UPB體現為趨利和避險兩種方式。趨利行為表現為工程項目團隊在做決策時往往更多地考慮企業的利益,主動幫助企業最大限度的地獲取利益。例如:由于承包商在投標報價中報了低價,造成利潤很少甚至無利可圖的狀況,就會在施工過程中偷工減料,對材料的采購也以次充好;承包商與設計單位合謀,利用設計變更獲取額外收益;承包商與監理單位合謀,更改施工方案獲取額外收益;承包商與業主(主要是房地產開發商這類本身存在不重視工程質量的業主)合謀以謀求利益最大化等等。而避險行為主要表現為工程項目團隊在處于信息不對稱的劣勢地位下,為了躲避風險或彌補不可抗力等因素帶來的損失而采取的維護企業利益的行為,而這種行為很有可能是違背道德、法律或合理行為標準的。例如:利用合同漏洞規避風險,在合同中增加不合理的風險轉移條款;在索賠事件發生時,工程項目團隊將費用報高以獲得更多的補償。
為了對工程項目團隊成員UPB的內涵有更深入的認識,對其特征概括如下:(1)是項目團隊成員有意識的自發行為;(2)出于維護組織利益、提升管理績效的目的;(3)沒有在正式的工作職責描述中規定,也沒有得到上級主管的命令;(4)從短期來看確實提升了企業收益,但從長遠角度來看造成了不良影響,損害了企業利益、破壞了企業形象。
(3)工程項目團隊組織慣例。Nelson和Winter指出慣例是企業在演化、競爭和創新的過程中,圍繞工作任務形成的有規律的、可預測的組織行為模式[12]。Feldman和Orlikowski將組織慣例定義為組織中多個行動者參與的、重復性的、具有連鎖順序的活動[13]。慣例的研究經歷了一個從個體層面轉移到群體和組織層面的過程,而組織合作層面的慣例也逐漸成為學者們所關注的焦點。
就慣例在某一個行業中的表現而言,已有部分研究試圖在厘清組織慣例的內涵特征的基礎上,研究其在不同情境下的具體行為。王永偉等認為行業慣例類似于基因一樣決定著行業的發展方向,是行業的一切規則和可以預測的行業行為[14]。Becker將慣例定義為交互的行為模式、組織的規則以及標準化的作業程序,能夠表達組織的行為、思想的行動部署[15]。Mantas認為組織慣例產生于個體行動的相互聯系,是一種集體現象[16]。嚴敏等學者指出行業慣例是行業內部從業者自發實施和遵循的默會慣例,是相對于正式制度而言的柔性約束[17]。基于此,本研究認為工程項目情境下組織慣例是指項目各參與方不斷的交互合作過程中形成的相對穩定的互利互惠的社會交換規范共識,并且以良好的項目績效為導向、被大部分參與方成員共同接受,具有嵌入性、路徑依賴性、變革性、適應性等特征。
王永偉等學者通過對組織慣例內在結構的研究強調了組織共識、組織規范和組織行為三個維度[18]。徐建平基于扎根理論和組織學習理論認為在中國情境下,組織慣例包含內隱規范、行動邏輯和交互共識三個維度[19]。由于組織慣例所具有的背景依賴性、嵌入性和特定性等特征,在工程項目背景下,組織慣例需要融入作為項目關系治理的特定情境,從而形成互利互惠、有道德約束的工程項目團隊組織慣例,以實現組織柔性約束。
(二)心理授權與不道德親組織行為
根據社會交換理論的互惠原則,不管是人與人之間或是人與組織之間,互惠原則都是潛在的交易規范,個體也會依據交互的性質做出不同的回應行為。研究發現,在社會交換關系中個體可以滿足自身情緒的需要,組織給予個體不僅是薪水報酬、職位發展,還有心靈上的滿足,例如尊重、承諾和信任等[20]。遵照這一邏輯,員工表現出親組織行為,不僅是為了履行雇傭義務,同時也是對組織或領導施予良好待遇的一種報答[21]。研究表明,提高心理授權程度,讓員工感受到自身工作的意義,給予員工更多的自我挑戰機會和決策權力,會大大增強員工對組織的依附感和認同感。員工的組織認同程度越高,就會越主動自愿地采取行動維護組織利益,甚至會在這種內部歸屬感的強烈動機支配下,降低自己的道德意識,選擇不道德的行為方式并且對其“合理性”進行辯護[22-23]。因而提高心理授權程度,有可能會使員工更多地關注于對組織和領導的報答,而忽略了這種報答行為是否會對組織以外的人造成不良影響。
此外,Aryee發現了心理授權與員工的離職率呈負相關,即能夠降低離職率[24]。學者Lavelle通過研究發現當員工擁有自主決策空間時,將會更愿意承擔責任,從而擺脫束縛形成良好積極性[25]。由此可以看出,在高程度的心理授權下,工程項目團隊成員會獲得更多的來自組織的信任和支持,形成一種內部人的身份認知,從而形成更高的組織認同水平和情感歸屬。此外,員工通過一系列的授權措施從內心真正體會到了工作意義,擁有了自我選擇的權力,認識到了自身工作對組織戰略發展的影響力。這些高水平的組織認同和心理上的滿足(作為組織給予員工的非物質獎勵),作為社會交換,員工愿意表現出更多的親組織行為。一些學者甚至認為,那些高度認同他們組織的個體可能會選擇忽視道德標準,從而采取使組織獲益但卻可能以損害組織外群體的利益為代價的行為。在某種意義上,強烈的組織認同可能會強迫員工放棄道德標準去采取表面上幫助組織的行為。
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認為在高程度的心理授權下,工程項目團隊成員表現出強烈的親組織行為意愿,但是這種意愿有可能會演化為不惜以損害組織外群體的利益為代價的行為,即UPB。由此,提出假設:
H1:心理授權與工程項目團隊成員UPB呈正相關。
H1a:工作意義與工程項目團隊成員UPB呈正相關;
H2a:勝任能力與工程項目團隊成員UPB呈正相關;
H3a:工作自主性與工程項目團隊成員UPB呈正相關;
H4a:影響力與工程項目團隊成員UPB呈正相關。
(三)組織慣例的調節作用
在以互利互惠為核心的慣例的作用下,在特定的社會關系網絡中形成了知識共享行為[26],項目各參與方之間的信任得到增強,工程項目的合作效率得到有效改進,從而使業主、承包商等項目參與方的總體收益增加,并且各協同合作方的關系得以鞏固。而項目各參與方是項目成功的關鍵因素[27],網絡成員關系的穩定能保證個體在可持續的基礎上互動[28],從而有助于眾多項目參與方的短期利益服從長遠利益,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機會主義行為發生的機率。由此可見,在工程項目團隊組織慣例的調節作用下,項目各參與方對非正式制度規則和社會價值觀的遵守漸漸成為了一種默認的慣性,這種慣性被各參與方所認同,產生一種行為自律。因此,在互惠互利的組織慣例影響下,工程項目團隊成員的情感型信任會得到增強,更多地考慮項目的整體利益,此時更有利于各方的合作。
而工程項目團隊組織慣例作為組織的柔性約束,是一種延遲的、有道德約束的社會交換,會在組織合作層面上促進各參與方合作關系的穩定性,從而促使團隊成員感知到道德偏差,對感性因素造成的道德偏移發揮調節作用。因此,提出假設:
H2:組織慣例負向調節心理授權對工程項目團隊成員UPB的影響。
綜上所述,本研究的模型見圖1所示。

圖1 心理授權對工程項目團隊成員UPB行為的影響機制模型
三、研究設計
(一)數據收集
本研究以中國大陸建筑業工程項目團隊成員為調查對象,采用問卷調查的方式進行數據收集。研究者于2016年11月至2017年2月期間進行調研,采用現場紙質填寫和電子版相結合的方式發放問卷,統一回收后進行篩選和分析。在調研過程中,研究人員主要負責向受訪團隊成員說明此次調研的目的,著重強調問卷的匿名性以及保密性,告知他們答案并無對錯之分,并對相關問卷填寫問題進行解答,以便保證所獲數據的可靠性和客觀性。此次調研共計發放問卷份235份,收回225份,剔除信息嚴重缺失、連續選擇同一個答案、答項前后矛盾等無效問卷后,得到有效問卷份192份,問卷有效回收率為85%,符合最終問卷數量為所答題項五倍以上的要求。通過對所收集的問卷進行分析,發現項目分散在湖北(9%)、西安(11%)、天津(17%)、北京(13%)、河北(14%)、青海(11%)、山東(16%)、海南(9%)等地。
(二)測量工具
本研究中所要測量的變量有三個,心理授權、不道德親組織行為、組織慣例。問卷所識別出來的初始指標制作,均采用Likert5點法度量,1表示非常不贊同,5表示非常贊同。各變量的量表來源和信度如下。①心理授權。采用Spreitzer提出的心理授權量表,包含4因子12個題項,本研究中該量表的Cronbach’s α值為0.839。②不道德親組織行為。采用Umphress研究中開發的UPB量表,但由于中西方組織情境的較大差異以及工程項目的特定工作情境,通過文獻分析和訪談的方法對原有量表進行了改編,使之更適用于中國情境下的工程項目團隊成員的研究,在預測試問卷中由于題項“為了幫助項目團隊,我愿意做任何事”相關系數小于0.5,因此刪除該題項,用其余6個題項進行測量,本研究中該量表的Cronbach’s α值為0.904。③組織慣例。借鑒徐建平對組織慣例的測量量表,通過文獻分析和訪談的方法對原有量表進行了改編。由于在工程項目情境下,受特定慣例的影響,工程項目團隊成員不會只考慮自身利益,而是會考慮到項目整體的利益,因此在工程項目團隊慣例中增加了互利互惠維度,使之更適用于中國情境下的工程項目團隊成員的研究。包含4因子14個題項,本研究中該量表的Cronbach’s α值為0.842。
四、數據分析與結果討論
(一)測量量表的信度和效度檢驗
本研究采用SPSS18.0對各變量進行探索性因子分析,檢驗其信度和效度,結果見表1。各變量的Cronbach’s α值均大于0.700,表明各變量具有較高的內部一致性,問卷具有良好的信度水平。
效度分析主要包括內容效度和構建效度。關于內容效度,研究中各變量的測量都是在回顧整理已有文獻的基礎上,結合本研究的特點并參考專家意見和調查對象的反饋進行適度修訂,因此變量量表具有良好的內容效度。關于構建效度,各變量題項的因子載荷均大于0.5,最終累積解釋方差均大于60%,符合標準。通過KMO和Bartlett球體檢驗,得到的各變量KMO值均大于0.7,表明這些題項能夠反映相關構念,收斂效度良好,Bartlett球度檢驗Sig顯著,表明數據樣本為正態分布,適合做因子分析。采用AMOS17.0進行驗證性因子分析檢驗各主要概念因子之間的區分效度,結果表明心理授權的四維度結構模型的擬合度較好,各擬合系數依次為χ2/df=2.626,低于3;RMSEA=0.092,處于0.08-0.10之間;GFI=0.905,AGFI=0.845,NFI=0.908,CFI=0.940,整體符合高于0.9的要求。心理授權、不道德親組織行為以及組織慣例三個量表的AVE值的平方根分別為0.748、0.749、0.735,各變量的相關系數分別在0.469-0.709之間,說明各變量AVE值平方根均大于其相關系數,表明具有較好的區別效度。

表1 探索性因子分析結果
本研究運用驗證性因子分析方法檢驗心理授權、組織慣例、不道德親組織行為3個潛變量的區分效度,擬合度指標見表2。對各個模型的擬合指數進行比較,結果表明,三因子模型擬合指標均達到了相應的標準,且明顯優于其他的備選模型。
(二)描述性統計分析
采用SPSS18.0對數據進行描述性統計分析,相關分析結果如表3所示。由表3可知,心理授權與不道德親組織行為顯著正相關,相關系數為0.709,在0.010水平上顯著相關,該結果為本研究的假設提供了初步支持。

表2 驗證性因子分析和共同方法偏差檢驗結果

表3 均值、標準差和相關系數
注:**為在0.010水平(雙側)上顯著相關,*為在0.050水平(雙側)上顯著相關。
由于問卷各變量數據采用自陳量表的形式,并且都是由同一調研對象提供,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偏差,盡管采用不同量表運用不同指導語言、匿名填寫等方法,但仍需檢驗共同方法偏差對研究結果的影響。首先,通過未經旋轉的探索性因子分析顯示有9個初始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被分析出,第一個因子占總方差的比例為30.734%,未占多數。然后,通過驗證性因子分析進行多個模型間的比較(見表2),單因子模型擬合較差,而三因子模型能夠較好擬合。通過上述方法驗證,可判斷不存在共同方法偏差的影響。
(三)研究假設的驗證結果
(1)心理授權與不道德親組織行為的關聯關系
運用SPSS18.0對心理授權與不道德親組織行為的主效應進行檢驗,輸出結果中的標準化系數作為評價工作意義、勝任能力、工作自主性、影響力與不道德親組織行為的相關程度,見表4。結果表明,工作意義與不道德親組織行為的相關系數為0.053,勝任能力與不道德親組織行為的相關系數為0.097,工作自主性與不道德親組織行為的相關系數為0.261(p<0.01),影響力與不道德親組織行為的相關系數為0.503(p<0.01)。表明工作自主性、影響力都對不道德親組織行為具有顯著正向作用,雖然在回歸分析中工作意義、勝任能力未達顯著水平,但其與“不道德親組織行為”變量的積差相關系數分別為0.403(p=0.000)及0.394(p=0.000),均達到顯著的正相關,且其相關程度為中度關系。表明工作意義、勝任能力、工作自主性和影響力都對團隊成員不道德親組織行為有正向作用,假設H1及其子假設成立。

表4 心理授權對不道德親組織行為影響的回歸分析
注:*表示p〈0.05顯著,**表示p〈0.01顯著,***表示p〈0.001顯著,下同。
(2)組織慣例的調節效應檢驗
表5模型2考察組織慣例在心理授權與不道德親組織行為關系中的調節作用,將心理授權與組織慣例中心化后的交互項對不道德親組織行為進行回歸檢驗,發現組織慣例在兩者之間的調節效應顯著,β=-1.494,在0.050水平上顯著相關,H2得到驗證。由圖2可知,與行業慣例使用明顯的情況相比,行業慣例使用不明顯時工程項目團隊成員在面對心理授權時更愿意從事不道德親組織行為(其回歸直線處于上方),表明在心理授權程度同等變化的情況下,組織慣例使用不明顯時,工程項目團隊成員更傾向于選擇不道德親組織行為來回報組織的心理授權。

表5 調節效應的層次回歸結果

圖2 組織慣例對心理授權與工程項目團隊成員不道德親組織行為關系的調節作用
五、研究結論與管理啟示
(一)研究結論
本研究在工程項目情境下,以社會交換理論為依據,構建并檢驗心理授權對于工程項目團隊成員UPB關系的影響模型,考察組織慣例在上述兩者關系中的調節機制,研究結果表明:①心理授權對工程項目團隊成員UPB存在顯著正向影響,其中工作自主性和影響力這兩個維度對團隊成員UPB的正向影響更為顯著;②組織慣例負向調節心理授權對工程項目團隊成員UPB的正向影響。
通過對192名工程項目團隊成員數據進行實證檢驗表明,在工程實踐中高程度的心理授權確實是激發團隊成員從事UPB的重要因素。研究發現,心理授權各維度都對團隊成員UPB存在正向影響,而工作自主性和影響力這兩個維度相較于其它兩個維度具有更為顯著的正向影響。表明高程度的心理授權能夠激發團隊成員的內在工作動機,使其認識到自身工作意義的重要,相信自己有能力完成某項任務,并且認為自己對組織的戰略和管理工作有重要的影響作用,產生更大的信心運用組織資源和把控組織的發展,從而產生強烈的組織認同感和依附感。而這種高度的認同感有可能迫使他們放棄道德標準去采取表面上幫助組織的UPB。
工程項目由于其外部環境的不可控性和內部合約的不完備性,需要團隊成員做出更多積極的角色外行為以利于項目成功,而較高程度的心理授權水平能夠激發團隊成員的自我效能,使其體驗到更多的自主性、控制感,從而會更積極主動地做出有利于項目成功的角色外行為。在工程項目情境下,工作自主性和影響力相較于工作意義和勝任能力更能使團隊成員產生對組織戰略和管理工作的重要影響,由此產生相對更強烈的組織認同感和依附感,從而在這種內部歸屬感的強烈動機支配下,降低自己的道德意識,選擇不道德的行為方式自愿主動采取行動維護組織利益,甚至對其“合理化”。工程項目團隊組織慣例作為一種柔性約束受到互利互惠的慣例的影響,在一定程度上能夠降低機會主義行為的發生機率。也就是說,組織慣例能夠有效地調節心理授權對UPB的作用,越顯著地使用正面的組織慣例,團隊成員在感知到更高程度的心理授權時,越傾向于產生有益的角色外行為,從而抑制UPB的產生。研究結果不僅為心理授權與UPB的關系提供了有力的新證據,同時也為理解心理授權對工程項目團隊成員負面行為影響的心理機制提供了新的視角。
(二)管理啟示
本研究的相關結論可以為國內工程項目管理實踐提供一些有意義的啟示和參考,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1)工程項目團隊管理者與團隊成員應充分警惕UPB產生的原因及負面影響。受工程項目組織間激烈的競爭以及傳統的粗放式發展方式的影響,工程項目團隊成員在表現出更強的親組織行為意愿的同時往往不惜以損害組織外群體的利益為代價。UPB短期內、表面上會使組織受益,但實則終將對項目造成巨大損失,同時對承包商企業的聲譽和合法性帶來巨大的傷害。因此,工程項目團隊管理者應具有長遠的戰略視角,不能為了短期內、表面上的利益而忽視甚至是默許團隊成員實施UPB。工程項目團隊組織應該樹立正確的倫理取向,促使團隊成員提高自身的道德水準,更加清晰地審視自身行為,有效避免組織制度設計缺陷以及個體行為作用扭曲。
(2)工程項目團隊管理者應充分重視心理授權的負面影響帶來的弊端。本研究發現,雖然較高程度的心理授權能夠促進工程項目團隊成員的親組織行為,但是團隊成員為了回報組織的心理授權、避免組織受到傷害,可能會選擇忽視道德標準,從而采取使組織獲益但卻可能以損害組織外群體的利益為代價的行為。在某種意義上,高程度的心理授權能夠促使工程項目團隊成員產生強烈的組織認同感,從而可能會促使團隊成員放棄道德標準去采取表面上幫助組織的行為。因此,工程項目團隊管理者在對下屬進行高水平的心理授權時,應該以高道德標準引導團隊成員行事,充分發揮心理授權的積極作用,減少其消極作用,鼓勵團隊成員采取互惠性質的組織公民行為來為組織做出貢獻。同時,工程項目團隊管理者應積極構建有道德的企業文化,通過營造良好的企業道德氛圍引導團隊成員做出有利于企業長遠利益和項目整體利益的行為。
(3)應充分重視組織慣例對心理授權和工程項目團隊成員UPB的負向調節關系。工程項目團隊組織慣例是圍繞工作任務形成的有規律的、可預測的組織行為模式,是組織成員在長期實踐中處理相似問題時自發考慮組織以往實踐所接受的不成文的規范,最終形成集體性的默契、共識和觀念。在工程項目情境下,組織慣例會受到項目治理特定情境的慣例的影響,使得團隊成員在工作實踐中不僅考慮自身利益,還會考慮到項目整體的利益。因此,在這種互利互惠的組織慣例影響下,成員之間情感型信任會得到增強、更有利于雙方的合作,減少了機會主義行為。從而形成一種延遲的、有道德約束的社會交換,有效調節了團隊成員的道德偏差。由于建筑工程需要隨時應付各種臨時狀況和新增事件,因此柔性的組織慣例在建筑業的運轉中發揮了非常重要的潤滑作用。鑒于此,工程項目團隊管理者應強化互利互惠的組織慣例的調節作用和對UPB的抑制作用。
參考文獻:
[1]曾小春,胡賢文.工程項目管理中的倫理風險與防范[J].中國軟科學,2002(6):123-125.
[2]李伯聰.工程與倫理的互滲與對話——再談關于工程倫理學的若干問題[J].華中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4):71-75.
[3]張桂平.職場排斥對員工親組織性非倫理行為的影響機制研究[J].管理科學,2016,4(29):104-114.
[4]魏 峰,袁 欣,邸 楊.交易型領導、團隊授權氛圍和心理授權影響下屬創新績效的跨層次研究[J].管理世界,2009(4):135-142.
[5]何伯森.工程項目管理的國際慣例[M].北京: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2007.
[6]馮必揚.人情社會與契約社會——基于社會交換理論的視角[J].社會科學,2011(9):67-75.
[7]Graham K A, Ziegert J C, Capitano J. The effect of leadership style, framing, and promotion regulatory focus on unethical pro-organizational behavior [J].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2015, 126(3):423-436.
[8]EffelsbergD A, Solga M.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 in-group versus out-group orientation: Testing the link between leader’s organizational identification, their willingness to engage in unethical pro-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follower-perceived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J].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2015, 126(4):581-590.
[9]李根強.倫理型領導、組織認同與員工親組織非倫理行為:特質調節焦點的調節作用[J].科學學與科學技術管理,2016,12(37):125-135.
[10]譚亞莉,廖建橋,王淑紅.工作場所員工費倫理行為研究評述與展望[J].外國經濟與管理,2012,3(34):40-48.
[11]Umphress E E, Bingham J B, Marie S M. Unethical behavior in the name of the company: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organizational identification [J].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2010, 95(4):769-780.
[12]Nelson R, Winter S. An evolutionary theory of economic change [M]. MA: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1982.
[13]Feldman M S, Orlikowski W J. Theorizing practice and practicing theory [J]. Organization Science, 2011, 22(5): 1240-1253.
[14]王永偉, 馬 潔. 基于組織慣例、行業慣例視角的企業技術創新選擇研究[J].南開管理評論,2011(14): 85-90.
[15]Becker M C, Zirpoli F. Applying organizational routines in analyzing the behavior of organizations [J].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2008, 66(1): 128-148.
[16]Mantas Vilkas. The effects of exogenous change on interaction patterns among members of organizational routines [J]. Procedia-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2014,156:135-140.
[17]嚴 敏,嚴 玲,鄧嬌嬌.行業慣例、關系規范與合作行為:基于建設項目組織的研究[J].華東經濟管理,2015,29(8):165-174.
[18]王永偉,馬 潔,吳湘繁,等.新技術導入、組織慣例更新、企業競爭力研究——基于諾基亞、蘋果案例對比研究[J].科學學與科學技術管理, 2012,33(11):150-159.
[19]徐建平.組織慣例的演化機制與效能研究:基于學習視角[D].杭州: 浙江大學, 2009.
[20]Rhoades L, Eisenberger R, Fasolo P, et al. Perceived organizational support and police performance: The moderating influence of social motional needs [J].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1998, 83(2): 288-297.
[21]Umphress E E, Bingham J B. When employees Do bad things for good reasons: Examining unethical pro-organizational behaviors [J]. Organization Science, 2011, 22(3): 621-640.
[22]Dejun Tony Kong. The pathway to unethical pro-organizational behavior: Organizational identification as a joint function of work passion and trait mindfulness [J].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2016, 93: 86-91.
[23]Conroy S, Henle C A, Shore L. Where there is light, there is dark: A review of the detrimental outcomes of high organizational identification [J].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2017, 2(38):184-203.
[24]Aryee S, Chen Z X. Leader-member exchange in a Chinese context: Antecedents, the mediating role of psychological empowerment and outcomes [J].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2006, 59(6): 793-801.
[25]Lavelle J J, Brockner J, Konovsky M A, et al. Commitment, procedural fairness, and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 A multifocal analysis [J].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2009, 30(7): 337-357.
[26]尚淑秀,張再生.基于社會資本視角的虛擬企業知識共享[J].中國軟科學, 2013(11):101-111.
[27]丁榮貴,王金安,孫 華, 等.項目利益相關方社會網絡邊界確定方法研究[J].軟科學,2015,8(29):124-128.
[28]孫永磊,陳 勁,宋 晶.文化情境差異下雙元慣例的作用研究[J].科學學研究,2015,9(33):1424-14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