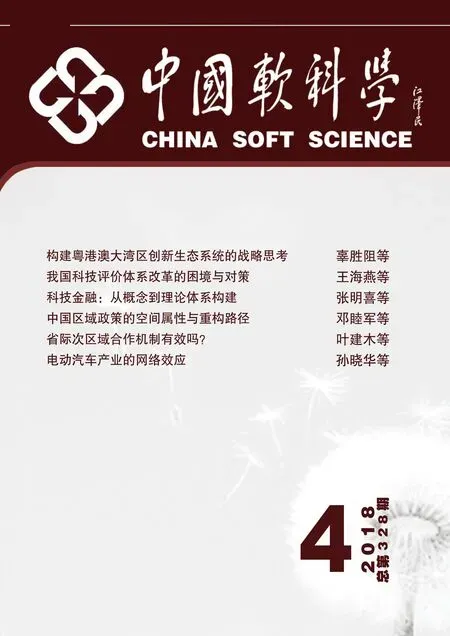精準扶貧背景下旅游扶貧效率研究
——以湖北大別山區(qū)為例
孫春雷,張明善
(湖南大學 工商管理學院,湖南 長沙 410082)
一、引言
2012年,國務院公布的《中國農村扶貧開發(fā)綱要》將我國的貧困地區(qū)劃分為14個集中連片特殊困難地區(qū)。自此,我國扶貧工作開始了“重點出擊,各個擊破”的階段。自從2013年習總書記提出精準扶貧以來,我國長期堅持實施的扶貧工程進入精細化階段,精準扶貧對目前的扶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黨的十九大報告對于如何利用精準扶貧,決勝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戰(zhàn)略目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015年,國家旅游局和國務院扶貧辦提出了“五年目標”,即在5年時間內,以旅游為扶貧手段,減少至少16.9%的貧困人口。這也就是說需要幫助1100萬的貧困人口通過旅游實現(xiàn)脫貧。尤其是在某些旅游資源稟賦優(yōu)異的省市,旅游扶貧實現(xiàn)的脫貧人數占全省市貧困人數的20%。
當前我國精準扶貧到了最為關鍵的時刻,如何充分發(fā)揮不同的精準扶貧手段,實現(xiàn)2020年脫貧摘帽,從而全面實現(xiàn)小康社會的戰(zhàn)略目標,是當前需要重點解決的課題。因此探索不同的精準扶貧路徑并評價這些扶貧路徑的效率十分關鍵,意義重大。
旅游扶貧是精準扶貧的主要路徑,在旅游以各種各樣的方式助力扶貧的同時,扶貧同樣也不斷讓旅游的發(fā)展空間變得更為寬廣。在我國貧困地區(qū)與旅游資源的分布有著極高的重合性。數據顯示:我國有超過70%以上的優(yōu)質資源分布在老少邊窮等貧困地區(qū);在全國820多個國家級貧困縣中,與落后的經濟發(fā)展和閉塞的地理區(qū)位相對應的是,大部分都擁有著品級極佳的旅游資源[1]。扶貧政策的落地,為當地旅游發(fā)展改善了基礎條件,提供了發(fā)展和保護生態(tài)環(huán)境的經濟支持,同時也為實現(xiàn)這些地區(qū)脫貧提供了現(xiàn)實的可能。
因此,基于此背景,本文以精準扶貧為研究視角,實證檢驗分析旅游扶貧的效率和質量。從而為提升旅游扶貧的應用價值及針對不同特征的貧困地區(qū),有效地探索旅游發(fā)展模式,及時脫貧提供有價值的策略和建議。
二、湖北大別山區(qū)旅游扶貧效率DEA實證分析
(一)對象選取與數據來源
2015年,《大別山革命老區(qū)振興發(fā)展規(guī)劃》由國務院牽頭發(fā)布,結合規(guī)劃中提到的大別山試驗區(qū)的8個縣市,本文依據旅游資源的優(yōu)劣程度,剔除不具備3A級資質以上景區(qū)的新洲區(qū)、云夢縣、廣水市、團風縣、黃梅縣等地,本文所指的湖北大別山區(qū)域為黃州、浠水、紅安、羅田、麻城、英山、蘄春、大悟、孝昌、孝南、安陸、應城、曾都、隨縣、棗陽和黃陂等16個縣市區(qū)。本文所選的湖北大別山16個縣市區(qū)在旅游扶貧方面極具代表性,研究得出的結論同樣具有普適性。
對比于其他地區(qū),從自然旅游資源來看,有40%的森林覆蓋率,區(qū)域內山川廣布、河湖成片,生態(tài)環(huán)境良好。從人文旅游資源來看,大別山地區(qū)的革命遺址、名人故居等紅色旅游資源數量多、分布廣,在中部地區(qū)尤為突出。
DEA方法最終測算出來的結果是否具有現(xiàn)實意義,是否有效都取決于選擇的測量指標是否科學合理,是否具有代表性[2]。一般情況下,選取DEA指標有三個方面的要求。第一是科學性:投入要素與產出要素之間必須有因果聯(lián)系,且評價指標體系與各縣市的旅游扶貧效率之間必須有內在的邏輯關系。第二是可靠性:指標本身的來源必須是第一手調查資料、可靠的期刊雜志或者官方統(tǒng)計資料,而且必須使用專業(yè)術語。第三是數據量化:指標可以追溯源頭,有實際的檔案數據可以查驗,并且數據可以量化。
另外,DEA 方法中對于決策單元的數量有著硬性的要求,DMU 個數必須大于投入指標與產出指標之積的兩倍;本研究中,DMU個數=16,產出指標個數= 2,投入指標個數=3,而16﹥2(2*3),符合要求。
對于產出指標體系,貧困是描述居民生活狀態(tài)的詞匯,于是選取了歷年脫貧人口數量。旅游扶貧是旅游產業(yè)對當地經濟的帶動,貧困人口的收入可以直接反映當地扶貧的效果,因此選擇貧困人口收入作為產出指標。由此,產出指標體系由貧困人口收入和歷年脫貧人口數量構成。由于需要評價的是旅游對經濟的扶貧效應,對于投入指標體系需要選取旅游發(fā)展各方面投入的指標,地方人均旅游收入可以大致描繪旅游業(yè)發(fā)展的成果效應,人均旅游接待人次可以衡量當地的旅游吸引力和接待能力。與此同時,扶貧資金投入則可以直接衡量政府在旅游扶貧方面的專項投入。考慮到與產出指標體系的對應關系,選取政府扶貧資金投入、人均旅游接待人次和人均旅游收入構成投入指標體系。數據來源于2011-2015年湖北大別山區(qū)16個縣市政府工作報告與歷年國民經濟與社會發(fā)展統(tǒng)計公報,湖北省人民政府扶貧開發(fā)辦公室統(tǒng)計數據。
(二)Super-DEA超效率分析[3]
本文利用DEA-SOLVER Pro 5.0,計算出2011年—2015年間,湖北大別山區(qū)16個縣市和區(qū)旅游扶貧超效率,結果如表1。
從整體情況上看,從2011年起,湖北大別山區(qū)域大部分縣市和區(qū)都保持在中高水平的階段,一直到2015年,湖北大別山16縣市的旅游扶貧效率一直都保持在中高水平的階段。從時間關系上看,從2011年開始,湖北大別山16縣市的旅游扶貧效率經歷了先下降后上升的變化過程。說明在初期階段,各種生產資料的配置情況經歷了一個探索的過程。在湖北大別山區(qū)域16個縣市中,麻城、蘄春、棗陽、黃陂均出現(xiàn)了連續(xù)幾年完全有效的情況,占所有縣市的25%。從以上的情況可以看出,在湖北大別山區(qū)域之內僅僅只有幾個縣市能夠達到生產的最佳前沿面上,換言之,就是達到了產出最大化。
從各個縣市的情況上看,在湖北大別山區(qū)16個縣市中,蘄春縣2011-2015年旅游扶貧效率平均值最高,其中五年均達到了DEA有效。在2016年度,蘄春縣有120個村被列入全國鄉(xiāng)村旅游扶貧重點村,每一個扶貧重點村的目標都是旅游營業(yè)收入每年能夠達到100萬元,這些重點村占全縣所有行政村的20%。在2014年和2015年期間,在湖北大別山區(qū)16縣市中蘄春縣的脫貧人數最多,其旅游收入增幅分別為70%和35%,在大別山區(qū)中占據首位。5年來,蘄春縣依托李時珍故居、國家地理標志保護產品蘄艾,堅持打好人文和保健牌,蘄春縣旅游扶貧效果顯著,在大別山區(qū)內形成一定的示范效應。
(三)規(guī)模報酬階段解讀
在DEA模型中,判斷規(guī)模報酬階段主要是對兩個前提條件下的情況進行對比:第一個是旅游扶貧規(guī)模收益不變,第二個是在規(guī)模收益非增條件下的效率。規(guī)模遞減階段是指規(guī)模效率非增條件下的效率>規(guī)模收益不變條件下的效率,此時,說明旅游扶貧的發(fā)展已經無法消化旅游扶貧的投入要素[4]。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需要減少旅游扶貧要素的投入規(guī)模。而規(guī)模遞增階段則恰恰相反,是指規(guī)模效率非增條件下的效率<規(guī)模收益不變條件下的效率,此時,說明旅游扶貧的要素還沒有達到最為優(yōu)化的規(guī)模,需要進一步加大旅游扶貧的要素投入。湖北大別山區(qū)規(guī)模報酬階段一覽表如表2所示。

表1 湖北大別山區(qū)縣市旅游扶貧超效率計算結果

表2 湖北大別山區(qū)規(guī)模報酬階段一覽表
注:Increasing表示規(guī)模報酬遞增,Decreasing表示規(guī)模報酬遞減,Constant表示規(guī)模報酬不變
以2015年為例,浠水、紅安、麻城、英山、蘄春、應城、曾都、棗陽、黃陂均屬于規(guī)模報酬不變的階段,黃州、羅田、大悟、孝昌、孝南、安陸均屬于規(guī)模報酬遞增的階段,僅隨縣處于規(guī)模報酬遞減階段。說明湖北大別山16個縣市旅游扶貧的最大效益還沒有完全發(fā)揮出來,大多數縣市可以繼續(xù)增加旅游扶貧資金等投入要素,仍然存在較大的上升空間。
(四)Malmquist指數動態(tài)分析
由于Malmquist生產率指數可以判斷出當年的旅游扶貧效率與上一年相比的變化情況,能夠對湖北大別山區(qū)16個縣市旅游扶貧效率進行動態(tài)變化的分析[5]。本文采用MI指數來對湖北大別山區(qū)的16個縣市歷年旅游效率的變化情況進行判斷。
基于2011—2015年大別山區(qū)的原始數據,采用MI方法,利用DEA-SOLVER Pro5.0軟件計算出2011—2015年大別山區(qū)16縣市的旅游扶貧DEA效率變化程度,如表3所示。
從時間維度來看,2011—2015年湖北省大別山各縣市旅游扶貧效率大小不斷變化。在全部的80個數據中,共有26個數據小于1,占到全部數據的32.5%;共有54個數據大于1,占到全部數據的67.5%。說明大部分情況下,大別山16個縣市和區(qū)的效率每年均有增長。

表3 湖北大別山區(qū)旅游扶貧效率MI指數
旅游扶貧效率在5年時間內變化較為明顯的有:羅田縣的MI從2012年的0.514上升到2013年的1.043,英山的旅游扶貧效率MI從2011年的0.790上升到2012年的1.261。一般來講,旅游效率增長的高低會受到目標地區(qū)本身經濟基礎、經濟發(fā)展的快慢程度、一二三產業(yè)的分布情況、技術使用是否足夠廣泛和深入等。對于旅游扶貧的縣市而言,扶貧效率增長快速主要分為兩種情況。第一種情況是,縣市本身旅游扶貧效率不高,旅游資源本身不夠豐富,經濟基礎較為薄弱,技術使用程度較低。但由于直接借鑒了先進地區(qū)的經驗與方法,能夠保持較為快速的增長率。第二種情況是,縣市本身的旅游扶貧效率較高,說明旅游資源稟賦優(yōu)異,旅游產業(yè)健康發(fā)展,在旅游發(fā)展生命周期進入鞏固期之后,采取了相應的措施,例如調整產業(yè)發(fā)展戰(zhàn)略、采用先進科學技術等等方式,另一部分縣市則恰恰相反。
由數據可以看出,大別山區(qū)在開展旅游扶貧之初,經歷了一段時間的探索磨合期。而后的幾年,大別山區(qū)旅游產業(yè)發(fā)展能夠充分合理配置各種資源,發(fā)揮最大的效益,改善當地人民生活質量,提高經濟發(fā)展水平,極其顯著地解決了當地一部分貧困人口的脫貧問題。
(五)效率形態(tài)類別分類
針對旅游效率的評價可以從絕對數和相對數兩方面進行,從而對湖北大別山區(qū)的16個縣市進行動態(tài)效率形態(tài)類別的分類。本文主要講其分為4種類型:Ⅰ型,Ⅱ型,Ⅲ型,Ⅳ型。為了區(qū)分出各種形態(tài)的臨界值,本文將湖北大別山區(qū)5年間的DEA平均值0.860設置為橫坐標的臨界值[6],將MI為1設置為縱坐標的臨界值。由此,劃分出四種類型,如圖1和表4所示。
由表4可以將大別山16縣市的綜合效率-效率變化率劃分為4種類型,根據2011—2015年各縣市的綜合效率和效率變化率的高低不等,將其劃分為穩(wěn)定、漸進、往復三種旅游扶貧效率演變模式。
穩(wěn)定式演變模式:是指在5年間,絕大部分時間的綜合效率——效率變化率處在同一個象限內變化。在大別山區(qū)16縣市中,有浠水、應城、曾都和棗陽屬于穩(wěn)定型演變模式。其中,浠水縣一直保持在第二象限,每年的旅游綜合效率和MI變化率均保持在高水平上。說明浠水縣在2011—2015年的時間內,憑借其優(yōu)異的旅游資源稟賦,在其轄區(qū)內旅游產業(yè)的發(fā)展極大地發(fā)揮了扶貧作用。浠水、應城、曾都、棗陽在2011—2015年始終保持在第二象限,綜合效率高——MI變化率高的階段。說明這四個地區(qū)一直以來,依托當地旅游資源,有效帶動了當地貧困人口的脫貧。

圖1 綜合效率-效率變化率分布圖

縣市2011年2012年2013年2014年2015年演變模式黃州ⅣⅡⅢⅢⅠ———浠水ⅡⅡⅡⅡⅡ穩(wěn)定紅安ⅢⅢⅠⅢⅠ漸進羅田ⅣⅢⅠⅠⅠ漸進麻城ⅣⅡⅡⅡⅡ漸進英山ⅢⅡⅢⅢⅠ———蘄春ⅣⅡⅡⅡⅡ漸進大悟ⅣⅢⅢⅢⅠ———孝昌ⅠⅠⅢⅠⅠ往復孝南ⅡⅡⅡⅣⅡ往復安陸ⅠⅠⅡⅡⅡ漸進應城ⅡⅡⅡⅡⅡ穩(wěn)定曾都ⅡⅡⅡⅡⅡ穩(wěn)定隨縣ⅠⅡⅣⅢⅡ———棗陽ⅡⅡⅡⅡⅡ穩(wěn)定黃陂ⅣⅡⅡⅣⅡ往復
漸進式演變模式:是指在5年時間內,綜合效率——效率變化率主要從一個象限轉移到另一個象限,相對平穩(wěn)過渡的情況。在湖北大別山區(qū)16縣市中,有紅安、羅田、麻城、蘄春、安陸屬于漸進式演變模式。紅安縣、羅田縣從第三象限逐漸演進到第一象限,說明這兩個縣市在5年時間內,逐漸從綜合效率低——MI變化率低演進到綜合效率低——MI變化率高的階段,即旅游扶貧的綜合效率的變化趨向是歷年不斷增長。麻城、蘄春和安陸則逐漸演進到了綜合效率高——MI變化率高的第二象限。
往復式演變模式:是指在5年時間內,從一個象限到另一個象限之間循環(huán)往復變化的情況。在湖北大別山區(qū)16個縣市中,有孝昌、孝南和黃陂屬于往復式演變模式。孝昌從第一象限到第三象限之間往復,說明其MI變化值時高時低不穩(wěn)定。孝南縣和黃陂區(qū)總體情況偏好,雖然屬于往復式演變,但其綜合效率總體而言一直保持在較高的狀態(tài)。
其余縣市在5年之間內的演變情況無明顯規(guī)律,需要加長觀察年限后進行觀察和論證。
三、湖北大別山區(qū)旅游扶貧模式選擇及發(fā)展對策
由于湖北大別山區(qū)16個縣市的旅游扶貧效率與旅游資源分布的情況不同,大別山區(qū)內16個縣市適宜采用的旅游扶貧模式也會有所差異。本文根據各個縣市5年來旅游扶貧效率和其動態(tài)演變的情況,將大別山16個縣市分為了雙低型地區(qū)、朝陽型地區(qū)、黃金型地區(qū)和潛力型地區(qū),并探索了不同類型地區(qū)的典型特征和旅游扶貧發(fā)展對策。
(一)雙低型地區(qū)——產業(yè)聯(lián)動模式
1.雙低型地區(qū)特征與模式選擇
雙低型地區(qū)在湖北大別山區(qū)16個縣市中處于較低的發(fā)展水平,其旅游扶貧效率低,且每一年的旅游扶貧效率增量小,甚至逐年遞減。造成旅游扶貧效果不佳的原因既有當地旅游資源稟賦不夠優(yōu)異,旅游接待能力不強,也有當地貧困人口參與旅游程度較低,未從旅游產業(yè)的發(fā)展中獲益等等因素。
雙低型地區(qū)旅游業(yè)發(fā)展和起步較晚的區(qū)域,旅游扶貧還處于探索階段,貧困人口從旅游發(fā)展中獲得效益的情況還不明顯。這一類地區(qū)一方面需要加大旅游扶貧的投入,例如地方旅游扶貧專項資金等;另一方面,則需要借鑒其他基礎條件類似的區(qū)域的成功經驗,來不斷提高自身的旅游扶貧效率。
這一類的縣市,旅游產業(yè)自身發(fā)展可能先天不足,所謂旅游產業(yè)“獨善其身”“單打獨斗”肯定是行不通,也無法帶動當地貧困人口致富。因此,可以融合區(qū)域內其他優(yōu)勢產業(yè)的發(fā)展來實現(xiàn)“產業(yè)聯(lián)動”,例如依托其他產業(yè)來降低旅游產業(yè)發(fā)展的經濟要素成本,發(fā)揮各產業(yè)的優(yōu)勢,實現(xiàn)1+1>2的效果,適用于產業(yè)聯(lián)動型旅游扶貧模式。
2.雙低型地區(qū)旅游扶貧發(fā)展對策
在施行“產業(yè)聯(lián)動型”的旅游扶貧開發(fā)策略的時候,要注意精準劃分產業(yè)主導部門的職責權限。避免在產業(yè)聯(lián)動過程中相關部門因利益沖突等問題出現(xiàn)監(jiān)管不周、逃避責任等問題;要注意加強產業(yè)結構的轉型升級,保障產業(yè)結構比例的協(xié)調發(fā)展,避免因旅游扶貧開發(fā)造成的產業(yè)結構失衡問題。
(二)朝陽型地區(qū)——區(qū)域聯(lián)合模式
1.朝陽型地區(qū)特征與模式選擇
在大別山16縣市中,有羅田、紅安、孝昌、安陸為朝陽型地區(qū)。羅田縣的地形可以以“八山一水一分田”來概括。正因為如此,羅田縣耕地面積小,土地肥沃程度低。長期以來,羅田縣都名列全國貧困縣名單。其中,天堂寨、九資河和進士河漂流在華中地區(qū)屬于優(yōu)質資源。精準扶貧目前已經被編入了羅田縣十三五規(guī)劃中,并確立了3.7萬貧困戶和12萬貧困人口脫貧的年度任務。
紅安縣在2016年由政府牽頭創(chuàng)建“全省旅游精準扶貧示范區(qū)”。在行政層面上確定了30多個旅游扶貧村,將旅游精準扶貧落實到戶。最近的一個階段,紅安縣的旅游扶貧主要通過兩種途徑:第一是旅游+鄉(xiāng)村,紅安縣土壤獨特,盛產花生和紅薯,土特產銷售成為鄉(xiāng)村+旅游的切入口;第二是旅游+體育,依托當地的山岳和湖泊,開展對天河漂流旅游、攀巖旅游等體育旅游項目。
孝昌縣境內有多處古代墓葬遺址,具有開發(fā)歷史遺址旅游的先天優(yōu)勢。同樣的,在擁有高質量的旅游資源的同時,孝昌縣也連年無法擺脫“貧困”這一頂帽子。2016年,孝昌縣共有34個村入選國家鄉(xiāng)村旅游扶貧重點村。2015年的統(tǒng)計資料顯示,孝昌縣城鎮(zhèn)人均可支配收入為湖北大別山16個縣市的末位。同時,由于大悟縣和孝昌縣均為國家級重點貧困縣,社會經濟水平較低,交通通達性有待于進一步提升。從地理空間上來看,孝昌縣在湖北大別山區(qū)16個縣市中最為接近武漢市和黃岡市,非常適合開展區(qū)域聯(lián)合旅游扶貧的開發(fā)與合作。
安陸市,在全省范圍內屬于旅游開發(fā)較早的縣市。近年來安陸市,將主要精力放在了旅游扶貧資金的規(guī)范運作和整合旅游資源進行大項目投資上,其中古銀杏國家公園和白兆山旅游風景區(qū)均屬于成功的精準旅游扶貧項目案例。另一方面,安陸市占據地理區(qū)位的優(yōu)勢,是鄂西生態(tài)文化旅游圈的重要門戶城市,因此,在聯(lián)合發(fā)展中需要注意調和各方的利益,實現(xiàn)各個區(qū)域的共贏乃至多贏。
綜合來看,這類地區(qū)的典型特點是社會經濟條件較差,但旅游資源稟賦度相對較高。與其他區(qū)域相比,該區(qū)域產業(yè)結構單一化,經濟效益低,旅游扶貧開展缺乏最基本的基礎條件。必須依托周邊地區(qū)旅游資源稟賦優(yōu)異的縣市,尋求區(qū)域合作。采用“區(qū)域整合模式”為主體扶貧模式,與周邊縣市共同開發(fā)旅游資源,擴大旅游發(fā)展的規(guī)模,產生規(guī)模效應和聚集效應,來提高整個區(qū)域的旅游市場競爭力。
2.朝陽型地區(qū)旅游扶貧發(fā)展對策
朝陽型縣市的主要類型分布在Ⅰ型,即旅游扶貧效率低——扶貧效率變化率高的類型。這一類型的縣市呈現(xiàn)出旅游綜合效率低下,但是每一年都處于逐漸增長的形勢。從整體趨勢和前人的研究結果上看來,這一類的縣市一般情況下都會緩慢的演進到第二象限中。這一類型的縣市應當采取緩進式的策略,即在保持區(qū)內的各項行政層面的策略等外部環(huán)境不變的情況之下,逐步加大旅游扶貧要素的投入,例如增加旅游專項扶貧資金,加大貧困人口在旅游開發(fā)過程中的參與等等,來確保旅游扶貧效率的穩(wěn)定增長,促使其漸進式發(fā)展到Ⅱ型。
另一方面,在實行“區(qū)域聯(lián)動模式”的過程中,要注意避免將“沿勢開發(fā)”異化為“附勢開發(fā)”,即在借助大區(qū)域旅游扶貧開發(fā)福射效應的同吋,能長期依附于大區(qū)域的開發(fā)模式,而失去本區(qū)域的特色性開發(fā);要堅持在區(qū)域整合過程中不斷加強自身能力的建設,在學習中提升,進而實現(xiàn)該區(qū)域旅游扶貧的“跨越式發(fā)展”。與此同時,由于跨區(qū)域的精準扶貧涉及到資金等方面的問題,因此在操作過程中需要堅持陽光操作管理、農戶信息管理和扶貧事權管理。通過建立扶貧項目庫,公開旅游扶貧資金的使用,讓貧困人口切實享受到旅游精準扶貧的幫扶措施。
(三)黃金型地區(qū)——政企合作模式
1.黃金型地區(qū)特征與模式選擇
在湖北大別山區(qū)16個縣市中,浠水、應城、曾都和棗陽屬于此種類型。
浠水縣是湖北省精準扶貧攻堅戰(zhàn)的重要區(qū)域之一,長期以來浠水縣,都存在著大量的貧困人口,貧困范圍大,程度深。數據顯示,2016年浠水縣仍有97個貧困村,13.7萬貧困人口,占全縣總人數的11.5%,屬于貧困的重災區(qū)。在省政府和市政府的指導之下,浠水縣制定下了在2018年全面消除貧困的目標。浠水縣山清水秀,旅游資源豐富多樣,山岳資源有4A級景區(qū)三角山,濕地資源有望天湖和白蓮河水庫,通過旅游的發(fā)展,浠水縣已經有一大部分貧困人口脫貧。旅游扶貧將成為浠水縣精準扶貧攻堅戰(zhàn)的有力武器。
應城市在2014年的精準識別對象的基礎之上,在2015-2016年組織拉網式摸底調查。數據顯示,應城市目前貧困村共58個,貧困人口共1.7萬人,占全市人口的2.4%,說明應城市貧困程度一般,經濟基礎較好,在旅游扶貧的過程中,能夠提供更好的基礎條件。應城市主要以湯池溫泉為龍頭,吸納當地貧困人口參與旅游產業(yè)扶貧。除此之外,應城市還積極延長旅游產業(yè)鏈,將當地的土特產包裝打造成本地旅游特產,提升產品附加值,創(chuàng)造機會將貧困人口帶入到旅游發(fā)展中。
曾都區(qū)距離市區(qū)較近,可以吸引市區(qū)客源,同時具有良好的經濟基礎和硬件設施。目前,曾都區(qū)主要采取政企合作、重點項目建設的措施,不斷推進旅游精準扶貧。其中,千年銀杏谷經過專家規(guī)劃,前瞻性建設了永久停車場和游客服務中心,完善基礎設施。另一方面,深入推進精準扶貧攻堅工程,堅持旅游扶貧到戶,開展打造“城邊路邊”農家樂旅游帶。引導曾都區(qū)周邊的萬店、何店、北郊等鎮(zhèn)、辦事處、管委會發(fā)展鄉(xiāng)村休閑旅游,促進農民增收和城鄉(xiāng)一體化建設,促進鄉(xiāng)村旅游長足發(fā)展。
麻城市旅游產業(yè)發(fā)展起步較早,在2017年政府工作會議上,確定了完成31個貧困村、8488名貧困村民的脫貧;堅持精準扶貧項目資金到戶的原則,每年設立不低于2000萬元的旅游專項基金,并以節(jié)事活動不斷豐富旅游產品,吸引貧困人口參與扶貧,并確立了以農家樂發(fā)展作為旅游扶貧開發(fā)主線的戰(zhàn)略,對貧困人口參與組織的農家樂給予每年1萬元的標準補貼,堅持精準扶貧資金到戶。
黃金型地區(qū)在進行旅游開發(fā)的時候,適宜采用“政企合作”的模式。這類縣市目前旅游扶貧效率處于較好的狀態(tài),綜合效率值高,且每一年都處于增長的態(tài)勢。雖然目前的情況較好,但是黃金型地區(qū)的未來發(fā)展?jié)摿Σ⒉粡姡枰3肿≥^高的綜合效率和低速增長的良好狀態(tài),否則就很容易進入停滯期或者是倒退期。這一類地區(qū)旅游開發(fā)已經進入了鼎盛時期,后續(xù)的開發(fā)潛力并不大,需要政府層面進行宏觀引導,避免步入資源開發(fā)殆盡之后的倒退期。從旅游扶貧的成效來看,這一部分縣市目前的旅游發(fā)展有效地帶動了貧困人口的脫貧,并且其扶貧之后脫貧人口數量和貧困人口的收入在逐年增大。
2.黃金型地區(qū)旅游扶貧發(fā)展對策
旅游扶貧效果的好壞離不開當地旅游資源的品質,同時,也與當地的政府支持力度息息相關。政府主導、企業(yè)合作的模式不僅可以在行政層面為旅游精準扶貧提供良好的政策環(huán)境和戰(zhàn)略指引,同時也能夠最大程度解決由于信息不對稱引起的“市場失靈”現(xiàn)象。因此,這類縣市應當不斷調整三大產業(yè)的分布與構成,改善旅游扶貧投入要素的針對性與合理性。
此類地區(qū)有兩點需要注意,首先,政府必須對引進的企業(yè)進行有效的甄別,引進本身具有資金實力、市場運作經驗和先進管理理念的企業(yè)。而且引進的企業(yè)并不是多多益善,而是需要堅持適度原則,根據當地的旅游資源情況,客源市場情況做出綜合分析,既要滿足當地精準旅游扶貧的需求,防止出現(xiàn)旅游漏損,又要有一定的良性競爭來促進企業(yè)的健康發(fā)展。其次,政府并非在引進了適量的企業(yè)之后,便可以高枕無憂。政府只有明確規(guī)定,企業(yè)必須利用當地原材料,在雇傭的員工中有固定比例的當地貧困人口,并保證在管理崗位中有一定數量的當地居民,才能夠保護當地經濟的優(yōu)先發(fā)展,行程當地的產業(yè)循環(huán)。
(四)潛力型地區(qū)——項目支撐模式
1.潛力型地區(qū)特征與模式選擇
在湖北大別山區(qū)16個縣市中,有麻城、蘄春、孝南、隨縣和黃陂屬于此類情況。
麻城憑借其優(yōu)越的地理位置和豐富的土地資源,相較之下?lián)碛辛肆己玫慕洕l(fā)展基礎。除此之外,麻城市旅游局近幾年在A級景區(qū)評審申報上面取得了很好的成績,目前麻城市境內有一大批4A和3A景區(qū)。自2008年以來“人間四月天,麻城看杜鵑”便成為了麻城市旅游的引爆點。麻城市被譽為中國杜鵑花之城,每年春夏季節(jié),為麻城市吸引著成千上萬的省內外游客紛至沓來。旅游業(yè)的騰飛直接激活了麻城市其他關聯(lián)產業(yè)。曾經長期名列國家級貧困縣名單的麻城,也因為旅游產業(yè)的發(fā)展,每年帶動大量貧困人口脫貧。自國家戰(zhàn)略層面提出精準扶貧以來,麻城市旅游扶貧找到了新的發(fā)展方向。2015年,麻城市提出了《麻城市旅游產業(yè)精準扶貧工作實施方案》,實施“3138工程”,詳細規(guī)劃了精準旅游扶貧資金的分配與使用,其中規(guī)劃幫扶3000戶貧困戶參與旅游產業(yè)鏈。
蘄春縣是湖北大別山連片貧困特區(qū)的“頑疾”之一,蘄春縣目前有136個貧困村,有14.4萬貧困人口,貧困人口占到全縣農業(yè)人口的17.65%。從地形上看,蘄春縣大部分地區(qū)處于山地地形,交通不便。交通的便捷程度直接影響著外界信息交流、思想觀念的開放和致富路徑的多寡,正因為如此,出現(xiàn)了路邊村富裕,山區(qū)村貧困的聚集現(xiàn)象。蘄春縣發(fā)展旅游以來,打通了村與村之間的交通聯(lián)系,縣級政府利用旅游專項資金來培育旅游產業(yè)的發(fā)展,在研究自身旅游資源優(yōu)勢的前提之下,逐漸形成了“藥旅聯(lián)動”的養(yǎng)生旅游產業(yè)發(fā)展路徑。旅游的發(fā)展帶來了交通的便利,也拉動了蘄春縣山區(qū)村的經濟發(fā)展,貧困人口不用再背井離鄉(xiāng)遠赴省外一線城市謀求生路,在家門口就能夠就業(yè),就好業(yè)。旅游精準扶貧成為蘄春縣脫貧致富的重要途徑之一,旅游產業(yè)正全力推進著蘄春縣實現(xiàn)2018年貧困摘帽的終極目標。
孝南區(qū)是孝感市唯一的兩個貧困縣(區(qū))之一,孝南區(qū)也長期名列湖北省十大貧困縣和國家級貧困縣。孝南區(qū)距離孝感市市中心距離近,擁有著經濟基礎好、基礎設施完善、客源充足等旅游發(fā)展的優(yōu)勢。孝南區(qū)依托“董永故里,孝德名城”的旅游形象,圍繞孝感市和武漢市開發(fā)都市周邊鄉(xiāng)村旅游,是實現(xiàn)旅游精準扶貧的方向之一。
隨縣一縣的貧困人口占據整個隨州市貧困人口的41%,集中了全市大部分的貧困人口。與此相對應的是隨縣豐富的旅游資源。隨縣憑借炎帝神農故里的旅游資源,極大帶動了當地貧困人口的脫貧致富。
黃陂在旅游扶貧的發(fā)展方面起步較早,為了加快轉變經濟發(fā)展方式,黃陂區(qū)一直以來都將旅游作為實施精準扶貧的重要支柱產業(yè)來抓,其中,黃陂的北部地區(qū)經過精心的特色打造,已經形成了旅游名鎮(zhèn),并且形成輻射效應,完成了貧困人口的就地轉城鎮(zhèn)化。在2016年年底,黃陂區(qū)城鎮(zhèn)化達到了50%以上。另外,黃陂區(qū)的農家樂星級評定、休閑農莊星級評定等都已經走在了全省的前列。黃陂通過“村景融合、農旅結合、精準扶貧”的方式大力發(fā)展鄉(xiāng)村旅游,就近吸引武漢市的游客實現(xiàn)了全區(qū)的旅游產業(yè)脫貧致富。
潛力型地區(qū)的典型特點是旅游綜合效率高,但是變化率低。經過多年的綜合結果來看,這一類型中的許多地區(qū)在進入第四象限之前,都是從第二象限演變而來[7]。這一類型的縣市的特征是旅游扶貧的綜合效率比較高,但是MI變化值低于1,說明其旅游扶貧是逐年遞減的。并且據觀察來看,這一類的縣市往往是從綜合效率高——歷年遞增的黃金型地區(qū)演變而來。究其原因,這類地區(qū)往往旅游開發(fā)較早,目前旅游資源已經開發(fā)殆盡。最好的辦法是開拓出新的旅游扶貧發(fā)展的增長極,這一類型的地區(qū)比較適合采用項目支撐的模式,將旅游扶貧的發(fā)展從依靠旅游資源中解放出來,以項目為驅動,靈活運作。讓項目的發(fā)展處在可控范圍之內,讓項目的經濟效益能夠惠及貧困人口。
2.潛力型地區(qū)旅游扶貧發(fā)展對策
潛力型地區(qū)在旅游開發(fā)扶貧的過程中,適應于采用“項目支撐型”的模式。在目前已有的旅游開發(fā)布局之下,從景區(qū)依賴型向項目驅動型轉變,擺脫在旅游扶貧過程中的旅游資源依賴性。要積極與國家政府組織、非政府組織建立關系,通過相關的項目對旅游開發(fā)者和當地社區(qū)居民形成一個強有力的監(jiān)督管理體制,從而有效約束開發(fā)者與受益者的行為。這一類型的區(qū)域在實行“項目支撐模式”的過程中,要注意有效控制好項目驅動的度,在為貧困地區(qū)提供項目支撐的同時,需要注意的是不能夠過分依賴項目,且在利益分配的過程中,需要政府發(fā)揮宏觀調控作用,將貧困人口納入利益分配體系中。
參考文獻:
[1]查建平, 王挺之. 環(huán)境約束條件下景區(qū)旅游效率與旅游生產率評估[J]. 中國人口·資源與環(huán)境, 2015(5):92-99.
[2]曹芳東, 黃震方, 徐 敏,等. 風景名勝區(qū)旅游效率及其分解效率的時空格局與影響因素:基于Bootstrap-DEA模型的分析方法[J]. 地理研究, 2015, 34(12):2395-2408.
[3]李忠斌, 肖博華, LIZhong-bin,等. “一帶一路”省區(qū)文化旅游產業(yè)效率研究:基于PCA-DEA組合模型[J]. 廣西師范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16, 37(2):42-47.
[4]王耀斌, 孫傳玲, 蔣金萍. 基于三階段DEA模型的文化旅游效率與實證研究:以甘肅省為例[J]. 資源開發(fā)與市場, 2016, 32(1):125-128.
[5]張大鵬, 鄧愛民, 李鶯莉. 基于DEA-MI模型的資源枯竭型城市旅游業(yè)效率評價研究[J]. 宏觀經濟研究, 2015(9):117-126.
[6]王恩旭, 吳 荻, 匡海波. 基于標準離差-G1-DEA的旅游機場競爭力與效率差異性評價的對比研究[J]. 科研管理, 2016, 37(2):152-160.
[7]唐 睿, 馮學鋼, 周 成. “絲綢之路經濟帶”入境旅游市場效率研究:基于西北五省(區(qū))DEA-面板Tobit的實證[J]. 國際經貿探索, 2017(7):4-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