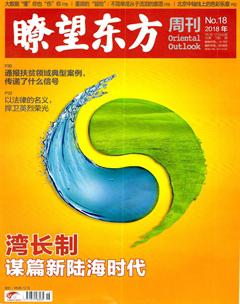曹娥江的陶瓷業為何凋敝
鄭嘉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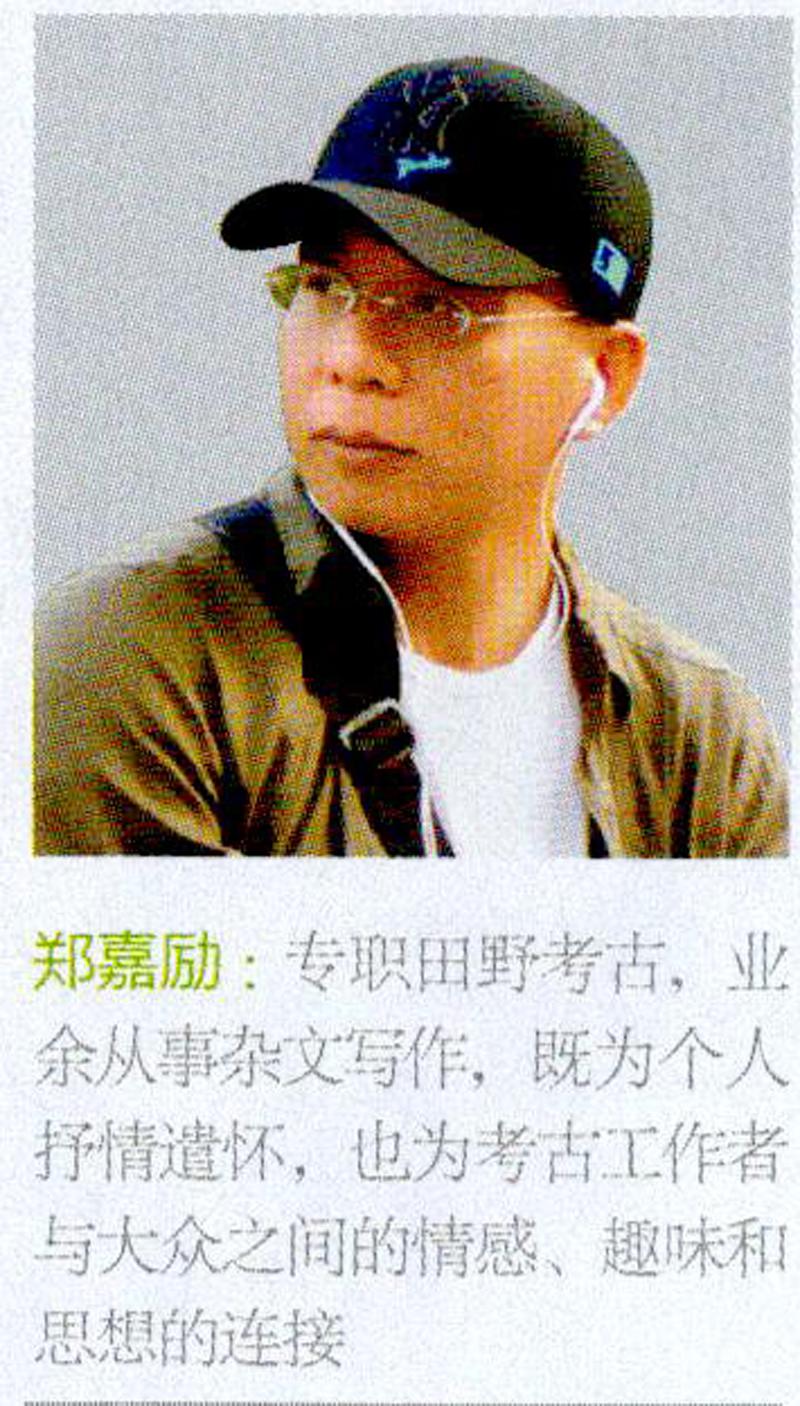
進入東晉后,當地的青瓷生產為何突然衰落
曹娥江上游,發源于浙中的山區,中游流經嵊州、上虞的低山丘陵,進入下游的水網平原,最終歸于大海。
曹娥江中游地區,即自今上虞縣南部上浦鎮至嵊州北部一線,山水清嘉,沃野千里。在嵊州境內,曹娥江有個詩意的名字——剡溪,古典文學愛好者,也許不陌生。東漢永建四年(129),在上虞縣南鄉、剡縣(今嵊州)北部,置有始寧縣。
漢六朝時期,上虞、始寧兩縣乃人文薈萃之地。投江救父的孝女曹娥、今日尊為“唯物主義思想家”的王充,都是上虞人;謝安隱居的東山,謝靈運的莊園“始寧墅”。均在始寧縣。
上溯至剡溪,故事就更多了。“雪夜訪戴”——王羲之的兒子王子猷,居山陰,夜大雪,忽然想起遠在剡縣的友人戴逵,連夜乘舟前往,好不容易到了戴家門口,卻又轉身返回。人問其故,王子猷說:“我本乘興而來,而今興致巳盡,又何必見他呢?”
“舊時王謝”的故事,當然有說頭,可惜缺乏考古實物證據。在考古學家看來,曹娥江中游兩岸稱為“六朝勝地”,只因為此地有密集的漢六朝墓地,更有當時規模最大、品質最高的青瓷窯址群。
這里是漢六朝越窯青瓷的中心產區,上浦鎮石浦村四峰山的小仙壇窯址,所出青瓷,釉色瑩潤、胎骨堅致、胎釉結合緊密、吸水率低,被學術界公認為“成熟青瓷誕生地”而載入史冊。如今的小仙壇,地表已經撿不到瓷片了,只有一旁矗立的文物保護碑,說明這是中國最早燒造成熟瓷器的地方。
四峰山的青瓷確實好,2004年我在小仙壇附近的大圓坪發掘窯址,出土的東漢瓷器,論胎釉,論造型,比我兒時鄉下老家使用的粗瓷大碗強多了。
三國西晉時期,青瓷生產又有長足進步,臻于鼎盛階段。窯址數量多,生產規模大,瓷器品質高,工藝復雜。2006年,我在上浦發掘的尼姑婆山三國西晉窯址,代表了當時曹娥江流域與中國青瓷生產的最高水準,前來現場考察的古陶瓷專家無不贊嘆。
窯場通常分布在依山傍水的低山緩坡。燒窯需要燃料,制瓷需要瓷土,生產與運輸需要水源,龍窯建造需要利用低山的自然坡度。這些條件,曹娥江下游平原、上游山區并不具備,唯有中游兩岸的低山丘陵,天造地設,適宜建窯制瓷。自東漢至西晉,青瓷作為本土的傳統產業,獨步海內。
然而,當歷史進入東晉后,當地的青瓷生產突然衰落,規模萎縮,窯址數量銳減;質量滑坡,復雜的器物,精美的裝飾,消失不見。
很多越窯研究者為此傷神。我在尼姑婆山窯址工作時,白天發掘,晚上躺在床頭想,到底什么原因?莫非東晉時候,松木砍光了,瓷土耗盡了,曹娥江水干了?
后來我終于“推測”出一個原因,興奮得幾天沒睡著。
東漢、三國、西晉時期,陶瓷本是曹娥江流域的傳統產業。西晉“永嘉之亂”后,中原大亂,北方世族、“舊時王謝”南遷,引發江南地區政治、經濟、文化領域內的巨變。
東晉時期,曹娥江流域逐漸為北方世族占據,傳說謝安隱居東山,王羲之寓居剡縣,謝玄、謝靈運祖孫占籍始寧,均為其例。他們憑借政治特權,每至一地,“封山占水”,開辟莊園。謝靈運《山居賦》描述的“始寧墅”,偌大的莊園,沿著曹娥江,南北綿延四十里,山峰河川、田園阡陌、茂林修竹、飛禽走獸、園林別業,應有盡有——新辟的莊園,多在依山傍水之處,正是此前本地人燒窯的地方。
北人占領山澤,禁止他人砍柴捕魚,遑論取土燒窯。正如《宋書》所言,“晉自中興以來,權門并兼,強弱相凌,百姓流離,不得保其業”,北人的到來,造成無數土著百姓的破產。瓷器是土著的傳統產業,而殖民者來自毫無制瓷傳統的北方,其“封山占水”造成陶瓷業的凋敝。
以上看法,未敢自是,勉強可以自圓其說。這就是考古學的魅力,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猜錯了,古人也不會跳出來還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