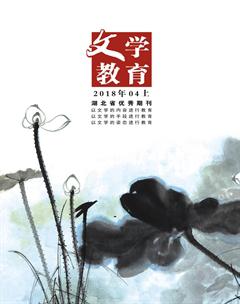評邵麗的《蔣近魯的藝術人生》
在邵麗的創作中,《蔣近魯的藝術人生》當屬于“掛職小說”或曰“官場小說”之列。她的這一系列作品歷來受到關注和研究,被稱為是通過官場來呈現多元化經驗的現實主義書寫。這種獨特的寫作既來自于她的生活經歷,也來自于她對自我經驗的藝術提煉。
與傳統的“官場小說”和20世紀90年代“新現實主義”涉及這一題材的作品不同,邵麗關注的不是官場生態和官員生活,因此也無意于書寫所謂“貪污腐敗、魚肉百姓、作惡多端、牢獄之災”等固化的官場故事。由于她的作家身份與掛職期間作為外來者、旁觀者的視角,她的小說多涉及與人性維度、文化記憶和性別經驗相關的書寫,《我的生活質量》、《劉萬福案件》、《明惠的圣誕》等均有此特質。
《蔣近魯的藝術人生》以“我”作為掛職副縣長的身份展開敘事。在“我”掛職的天中縣,老蔣任縣委書記。他雖為官員,卻無陳腐氣息。一上臺就大刀闊斧,立意招商引資,造福當地百姓。這樣富有情懷與膽識的官員形象我們曾經在新時期的“改革文學”中見到過,“改革”的陣痛、創新的阻滯、新舊的交替,常常作為小說中激烈的矛盾化和戲劇化而將敘事不斷向前推進,它們帶來暢快的閱讀經驗,不過也很容易落入以歷史進化論取代個人觀察的價值觀窠臼。
當然,在距離“改革文學”已經三十余年的今天,邵麗不可能再像當年的蔣子龍、張潔、柯云路等人那樣去寫官員,而另有其敘事法則與考量。一方面,她以詳細的筆墨鋪敘老蔣引發爭議的種種不“按套路”出牌的言行,比如公開歧視女性官員、提拔敢于擔當的下屬、反復折磨看中的干部、全力包裝貧瘠的旅游資源、干凈利落地收拾盤根錯節的國有企業……諸如此類,從多個側面、多個層次刻畫了一個“很少顧及別人的感受,而對自己的感受卻格外看重”的官場“異類”。另一方面,作者在情節的推進中,不斷摻入“我”與老蔣的數次不那么愉快的交道,或者“我”從旁人那兒聽到的老蔣傳聞,輔以第一人稱敘事者的感想與議論,疊床架屋地皴染出一個豐富生動的人物形象。
作者以蔣近魯在官場令人眼花繚亂的“行為藝術”將他的人生立體化、多面化地呈現出來。值得注意的是,小說的題目不是蔣近魯的“官場人生”,而是“藝術人生”。那么,他的“藝術”表現在何處呢?小說在開頭和結尾兩個部分點染出了他為數不多的“藝術行為”:書法與攝影。他在書法上“不入流”,卻自我感覺相當良好,且必須在掌聲與喝彩中完成書法,否則決絕扔筆而去;他的攝影作品還“不錯”,舉辦的攝影展有那么一些藝術品味,雖然前來參觀和奉獻諛詞的大都是他的同事和部下。“藝術”讓蔣近魯的人生確乎顯得與眾官不同,也讓這個官場人物帶上了幾分儒雅、個性與豪氣。
作者詳述老蔣的“行為藝術”與“藝術行為”,與其說是在書寫一種人生樣態,毋寧說是在書寫一種人生理想或者說理想化的人生。這樣的“儒官”在當下中國并非沒有,但他們的生存方式、處事哲學、官場終局,是否能夠像老蔣這么酣暢淋漓、平心順意,最后在一大摞舉報材料中還能明升暗降地保住官場位置,則是一個不那么容易得到肯定的問題了。
毫無疑問,《蔣近魯的藝術人生》是好讀的,它的敘事節奏明快、簡潔、動態十足、行云流水,因果鏈條前后呼應,這也是邵麗小說在其同代人創作中別樹一幟的原因。她以傳統的“現實主義”手法不斷地觀察、提取、淬煉所見所聞,將其凝結為具有敘事可信度與有效性的藝術存在。
不過,在快意閱讀之余,這種過于“流暢”的敘事也讓我存有一些疑慮。看起來,“果”都是“因”的必然性結局,而且每一個環節都那么“合理化”、“新聞化”,以致于難逃俗套。不得不說,這種不打磕絆的敘事走勢在某種程度上傷害了小說的品格。包括作者在結尾處通過解說老蔣拍的非洲象圖片來試圖回應、凝縮小說意蘊的做法,也未免太過刻意反而使得敘事內涵流于淺白。曾有批評家指出過,邵麗的小說雖然表現出了“新的理解和創造力”,但某些地方顯得“隨意”,“不大講究章法”。在將官場小說從新聞紀實、通俗文學提煉為真正能夠挖掘人性深度的敘事場域這個問題上,邵麗做出了一些推動,但目前可能需要在寫作“慣性”上剎一剎車,對敘事技巧與心理省察等方面予以新的彌補和塑造。
曹霞,著名文學評論家,現居天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