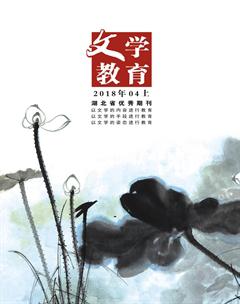鬼子小說創作中的民族記憶與文化身份認同
內容摘要:廣西仫佬族作家鬼子的創作放棄了一貫以來的精英立場而游離于三種文化立場之外,以個人化寫作取得邊緣立場,以“邊緣切入中心”尋求構建自身文化身份,從而達到重返主流的目的。鬼子寫作明顯的價值取向是對現代性弊端的批判與反思,其小說充滿了對“民族記憶”的追尋,對傳統美德的眷戀。而這樣的寫作價值取向是與鬼子擁有少數民族的身份,處于一種全球化、現代化與民族化沖突的兩難處境之中尋求文化認同有關。
關鍵詞:文化身份認同 價值取向 邊緣寫作 民族記憶
廣西仫佬族作家鬼子是“晚生代”作家的代表之一,晚生代作家的小說“不再遵循傳統小說歷史敘述與塑造典型的原則,而是更多地植入了后現代觀念,他們更多關注的是現代社會中生存的個體,把個體作為一個世俗時代的主體來加以確認和張揚。”[1]實現著個人悲劇到社會悲劇的推進。鬼子的寫作定位在最基本的人類情感和人類價值上,定位在人之所以為人的底線上,通過塑造一些命運坎坷的下層人物,揭示了我們的現代社會所存在的問題,甚至揭示了長期困擾全人類的問題:宿命、社會公平、現代社會中的自我迷失……
一.對現代性弊端的批判與身份認同的困惑
鬼子的小說具有非常強烈的批判與反思意識,通過對下層人物的書寫,以《瓦城上空的麥田》中的胡來城、“我”,《被雨淋濕的河》中的曉雷為代表,來引發人們對“弱勢群體”生存問題的探討,對社會公正的反思。一方面,城市無法給這些進城農民以歸宿感,他們無法確認自己的文化身份,無法在城市之中確證自我;另一方面,即使這些進城農民再次回到農村之后,農村也無法給他們以歸宿感和身份的認同,他們從內心上也依然依戀城市的生活,無法接受農村的生活。
在鬼子的小說《瓦城上空的麥田》中,幾乎所有的評論者都注意到了小說中的那個身份證,身份證是推動情節的重要道具,同時也是一個充滿象征意味的隱喻。故事的轉折點是李四丟掉身份證之后,連“父親”這個身份的認同都成了問題,盡管李四想盡各種辦法,還是不能讓兒女們相信自己是他們的父親。冷冰冰的身份證只是人的身份的物化證明,身份證的丟失卻讓李四無論是血緣關系上還是文化意義上的身份頃刻間全部丟失,成為導致一系列悲劇的直接原因,這是讓人匪夷所思而又觸目驚心的。但究其根源還是現代社會之中人與人之間關系的緊張與對立。李四的兒女們原來也是“鄉下人”,但進城之后,富裕之后,城市中的遍布于生活壁壘森嚴的猜忌、疏遠和冷漠使他們異化了。在理性大于情感,物質多于精神的現代化的城市里,李四的兒女們以非常警惕的心態對待每一個陌生人,他們在面對自己的親生父親時都是只認身份證不認人,他們忘了自己的來路,忘了自己的“根”,甚至面對辛辛苦苦將自己拉扯大的父親都無法進行對話和溝通,只認“物證”不認“人證”,憑著自己的理性判斷而不是憑著自己的情感拒絕自己的父親。在鬼子的小說《瓦城上空的麥田》中,充滿了對“身份”的現代性追尋,身份作為一種標示的定義,它不僅是由血緣組成的,還是社會和文化共同作用的結果。鬼子的小說以中國的現代化進程為基本背景,通過描寫城市化進程中的兩種不同身份的人——城里人與鄉下人,兩種文化——以小農經濟為基礎的古典文化與以工業經濟為基礎的現代文化的沖突,塑造了一系列來自農村的小人物在城市化進程中與文化轉型的大環境下的身份認同悲劇。
二.鬼子小說的文化身份追尋與寫作策略
鬼子小說中對“身份”的現代性追尋恰恰反映了晚生代作家對于自己文化身份的焦慮。鬼子作為晚生代的代表之一,是自覺站在下層平民立場上的作家,他的一系列作品所關注的始終是下層百姓的命運。與其他晚生代作家刻意逃避主流,走向邊緣不同的是鬼子寫作的立場定位與價值取向不僅體現了自身的文化身份,還與其人生經歷息息相關。鬼子出生、成長于廣西的一個邊緣貧困少數民族地區,人生的經歷十分坎坷,曾經因生計艱難而輟學,邊緣的下層平民是鬼子揮之不去的身份,苦難的下層小人物體現了作者的寄托于同情,書寫底層人物的苦難,表現他們巨大的生存壓力,是鬼子持續的創作主題。因此,鬼子的文化身份決定了他的小說創作價值取向,而其小說的創作價值取向又體現了他對自身文化身份的認同與追尋過程。
晚生代作家的邊緣敘事、個人寫作是時代文化語境下的選擇,也是他們通過邊緣切入中心,由邊緣回歸主流的一種“歪打正著”的手段。從表面上看,晚生代的作品不再像新寫實那樣為主流分享艱難,描敘正在發生的歷史事實,通過對平凡生活的書寫,通過呼喚人文關懷向主流尋求認同,但他們作品的深層仍然包含了精英的批判性、反思性與主流所呼喚的文化價值與精神。前面所提到的,鬼子小說的一個明顯價值取向是對現代性的批判與反思,正體現了這一點。但如果我們認真深入分析鬼子小說的深層文本結構可以發現,鬼子正是通過對下層小人物的邊緣敘事來完成了以邊緣切入中心,從而回歸主流的任務。中國的現代化進程是一個漫長而痛苦的過程,以鬼子為代表的晚生代作家則是以一種邊緣寫作完成了對這個過程的書寫。當現實社會中,如小說《上午打瞌睡的女孩》中那樣的下崗工人的問題越來越受到重視;如同《瓦城上空的麥田》中的胡來城那樣的城市無業游民的問題正在得到逐步解決;當共和國總理親自為如同《被雨淋濕的河》中的主人公曉雷那樣的農民工討回拖欠的工錢,并承諾切實解決農民工的權利問題時,我們可以聽到鬼子小說中振聾發聵的主流聲音。
三.少數民族作家的民族記憶與民族身份
幾乎所有評論家在評論鬼子時都沒有注意到鬼子的少數民族身份,鬼子文學創作中也似乎有意淡化自己的少數民族身份,作為一個邊緣地區的少數民族作家,鬼子的少數民族身份與民族記憶究竟在其創作中起什么樣的作用,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
民族記憶是一種民族的自我意識,是民族成員之間尋求認同的橋梁,也是構成民族文化身份的重要因素。薩義德曾提到,“每一種文化的發展與維護都需要一種與其相異質并且與其相競爭的另一個自我的存在。自我身份的建構,牽涉到與自己相反的“他者”身份的建構,而且總是牽涉到對與“我們”不同特質的不斷闡釋和再闡釋。每一個時代和社會都重新創造自己的“他者”。因此,自我身份或“他者”身份決非靜止的東西。”[2]這一論斷啟示我們,民族身份的建構與民族記憶的形成是一個在異質文化不的影響下不斷自我豐富和調整的動態發展過程。
鬼子的民族身份是仫佬族,從歷史上看,仫佬族一直都是一個處于漢族區域包圍之中的“孤島式”邊緣少數民族,即使到了今天,仫佬族的人口也沒有超過二十萬,絕大多數集中于廣西的羅城縣,多數人通漢語和壯語,無本民族文字,通用漢文。這就意味著仫佬族是一個長期以來受漢族文化影響很深的民族。對于仫佬族本民族的文化來說,存在一個非常強大的“他者”——漢族文化,因此仫佬族人的民族身份是在與漢族人、漢文化的交流、對話中不斷建構的,本身具有復雜性。鬼子成長于邊緣的少數民族地區,仫佬族本民族的文化與民族記憶根深蒂固地存在于其文化結構之中。同時,鬼子又有過大學教育的經歷,受到過漢族的精英教育,并且成年之后長期居住于城市之中,受現代化的城市文化的熏陶,其民族記憶自然會慢慢模糊與淡忘,這就使其文化身份更趨于復雜。
鬼子作為一個少數民族作家處于一種現代化與民族化沖突并存的兩難處境之中。一方面,民族記憶已經成為一種集體無意識融入鬼子的創作之中,因此他的小說更傾向于關注底層小人物的命運,具備強烈的現實性和人文關懷;另一方面,他又能夠正視自己民族存在的不足,以批判的眼光反思現代化的弊端,體現出對傳統美德的眷戀。“在異域文化與本土文化相碰撞的過程中,民族文化身份的認同成為區分他民族文化的顯著標志。民族文化身份意味著一種民族文化只有通過自己文化身份的重新書寫,能確認自己真正的文化品格和文化精神。這種與它種文化相區別的身份認同,成為一個民族的集體無意識和精神向心力,也是防止本民族文化消亡的措施。”[3]少數民族作家只有確立了自我身份認同,才能夠就能保證創作的明確方向定位。中國處于邊緣位置的少數民族作家應當擺脫自身文化身份認同的困惑,超越對本民族特殊文化的反映與表現,與中國文壇和世界文壇積極進行對話交流與碰撞,積極擴大影響,求得發展。
參考文獻
[1]程文超.鬼子的“鬼”[J]當代作家評論,2004(1):15.
[2]愛德華·薩義德.東方學[M].北京:三聯書店,2000.340.
[3]王岳川.后殖民主義與新歷史主義文論[A].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99.4. 147.
基金項目:廣西高校科研項目:當代廣西海洋文學的審美特質和發展策略研究(KY2015LX521);欽州學院黨建思政課題:新媒體語境下進一步加強高校宣傳思想工作策略研究(2015DJSZ02)
(作者介紹:鄧波,欽州學院黨委宣傳部理論科科長,講師,主要研究方向:文學批評,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