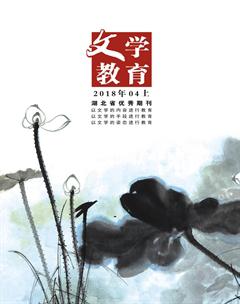井上靖《明妃曲》的承文本性
內容摘要:20世紀日本作家井上靖的小說《明妃曲》是在中國史傳文學、民間傳說及一些文人創作的王昭君故事的基礎上改寫而成的。作品從當代意識出發,顛覆了文學傳統及史實中王昭君的形象,賦予其時代意義,從而塑造出一個追求愛情、追求個人幸福的新女性形象。本文運用敘事學理論,從承文本性探討《明妃曲》的敘事策略及其由此而形成的獨特藝術魅力。
關鍵詞:井上靖 《明妃曲》 承文本性
當代日本作家井上靖的短篇小說《明妃曲》以當代人的眼光解釋了中國歷史上著名的昭君出塞的故事,塑造了一個愛情至上的昭君形象。本文試圖運用敘事學理論,從承文本性對井上靖《明妃曲》的敘事策略進行分析與闡述,進而探討其獨特的藝術魅力。
承文本性(hypertextuality)是熱奈特1982年出版的在《隱跡稿本》一書中重點論述的一個概念。熱奈特首先提出跨文本性這一概念。熱奈特認為跨文本性是“所有使一文本與其它文本產生明顯或潛在關系的因素,”[1]69并指出跨文本性的五種主要類型,即文本間性(intertextuality),其內涵與朱莉婭·克里斯蒂娃的互文性概念類似,指兩個或若干個文本之間的互現關系、副文本性(paratextuality),即正文與標題及序言等副文本的關系、元文本性(metatextuality),指一部文本與它所評論的其它文本之間的關系、承文本性(hypertextuality)、廣義文本性(architextuality或譯為原文本性),文本與其所述的文體之間的關系。熱奈特對文本間性、元文本性和承文本性等類型的區分,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之前朱莉婭·克里斯蒂娃的互文性概念范圍含混不清的問題,使這一理論具有了較強的實用性,使它不再滿足于只是代表解構主義觀念和關注文本意義及邊界的不確定性的指稱,而是成為一個明確的、可識別的實用性文學批評概念。
熱奈特認為承文本性是“表示任何聯結文本B(承文本)與先前的另一文本A(藍本)的非評論性攀附關系,前者在后者的基礎上嫁接而成。B文本作為A文本的派生文本,可以是對A文本的描述或改造,而不必談論它或者引用它。”[1]69后來,熱奈特對承文本作了更深層次的闡釋,他把“任何通過簡單改造或間接改造而從先前某部文本中誕生的派生文本叫做承文本。”[1]77井上靖的《明妃曲》是對中國史書《漢書·匈奴傳》、《西京雜記》及馬致遠《漢宮秋》的重寫與再度創作,是由上述文本派生出來的承文本。
中日兩國一衣帶水,在文化與文學上兩國關系十分密切,有關王昭君的故事在日本廣為流傳。深受中國古代文化影響的井上靖對王昭君的相關故事是十分熟悉的。在發表小說《明妃曲》的同時,井上靖發表了隨筆《王昭君》。在隨筆中,作者詳細介紹了中日兩國關于王昭君題材的創作發展歷程,并對中國典籍如《漢書·匈奴傳》、《西京雜記》及馬致遠《漢宮秋》等作品中王昭君的故事進行概述,指出它們在情節和思想方面的差異。由此可見井上靖雖然是一個日本作家,但是他對對王昭君的故事是十分了解并有一定程度的研究的。也許是因為這個原因,在小說《明妃曲》中,作者采取了學術探討的方式來展開王昭君的故事。
依據作家在改造原文本時所采取的方式的差異,承文本與原文本之間的關系可以分為“間接”改造與“直接”改造兩種不同的類型。“間接”改造是指承文本對原文本在故事結構、語言風格及藝術手法等方面的改造,熱奈特指出喬伊斯的《尤利西斯》與《奧德賽》的關系就是一種“間接”改造的關系。而“直接”改造則是承文本的作者對原文本的情節結構、人物關系以及語言表達等方面加以改造。井上靖的《明妃曲》即“直接”改造這一類型。井上靖從自己所處的時代文化語境對王昭君故事進行了解構與重建。
首先,《明妃曲》對《漢書·匈奴傳》、《西京雜記》及《漢宮秋》等作品進行分析與評價,并在分析的過程中對這些經典作品加以解構,認為作為史實,“有關王昭君的部分只有《漢書》上隔三調四地有那么三、四行記述”,而《西京雜記》和《漢宮秋》是“虛構的東西”、“全都是謊言”,“一點意思也沒有,無聊得很”質疑了這些作品的真實性,進而拋出了一個“真正的王昭君”的文本。這個鬧不清是小說還是隨筆的元朝作品也叫《漢宮秋》,據田津岡龍英所說,是在“大陸的某個皇宮的書庫里發現的”,而發現者和發現的地方目前不能公開,從而增加了作品的神秘感與真實性。[2]163
其次,就情節結構而言,《明妃曲》是在《漢書·匈奴傳》、《西京雜記》及《漢宮秋》等作品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昭君故事的源頭《漢書》關于王昭君的記載極為簡單,只有短短的幾行文字。當時匈奴因分裂而勢弱,呼韓邪單于“自言愿婿漢氏以自親。元帝以后宮良家子王墻字昭君賜單于”,王昭君到匈奴后為呼韓邪生下右日逐王伊屠智牙師,在呼韓邪死后,依匈奴風俗又嫁給呼韓邪的兒子復株累單于。作為一部虛構的文學作品,《西京雜記》在《漢書》王昭君事跡的基礎上增添了畫師毛延壽的情節,使王昭君的命運帶上了一絲悲劇色彩。馬致遠的《漢宮秋》并不拘泥于史實,改動比較大:首先,劇本把故事發生的背景改為匈強漢弱,昭君出塞是在脅迫下進行的,從而突出了王昭君的愛國精神;第二,畫工毛延壽的身份改為中大夫,因向昭君索賄未成而將其畫像獻給匈奴,并唆使匈奴索親,成為被譴責的主要對象;第三,王昭君未入匈奴便投河自殺,表現其對祖國之情深。
上述三部作品的基本情節,井上靖在隨筆《王昭君》均有敘述。作為一個承文本,盡管田津岡龍英一再強調《漢宮秋》等作品的虛構性,但從情節結構、人物關系來看,《明妃曲》是對這三部作品直接改造,其中與《漢宮秋》的關系更為密切。相對于《漢宮秋》所表現的民族情懷與愛國思想,《明妃曲》突出的是王昭君個人價值的實現,對個人幸福的追求。首先,在《明妃曲》中,王昭君雖然也是被選入宮,但她作為一個農家女,是帶著一種對“一般人可望而不可即的榮華富貴在等待著自己”這樣一種夢想來到深宮的,作品一開始就突出了她對個人幸福的追求。而作為一個出身于底層的民間女子,在當時能夠憑借自身的美色而成為皇帝的寵妃,也是她實現自身價值的主要或者說是唯一的途徑。其次,《明妃曲》突出了王昭君的情感生活,表現了她對愛情的追求與向往。被選入宮的王昭君前十年都沒有得到漢元帝的寵幸,是因為她沒有向漢元帝身邊的近臣毛延壽行賄,就這點而言,《明妃曲》與《漢宮秋》是一致的。但是不肯行賄的原因卻不一樣。在《漢宮秋》中,是因為王家“家道貧窮”,而在《明妃曲》中,主要是因為王昭君“她既不愿嘗受象其他女人那樣的悲慘命運,對元帝這個人也毫不動心。”[2]169可見《明妃曲》突出的是王昭君的情感追求。在接下來的情節發展中,進一步表現了這一點:在一次接待匈奴使者時,居于深宮而內心孤獨的王昭君與呼韓邪單于的長子一見鐘情,遇到了一個知心的人,激起了生命的火花。盡管翌年王昭君得到了元帝的寵愛,但“昭君知道,自己是在恨元帝,愛著匈奴的年輕人”。盡管《明妃曲》也有王昭君在黑河投水自盡這一情節,究其原因,并不是因為王昭君的不舍漢家,而是因為她知道了和親的對象并不是她鐘情的那個匈奴王子,而是他那七十歲父親的老單于,所以她的投河實質上是殉情,是因為自己憧憬的幸福生活的破滅。得救醒來后,昭君“看到了睡夢中也忘不掉的那個小伙子”匈奴王子勸慰她:“你就嫁給我父親吧,他已經年老了,快不久于人世了。他老人家一年之內就會死的,他死后,我將會成為單于,我要娶你當后妃。”“要是父親還能活幾年,我就把他殺死。他知道我是愛你的。倘若他總不讓手的話,幾支箭頭就將射穿他的胸膛。為了太陽,月亮和你,我什么事都干得出來。”[2]174這一情節揭示了王昭君故事的主題是愛情,為了愛情,可以不考慮個人的生死,不考慮國家民族的利益、也可以不考慮最基本的倫理道理觀念。對經典作品的改造或者模仿,既與作者的興趣愛好有關,也反映出一定時代文化的精神內涵。井上靖在作品中對昭君故事情節的改造及王昭君形象的塑造,與戰后日本社會個人主義價值觀的盛行是分不開的。
井上靖雖然將《明妃曲》的背景置于戰前日本某大學附近的小酒店,但是它與井上靖的其它作品一樣,在文本深處表達出了作者對歷史的執著與熱情。作為昭君系列故事的一個承文本,作者以其獨具特色的敘事技巧,在對昭君故事的顛覆與改寫中,使昭君這一人物烙上了時代的印記,成為一個追求個人愛情與幸福,富于現代意識的女性形象,從而賦予了作品新的時代意義。
參考文獻
[1]熱拉爾·熱奈特.熱奈特論文集[M].史忠義,譯.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0.
[2]井上靖.永泰公主的項鏈[M].賴育芳,譯.北京:作家出版社,1988.
基金項目:湖南省教育廳科研基金優秀青年項目(13B106):井上靖中間小說研究。
(作者介紹:袁盛財,邵陽學院中文系副教授,主要從事比較文學、日本文學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