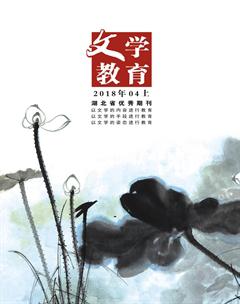《天黑前的夏天》小說結局合理性探討
黃靜
內容摘要:本文從多麗絲·萊辛中期小說《天黑前的夏天》結局的矛盾性出發,擬從文學倫理學視角探討“房子”及“海豹”等意象的倫理意義,最后指出女主人翁回歸家庭有其必然性,體現了文學的“倫理教誨作用”。
關鍵詞:《天黑前的夏天》 文學倫理學 小說結局
《天黑前的夏天》是英國著名作家多麗絲·萊辛(1919-2013)的中期作品。小說講述一位中年女子在某個夏日來臨之際,面臨身份危機,突然打破常規,走出規范生活的情感變化和心理體驗。該小說的結局“女主人翁凱特最終回歸家庭”被女性主義者視為一大敗筆。她們認為凱特最終屈服于黑暗,“接受了命運對她的安排,將繼續自己‘天黑般的生活。”[1](99)而Gayle Greene在《多麗絲·萊辛:變化的詩學》中將《天黑前的夏天》看成“一個封閉的環形,”[2](123)并指出了小說結局的矛盾性。而另一方面,Jean Pickering則認為凱特的旅程為“線性旅程”,她將“回家”與“海豹”意象聯系在一起,并賦予它們積極的涵義,她認為凱特的回歸意味著希望與重生,主人翁將海豹放歸她內心深處的大海是她心之所向。[3](135)筆者發現從文學倫理學視角看該小說的結局有其必然性。文學倫理學批評要求文學批評必須要回到歷史的現場,即在特定的倫理環境中批評文學。“倫理環境”、“倫理身份”、“倫理困境”、“倫理選擇”等都是文學倫理學批評的核心術語。“文學倫理學批評注重對人物倫理身份的分析。在閱讀文學作品的過程中我們會發現幾乎所有倫理問題的產生往往都同倫理身份相關。”[4](14)本文擬從該視角討論主人翁凱特的個人倫理選擇,回家的倫理意義并指出小說結局的合理性。
一.“房子”的倫理意義:身份回歸的象征
“房子”或“房間”的意象在萊辛小說中起著極其重要的作用。萊辛借用了弗吉尼亞·伍爾夫《一間自己的房間》中房子的意象,同時賦予它兩種特殊的意義:第一,她將房子內化到心理層面,讓房子由外部機構變成能突破內部心理障礙的象征;第二,她將房子延伸至整個社會。[5](177)
從文學倫理學角度來看,在這部小說中,“房子”是一種倫理象征:凱特為人妻為人母的身份。對她來說,“房子”是其安身立命的場所。當她還是無憂無慮小女孩時,“爺爺的石屋建在花園中央,花園里到處都是百合花和鳳凰樹。”[6](20)1984年的夏天,她遇見了邁克爾,搬進了邁克爾的“住所”。當她和邁克爾有了第三個孩子之后“沒過多久,他們按揭買了一棟房子,添了一輛小汽車,請了個鐘點工女傭,過起了規律的生活。他們這么做全是為了孩子。”[6](86)此時的凱特已不再是先前無憂無慮的小女孩,她有了為人妻母的身份,必須要為這一身份擔負起該有的責任,所以房子此刻的倫理意義象征著之后“四分之一”個世紀里與邁克爾共同生活撫養孩子的相濡以沫。在小說開始,凱特房子里由她精心照料了二十多的旖旎美麗的英式花園,需要“趁這個夏天,好好修整一番,”[6](19)“房子”的事情成了小事,“房子被出租”就這樣“被決定”了,凱特也生平第一次成了可有可無的人。
王麗麗在《多麗絲·萊辛的藝術和哲學思想研究》中指出“多麗絲·萊辛在其小說中用房子意象來象征主人翁試圖實現的某種自我并且房子與房間的關系暗示了主人翁與其他人之間的關系。”[5](188)凱特在國際食品組織部門的公用房間“十分寬敞,里面擺了不少桌子,有很多空間可以用……如今她已經習慣了這里,坐在里面忍不住矜矜自得地暗想自己在這一新階層的種種優越之處。”[6](37-38)在這里,她獲得了職業身份,短期的社會身份并且贏得了人們的尊重。而凱特與杰弗里在西班牙時住的房間,“帶了個陽臺,正對著一個公用小花園”[6](78)像極了自己家的房子,她總是待在陽臺回憶與家人之間的種種矛盾。這個房間和杰弗里的存在一定程度上幫助凱特理清母子矛盾并走出丈夫婚外性行為的心理陰影。當凱特生病之后,她所住倫敦酒店的房間,“像一個工具箱,那張單人床跟她和丈夫早年同床共寢的床鋪一樣大……上面懶洋洋地擺放了兩個玫瑰色靠枕,顯得像家一樣舒適。”[6](130)這間房喻指了凱特與丈夫早年辛苦工作養家糊口的日子及她與丈夫那種彼此知根知底,親密無間的時光。也正是在這間房里,她開始渴望見到自己的丈夫。當她終于鼓起勇氣來到自家花園大樹下時,發現房子變了,“一張沙發翻倒在草坪上,顯得十分落寞”[6](140)她對之前熟悉的房子竟一點兒感覺都沒有。房子發生了變化,則意味著她已經不再保留之前失去自我為人妻母的身份。最后,她在莫琳的地下公寓了獲得一間很小的屋子,“放了一張窄窄的小床和一個柜子。里面的溫度比前面朝南的公寓低好幾度。房間冷颼颼的。”[6](159)在這“還湊合”的房間里,凱特在幫助莫琳選擇婚姻伴侶的同時自己也選擇了接受完全真實的自己,她揭下一直為迎合丈夫身份而偽裝的面紗,不再染發,穿合身的衣服,毅然決定回家。“房子”對于凱特來說不僅是物質的,也是精神的,更重要的是它有著重要的倫理意義:通過回家,回到自己的房子來找回屬于自己的倫理身份。
二.“海豹”的倫理意義:追求真愛,找回“身份”的過程的象征
萊辛小說中另一重要的元素是她對主人翁夢境的精彩刻畫。萊辛的夢可以總結過去也可以預示未來。所以分析該小說中“海豹”之夢與凱特經歷之間的關系是把握小說脈絡的關鍵。貫穿凱特整個旅程的“海豹”之夢在小說中出現了15次。凱特送“海豹”回歸大海的系列夢境有著重要的倫理意義;它象征著凱特苦尋真愛、找回身份的過程。
“海豹”之夢第一次出現在“國際食品組織”,“原來是只海豹,擱淺了,正無助地躺在陰涼山坡邊一塊干燥的大石頭上,痛苦地呻吟著。”[6](29)此時的凱特,剛剛離開家,“生平第一次不被家人需要”得不到來自丈夫和孩子的尊重,已經失去了為人妻母的倫理身份。當她與杰弗里在西班牙時,夢中的海豹“在慢慢地、痛苦地朝遙不可見的大海爬去。”[6](94)凱特在這個夢里見到了她的情人,與情人做愛了,而海豹就在旁邊。她告訴自己必須先把海豹送回海里,于是與情人告別。這個“海豹”之夢暗示了現實生活中的凱特渴望完美無瑕的愛情,她發現自己在與杰弗里這段“女大男小”的荒唐的關系中,一直如“母親”般的“照顧”著的“兒子般”的角色,所以她義無反顧的離開了。當她來到倫敦的酒店,病得奄奄一息,終于懂得與自己的過去握手言和,開始懷念與丈夫長達四分之一個世紀的“相互廝守,不離不棄”。那夢中的“海豹”也在她的照料下“睜開了眼睛,輕聲地呻吟著。”[6](138)在夢里她抱起“海豹”繼續北行。而當凱特最后在莫琳的公寓里,給女兒般大的莫琳講述自己生活故事的同時,鼓勵莫琳勇敢地走進婚姻的殿堂。她成功的說服了莫琳也成功的說服了自己,最終坦然接受了不再偽裝、聽從于內心、為自己而活為人妻為人母的身份。此時的“海豹”已經被凱特平安送回大海。“海豹沉入水底,接著浮出水面,腦袋最后一次靠在礁石旁:用柔和的黑眼睛看了看她,然后閉上鼻孔潛入水中……她發現太陽掛在自己的正前方……”[6](232)原來她們夫妻之間母子之間的愛一直都在,只是換了一種形式。當她忽略了自己委曲求全去迎合他人,生活的重擔讓她忘記了生活中一些最本真的東西。而當她決定以全新的形象回歸家庭時,也就找回了自己該有的身份。所以海豹之夢的倫理意義,即凱特找回真愛找回身份的過程。在夢的最后“她望著它,望著這輪明亮碩大,歡快活潑,仿佛要引吭高歌的太陽。”[6](232)預示著凱特回家之后的生活必定是充滿希望的、和諧的和幸福的。
三.回家的倫理意義:接受倫理身份;履行倫理義務
凱特放棄了以前讓她感到約束的發型,穿上了合身得體的衣服,以全新的形象回家,是她深思熟慮之后做出的選擇。回家,體現了其重拾自我,走出倫理困境,坦然接受自己已不再年輕、孩子們已長大成人應該放手,這一為人妻為人母的倫理身份,并勇于履行其義務的重要意義。另一方面,凱特對丈夫和孩子深深的愛和依戀,說明她的心其實一刻也沒有離開過家,只是特殊的倫理環境造就了當時失去自我、失去身份的她,被暫時蒙蔽了雙眼,一時之間沒有找到正確的方式與家人及時溝通,看不到幸福的方向。所以最終重回“幸福的港灣”,“愛的懷抱”也是她的必然選擇。
凱特因身份危機和家庭倫理疏離產生的倫理困境是傳統中年婦女共同的問題。而她在走出倫理困境后所做出的倫理選擇并非永遠的離開而是勇敢的回歸家庭,體現了萊辛的人文關懷:宣揚其對家庭成員的理解、仁愛、寬恕及接受家庭倫理身份的同時又不失去自由意志的個人品德。聶珍釗教授指出:“文學產生于倫理表達的需要。”[4](5)凱特的回歸正好體現了文學的功能:文學的倫理教誨作用。因此該小說也仿佛提醒每一個人要對自己身份負責任;適當地自我調整,也是追求幸福和明確人生價值的一大途徑。
參考文獻
[1]張志榮.談意象在《天黑前的夏天》中的運用[J].短篇小說(原創版),2012(23)99-100.
[2]Gayle, Green. Doris Lessing: The Poetics of Change[M].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4.
[3]Pickering, Jean. Understanding Doris Lessing[M]. Columbia, S.C.: The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1990.
[4]聶珍釗.文學倫理學批評及其它——聶珍釗自選集[C].武漢: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12年.
[5]Wang, lili. A Study of Doris Lessings Art and Philosophy[M].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2007
[6]Lessing Doris. 天黑前的夏天[M].邱益鴻,譯.1版.海口:南海出版公司,
(作者單位:安徽淮南師范學院外國語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