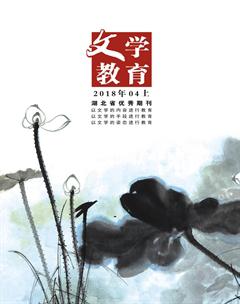陸機《文賦》的文體觀念及其在文體學上的意義
內容摘要:《文賦》在從兩晉到南朝的文體觀念及其相應的文體學著作發展的過程中具有重要意義,《文賦》的文體價值觀上承曹丕《典論·論文》,下接《文心雕龍》,在中國古代文體價值觀念發展的過程中處于重要的過渡位置,其所體現的文體觀比《典論·論文》有了很大的深入與創新。
關鍵詞:文體觀念 陸機 《文賦》
漢末曹魏曹丕的《典論·論文》已經初呈乍現了中國古代體用一如的文體觀結構,指出了“氣”在形成個體文體中的重要作用,但是,《典論·論文》對中國古代文體觀的討論畢竟只是一個初步展現,尚不夠細致;甚至,是比較粗糙的。這需要文人士子對文體的日益重視與追逐中不斷增強文體意識,對如何能夠形成別具一格的文體也必然會呈現出逐步深入的研究,這是士子們極為關心和重要的問題。西晉時期,著名文豪陸機對如何形成文體頗有心得,作有《文賦》,稍后的南朝藏榮緒在《晉書》中亦云:“機妙解情理,心識文體,故作《文賦》。”[1]《文賦》又是一篇展現中國古代文體觀的杰作,相比《典論·論文》而言,《文賦》在結構上趨向于完整與嚴密,在具體論述中趨向于細致與深入。
一.《文賦》的文體形成過程觀
如何能形成比較滿意的文體,是陸機所思考的問題。他將如何形成文體視為一個整體過程,本論文將其分為文體形成前的精神準備活動、文體形成的具體過程兩部分述之。
第一,形成文體前的精神準備活動。
《文賦》不是從一開始就直接談文體的,而是將文體形成之前的種種精神準備活動或注意事項按照步驟、次序地論述,這使陸機的文體觀在邏輯上是比較完整的。
從“佇中區以玄覽”到“伊茲事之可樂”[2]是這一部分的主要內容。這一部分可分為四個層次逐層深入。第一層次表達兩個意思,首先要在自然之中獲得情感:“遵四時以嘆逝,瞻萬物而思紛。悲落葉于勁秋,嘉柔條于芳春”,然后將昔日所學之文章、辭藻等涌上心頭:“詠世德之駿烈,誦先人之清芬。游文章之林府,喜麗藻之彬彬。”第二層次進入沉思與想象階段:“其始也,皆收視反聽,耽思傍訊,精騖八極,心游萬仞”,思維處于極度活躍狀態,從而能夠得到具有創造性的想法,獲得所要創造的藝術形象。第三層次進入具體的思路與文章結構的問題,陸機提供了多種方法:“或因枝以振葉,或沿波而討源。或本隱以之顯,或求易而得難。……”,或者由次要的引出主要的,或者由現象追蹤討源;或者由隱到顯,或者由易得難;等等。總而言之,文章要做到有條理:“理扶質以立干,文垂條而結繁”,即使內容再繁多也是井然有序的。第四層次強調在寫作中要一直保持平靜、寂寞之心態:“課虛無以責有,叩寂寞而求音”,從而達到從無到有的突變與飛躍。
第二,形成文體的具體過程。
從“體有萬殊”到“吾未識夫開塞之所由”[3]是這一部分的主要內容。這一部分可分為三個層次。
第一層次是要明確文類文體的基本規定性。進入狀態并獲得一定的思路后,該考慮把它寫成一篇什么樣的文章,即形成什么樣的文體的問題。世間的文體千變萬化:“體有萬殊,物無一量,紛紜揮霍,形難為狀”,該如何選擇?但是,不管最終要形成什么樣的文體,都要先選擇合適的文類文體作為載體,這時,就要對該種文類文體的內在規定性具有明確而又清晰的把握,其云:“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碑披文以相質,誄纏綿而凄愴。銘博約而溫潤,箴頓挫而清壯。頌優游以彬蔚,論精微而朗暢。奏平徹以閑雅,說煒曄而譎誑。”陸機在這里談了當時常用的十種文類,對每種文類之文體都進行了具有兩個修飾詞的對應式的歸納,這比曹丕的《典論·論文》中“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的簡單論述顯得細致得多。《文賦》與《典論·論文》最明顯的區別就是詩賦的位置由末位而一躍上升為首位,《典論·論文》仍然處在東漢末年文章要以政用為核心的理念的引導下,經過漢末曹魏人才觀念的發展,人們以性情作為判定一個人是否有才能的標志,而詩賦又是能夠體現才性的最佳載體,這種觀念在西晉時大概已經比較普遍,詩賦成為士人們狂熱追求的事物,其位置躍于所有文類之首也是理所當然之事。同時,陸機明確用“詩緣情”來表達詩體的內在特征,“詩”已經明確擺脫先秦以來的“詩言志”的社會功能意義而朝向一種講究技巧的創作樣式的方向發展。曹丕的“詩賦欲麗”已經含有這種意思,但還沒有《文賦》的表述明確。一般認為“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這兩句話是互文見義的,但本文認為這正是部分文人對“賦”的特長的明確認識及其對詩賦分工的心理傾向表現。一方面,賦是可以表情的,這沒有異議,這從屈原開始就用賦抒情;另一方面,詩也可以體物,但詩體物的效果沒有賦好。二者之間沒有截然割裂的界限,但是體物,文人們還是傾向于賦體的。銘體與誄體曹丕只用一個“實”字來制約即強調內容的真實準確,這與曹操崇尚故實有很大關系,“實”字之論從內容上來講不可謂不精,但作為文類的文體風貌描述則難可人意,陸機“誄纏綿而凄愴,銘博約而溫潤”則具體指出誄的文體要顯得動情而又悲哀,銘的文體要博深、簡潔而又溫文爾雅。對于書論,曹丕只用一個“理”字,即重于說理,《文賦》明確用“精微而朗暢”來表達論體風貌,即論理要精微細致而又豁朗順暢。曹丕用“雅”字來規定奏議,《文賦》指出不僅要“閑雅”,還要“平徹”,態度要平和,反映問題要透徹。其他曹丕沒說到的有碑、箴、頌、說四體,“碑”要文質相稱,“箴”要抑揚頓挫而又清壯,“頌”要從容不迫地盡顯繁盛之態,“說”要光亮而又具有煽動力。
在明確文類文體的基本規定性的基礎上,第二層次從“變”的角度闡述形成文體的心得。由于世間事物的千姿百態,由此而形成的文體也必然是千變萬化:“其為物也多姿,其為體也屢遷。”在變化莫測中,陸機強調了在形成文體中的三個重要因素:一是構思要巧妙,“會意也尚巧”;二是辭藻要華美,“遣言也貴妍”;三是在音律上要和諧,“暨音聲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接下來的“或仰逼于先條,或俯侵于后章”、“或文繁理富,而意不指適”、“或藻思綺合,清麗芊眠”、依次論述了在形成文體過程中文章的結構要合理、最好形成警策之語、不因襲前人而具有獨創性等基本要求。從反面,《文賦》提出了五種應該避免的情況,并提出要以“應”、“和”、“悲”、“雅”、“艷”來救治這五種文病。張少康先生指出,這五者其實反映了陸機在創作上的美學思想[4]。在形成文體的過程中,要注意的事情很多,要根據實際情況靈活處理:“若夫豐約之裁,俯仰之形,因宜適變,曲有微情”,可以說是對以上內容的補充和總結。
以上便是陸機在長期追求文體的過程中的心得,他對形成文體之前的精神準備活動、作為基礎性的文類文體及在形成文體過形成中應該做到和避免的種種事項都具有整體而又細致的把握:“普辭條與文律,良余膺之所服”,即使是這樣,他也感慨難以駕馭變化莫測的文體,“嗟不盈于予掬”。在第三層次中,他指出靈感在形成文體中的重要作用,靈感來的時候,下筆如有神助:“夫應感之會,通塞之紀,來不可遏,去不可止”;靈感枯竭的時候,文體就會偏枯:“理翳翳而愈伏,思軋軋其若抽。”[5]
二.《文賦》的文體價值觀
《文賦》的通篇都是圍繞如何形成文體而展開的,其最后一部分一般認為是講文章的社會功用的問題,本論文認為從全篇結構而言最后一段正是給出如此重視文體的原因:正是因為文章有如此巨大的社會功用,既能引導國家大事,又要承擔教化責任,“濟文武于將墜,宣風聲于不泯”[6],如此重要的東西當然要永世流傳,而具有美好的文體則是使其能流傳的重要手段,頗有孔子“言之無文,行而不遠”[7]之意。對文章的社會功用,陸機與曹丕“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的說法是一脈相承的,都是將文章提到國家大業的高度上;而陸機的說法則比曹丕又有所深入,文章究竟有哪些社會功用,曹丕沒有細說,曹丕是以帝王之豪氣而闡發文章的價值,他渴求的是通過文章以“立言”,未免功利色彩稍強了些。而陸機則不然,他對文章的社會功用論述已經呈現了邏輯性的深思,基本上可以分為兩個層次:第一層次:“恢萬里而無閡,通億載而為津。俯貽則于來葉,仰觀象乎古人”,徐復觀先生解釋前兩句說:“上句以空間言,下句以時間言;《說文》十一上:‘津,水渡也。由此岸到彼岸為水渡。言人之精神可以通于億載,而文為之津渡。”[8]徐氏解說甚當,由此句則文章乃是人可以穿越時空、翱翔宇宙、載通古今的津渡;第二層次:“濟文武于將墜,宣風聲于不泯。涂無遠而不彌,理無微而弗綸。配霑潤于云雨,象變化乎鬼神。被金石而德廣,流管弦而日新。”這一層次主述文章的教化作用,雖然內容基本上都在儒家思想之內,但卻展示的很具體。其重要意義在于,第一層次中人通過津渡,是為了能夠達到第二層次的“道”,也就是說,兩個層次之間形成了“人——文——求道”的關系,這已經和《文心雕龍·原道》中“圣沿文而垂道”的思想完全吻合。總之,陸機《文賦》的文體價值觀上承曹丕《典論·論文》,下接《文心雕龍》,在中國古代文體價值觀念發展的過程中處于重要的過渡位置。
三.《文賦》的文體觀在南朝文體觀發展中的重要作用
《文賦》的出現,在從兩晉到南朝的文體觀念及其相應的文體學著作發展的過程中具有重要意義:首先,文類文體是形成個體文體過程中的基礎性步驟,文類文體是載體,個體文體才是文人在現實中所努力追求的目標,《文賦》顯然繼承了從曹丕以來的體用一如的文體觀結構;其次,《文賦》是對文體形成這一過程的全面性論述,特別是用大量篇幅描述下筆前的精神準備活動,這是《典論·論文》不具備的,在結構上顯得更為完整和嚴密。再次,《文賦》是在《典論·論文》之后的相當長的一段歷史時期內對文體形成過程描述最為詳細的篇章:《文賦》對文體形成之前的精神準備活動進行了前所未有的細致描述;對文類文體的論述在數量上比《典論·論文》多,對各類文體內在規定性的描述上也比《典論·論文》更為具體;對個體文體形成的具體過程要做到的法則與應該避免的文病詳細列出,比曹丕只用“氣”來闡釋個體文體的形成更具有可操作的實踐性意義。《文賦》在當時非常具有影響力,被認為是最為詳盡的形成文體的學習寶典,《文心雕龍》云:“昔陸氏《文賦》,號為曲盡。”[9]第四,《文賦》對文類文體的闡述僅有十種,事實上,在漢末魏晉以來,文類的數量是非常繁多的,而且社會生產生活的發展又不斷的滋生新的文類,對文類文體的更為廣泛、甚至是全面性的總結成為必然走向;同時,士人們在爭相追逐個體文體的過程中,具體遇到的問題是變化無窮的,遠非《文賦》中所列條目所能籠盡,這促使更為細致的描述文體形成的著作的出現;另外,中國文章以及文體的來龍去脈具有十分深遠的歷史土壤,在論述上顯然還有極大的發展空間,隨著文人們思辨之學的發展與研究的深入,對文體的研究也有可能出現更為精深的思想及論著。《文賦》所體現的文體觀比《典論·論文》無疑有了很大的深入與創新,隨著文人們用文體展現才情越來越洶涌的狂潮,必將迎來文體觀念發展的大盛時代。
注 釋
[1]蕭統編、李善注:《文選》,中華書局,1983年,卷十七,第239頁,李善注引臧榮緒《晉書》.
[2]《全晉文》,卷九十七,第1024頁.
[3]《全晉文》,卷九十七,第1024—1025頁.
[4]張少康:《文賦集釋》,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年,第208頁.
[5]《全晉文》,卷九十七,第1025頁.
[6]《全晉文》,卷九十七,第1026頁.
[7]楊伯峻注:《左傳·襄公二十五年》,中華書局,2008年,第1106頁.
[8]徐復觀:《中國文學精神》,上海書店,2006年,第300頁.
[9]《文心雕龍·總術》,卷九,第655頁.
(作者介紹:呂紅光,浙江樹人大學人文與外國語學院副教授,文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