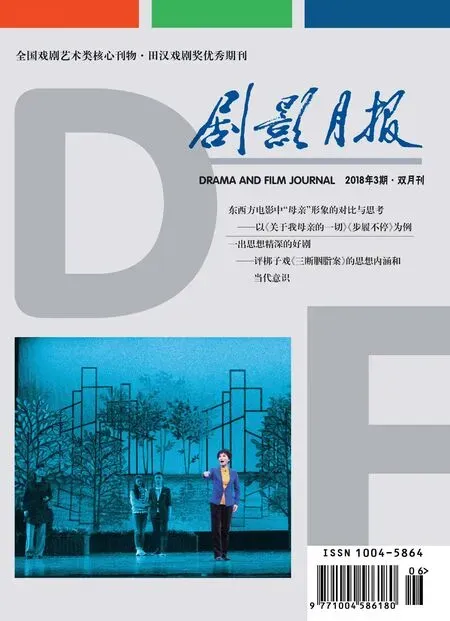原創(chuàng)京劇劇本的審美與技法
——以《四郎·嘆》為例
■戴謹(jǐn)憶
滿清王朝取得全國統(tǒng)治后,隨著時(shí)間推移社會(huì)趨于穩(wěn)定,滿漢民族矛盾由是從強(qiáng)烈變得舒緩,當(dāng)時(shí)的社會(huì)充盈著“民族矛盾和解、文化融合大團(tuán)圓”的氛圍。基于此,滿清統(tǒng)治者加大以“忠孝節(jié)義”為核心的道德倫理價(jià)值觀的宣揚(yáng),在戲曲文化領(lǐng)域誕生出一批以孝親團(tuán)圓、兒女情長為主題的京劇劇目,傳統(tǒng)京劇《四郎探母》正是契合了這種文化意識(shí)形態(tài)中“和”,誕生并流傳至今;而中央戲劇學(xué)院的原創(chuàng)京劇《四郎·嘆》,采擷楊家將題材,站在現(xiàn)代人的視角大膽構(gòu)思,進(jìn)一步發(fā)掘和完善傳統(tǒng)京劇《四郎探母》“忠孝不能兩全”的人文情懷,大獲成功,獲得中國話劇藝術(shù)研究會(huì)主辦的第六屆戲劇奧林匹克助演劇目最高榮譽(yù)。
若論原創(chuàng)京劇的成績,首先談及原創(chuàng)劇本。原創(chuàng)京劇劇本創(chuàng)作,要求編劇首先站在當(dāng)代人的視角對(duì)傳統(tǒng)京劇元素進(jìn)行整合并創(chuàng)新,其次便是去探尋中國傳統(tǒng)戲劇文化在不同歷史時(shí)期如何闡釋與演繹其不同的本體與精神。作為中央戲劇學(xué)院首部原創(chuàng)京劇的劇本,其創(chuàng)作宗旨必須堅(jiān)守學(xué)院派嚴(yán)謹(jǐn)厚重風(fēng)格,堅(jiān)持實(shí)踐服務(wù)于教學(xué)的本質(zhì),從“忠孝兩難的文化心態(tài)”及學(xué)生傳承載經(jīng)典文化的角度出發(fā),構(gòu)建個(gè)體意識(shí)對(duì)抗集體理性的同時(shí)審視和反思傳統(tǒng),并在規(guī)定請境內(nèi)強(qiáng)烈表達(dá)戰(zhàn)爭面前的家國人倫情懷。
編劇通過梳理傳統(tǒng)京劇《四郎探母》與原創(chuàng)京劇《四郎·嘆》中“共通的忠孝節(jié)義、不同的文化精神”——《四郎探母》是封建文化“偽大團(tuán)圓”的情境下,以楊四郎“生”為結(jié)局,掩藏忠孝難以調(diào)和的尷尬本質(zhì);《四郎·嘆》則是在現(xiàn)在“楊四郎自刎”的文化氣息中,重構(gòu)“個(gè)體意識(shí)對(duì)抗集體理性”“審視忠孝節(jié)義反思傳統(tǒng)”的兩個(gè)層面,在“人”的視域內(nèi)探討“忠孝不能兩全”的生活真實(shí)。可以說,《四郎·嘆》的創(chuàng)作,在一定意義上是運(yùn)用傳統(tǒng)京劇元素向“傳統(tǒng)戲劇”致以的極高敬意。
一、把握好楊四郎“忠孝兩難”文化心態(tài),發(fā)掘主人公楊四郎個(gè)體生命忠孝特質(zhì)和生存本能,展現(xiàn)楊四郎“忠孝”無法抉擇狀態(tài),同時(shí)將劇中人物的一種心理“兩極無間”的痛苦傳遞給觀眾,使觀眾的心靈體味和承受更深層次的歷史孤獨(dú)。
傳統(tǒng)京劇《四郎探母》的故事發(fā)生在宋遼對(duì)立時(shí)期,規(guī)定情境是宋、遼兩軍擺開決戰(zhàn)的架勢,大戰(zhàn)一觸即發(fā)。但是,《四郎探母》卻沒有對(duì)這場持久浩瀚的戰(zhàn)爭進(jìn)行正面描述,而是通過“兩國不和常交戰(zhàn),各為其主奪江山,兩國不和何時(shí)解”的話語一帶而過,制動(dòng)而取靜,將整出戲重點(diǎn)段落設(shè)定在一種相對(duì)和平的“戰(zhàn)爭間歇”中予以敘述,這也使得該劇從開場便具備向“內(nèi)”發(fā)掘的情景基礎(chǔ)和文藝氣質(zhì)。但是楊四郎唱段中“楊四郎被擒改名姓方脫此難,將楊字拆木易匹配良緣”所凸顯的生存矛盾與“蕭天佐擺天門在兩下會(huì)戰(zhàn),我的娘領(lǐng)人馬來到北番,我有心回宋營見母一面,怎奈我身在番遠(yuǎn)隔天邊,思老母不由我肝腸痛斷,想老娘淚珠兒灑在胸前,眼睜睜高堂母難得見,兒的老娘啊!要相逢除非是夢里團(tuán)圓”的文字卻難以全面展示向“內(nèi)”發(fā)掘的全部敘事——用楊四郎“孝不能盡”的苦楚來定位“探母”,無疑限制了楊四郎對(duì)更高層次“忠”的主題開展。因?yàn)槿绾螌钏睦伞岸嚯y多思無法抉擇”的生命狀態(tài)進(jìn)行呈現(xiàn),才是整出戲核心,而傳統(tǒng)京劇《四郎探母》在開展主題的過程中,過度突出“孝”文化,而對(duì)“忠”的表述明顯力度不夠,甚至有所忽略,以至于長期以來觀眾和評(píng)論者沉醉于全戲【西皮】腔調(diào)的優(yōu)美旋律中而忽略了“四郎文化”的文化本體認(rèn)知和研究。如何在已經(jīng)既定文化的基礎(chǔ)上,在不失唱腔旋律優(yōu)美之余創(chuàng)造出符合當(dāng)下文化意識(shí)形態(tài)且能夠讓觀眾激蕩胸懷的“四郎形象”,引起觀眾審美上的共鳴,這就要看編劇如何把握和拿捏楊四郎的“忠孝兩難”的文化心態(tài)。
原創(chuàng)京劇《四郎·嘆》編劇構(gòu)思的第一步,正是從這個(gè)“兩難文化心態(tài)”入手。首先,《四郎·嘆》的劇本,進(jìn)一步淡化了傳統(tǒng)京劇《四郎探母》中仍潛藏的“遼宋不兩立”民族主義情緒,對(duì)兩個(gè)軍事集團(tuán)“是與非”立場不做“對(duì)與錯(cuò)”的評(píng)論,而是重點(diǎn)將觀眾帶入一種客觀的戰(zhàn)爭廝殺情境中,引發(fā)觀眾對(duì)戰(zhàn)爭根源的思考。其次,《四郎·嘆》重點(diǎn)刻畫主人公楊四郎作為一個(gè)“個(gè)體”對(duì)“忠孝”的特質(zhì)進(jìn)行理解,將人物放入最為原始生存的本能狀態(tài)中,將楊四郎面對(duì)戰(zhàn)爭、面對(duì)兩個(gè)對(duì)立軍事集團(tuán)中親人的糾結(jié)無奈選擇表現(xiàn)出來,通過京劇念白和唱腔傾訴把楊四郎、佘太君、蕭太后真實(shí)鮮活的表現(xiàn)出來,從而展示出劇本的內(nèi)在的精神,引發(fā)觀眾對(duì)“家國”觀念和價(jià)值取舍進(jìn)行重新思考。第三,《四郎·嘆》矛盾層層遞進(jìn),三場戲劇矛盾沖突此起彼伏——【第一場】“戰(zhàn)鼓狼煙催人淚四郎身世疑竇生”【第二場】“家國人倫難抉擇巧試金湯萬念灰”【第三場】“血綻沙場命歸陰可嘆亡魂聚邊關(guān)”,一步步揭示出楊四郎“忠孝兩難的抉擇”,將楊四郎的那種心理上終極無間的狀態(tài)和淋漓展示出來,引起觀眾心靈上的思考。劇本搬上舞臺(tái)的過程,是編劇、導(dǎo)演、唱腔作曲、舞臺(tái)美術(shù)等多個(gè)主創(chuàng)部門在具體操作層面上的共識(shí)——將劇本中的那種人性的解構(gòu)通過導(dǎo)演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相結(jié)合的戲劇手法進(jìn)行處理,通過迭出不窮的矛盾沖突、形式鮮明的歌舞、一唱三嘆的唱詞和簡約大氣的舞臺(tái)美術(shù)對(duì)劇本的“孝親”觀念一一詮釋,強(qiáng)烈地表達(dá)出戰(zhàn)爭面前的家國人倫常情,達(dá)到構(gòu)建個(gè)體意識(shí)解構(gòu)集體理性、審視忠孝節(jié)義反思傳統(tǒng)文化、運(yùn)用傳統(tǒng)文化形式向真正的傳統(tǒng)致敬的三重目的。
原創(chuàng)京劇《四郎·嘆》在人物設(shè)置上充滿特點(diǎn),其中之一便是把傳統(tǒng)京劇《四郎探母》中蕭太后本應(yīng)擁有的戲劇魅力給“請了回來”,從而展現(xiàn)出一代明主蕭太后的英偉、睿智和謀略,并結(jié)合她在劇中“國母”、“岳母”雙重身份,突出“君王人性復(fù)雜”——為國家利益,不得不在戰(zhàn)爭前擊退流言,派楊四郎出征;而站在家庭的角度,又不愿讓這個(gè)乘龍快婿身世的流言得到證驗(yàn)。劇情設(shè)置【第三場】“血綻沙場命歸陰可嘆亡魂聚邊關(guān)”,楊四郎身世得到驗(yàn)證,蕭太后為了“鐵鏡公主”和“小孫兒”,仍然留楊四郎性命,展現(xiàn)出彌足珍貴的“人”性。為此,《四郎·嘆》用分別用【第二場】“家國人倫難抉擇巧試金湯萬念灰”的四段“哀嘆”和【第三場】“血綻沙場命歸陰可嘆亡魂聚邊關(guān)”的“哀嘆”,通過“起承轉(zhuǎn)合”展示出蕭太后內(nèi)心的斗爭。
【第二場】“家國人倫難抉擇巧試金湯萬念灰”
[起]蕭太后(白)近日里楊家將屯兵駐防,佘太君護(hù)糧草增援?dāng)U張。我已令蕭天左天門陣上,誓把那楊家將一并滅亡。眾軍士請戰(zhàn)功摩拳擦掌,成一統(tǒng)顧不得暗自神傷。
[承][轉(zhuǎn)]蕭太后(唱)實(shí)可嘆流言起攪我心腸,有細(xì)作在營中要把禍釀。今日里金鑾殿命婿為將,恐木易是楊家將有朝一日,反戈一擊怎奈我不及堤防,巧安排駙馬爺試探金湯。若不是那楊家將,流言自飛心歡暢。如若是楊家賊,我性命定會(huì)有傷。(白)不!(唱)驗(yàn)真?zhèn)卧跄軌虬底葬葆澹d邦,大局為重,顧不得親情殘傷。
【第三場】“血綻沙場命歸陰可嘆亡魂聚邊關(guān)”
[突轉(zhuǎn)][落]蕭太后(唱)駙馬底細(xì)今得驗(yàn),忠孝節(jié)義擺眼前。為國當(dāng)取他的命,孫兒鐵鏡一線緣。若他取得佘氏首,天理不容立當(dāng)斬。若他不斬佘氏女,哀家今日命難全。千難萬難難難難,生死面前由他選。
這種創(chuàng)作初衷,首先是一改傳統(tǒng)京劇《四郎探母》中蕭太后扁平,從而賦予歷史人物應(yīng)有的戲劇元素——蕭太后是掌權(quán)者的縮影,殺還是不殺楊四郎,這本沒有標(biāo)準(zhǔn)界限,但卻有最后的紅線,這條紅線就是“統(tǒng)治權(quán)利是否受到威脅”。無論多么親近家屬,一旦觸碰這條紅線,那必死無疑。但是,蕭太后作為一代明主,內(nèi)心深處卻欣賞為了“忠孝節(jié)義”去越線的人,其中唱詞“若他取得佘氏首,天理不容立當(dāng)斬”就是很好的例證。楊四郎“忠孝當(dāng)頭”不殺生母佘太君的行動(dòng),使得蕭太后動(dòng)了讓四郎繼續(xù)存活的惻隱之心,但隨即而來的是“若他不斬佘氏女,哀家今日命難全”后顧之憂讓蕭太后陷入兩難,因?yàn)椤皩?shí)可嘆流言起攪我心腸,有細(xì)作在營中要把禍釀”的輿論已經(jīng)在遼國蔓延,若不遏制必將會(huì)威脅統(tǒng)治。“兩難最終要抉擇一難”,這是一個(gè)常人不易察覺的帝王內(nèi)心,更是戲劇舞臺(tái)應(yīng)該充分展示給觀眾的看點(diǎn),這種展現(xiàn)不需要過多的筆墨,一筆帶過即可,但正是多個(gè)似此“細(xì)節(jié)”進(jìn)行鋪排和串聯(lián),進(jìn)一步展示了劇中蕭太后“人”的多面性,還原和拉伸了戲劇人物應(yīng)有的多元且厚重的生命維度。
在其他人物的創(chuàng)作上,《四郎·嘆》從人物關(guān)系和環(huán)境角度也多方發(fā)掘,重新構(gòu)建必要的人物關(guān)系。從【第一場】“戰(zhàn)鼓狼煙催人淚四郎身世疑竇生”起,編劇將傳統(tǒng)京劇《四郎探母》中“敵俘入遼當(dāng)駙馬”這一讓人匪夷所思的劇情進(jìn)行圓滿處理,將傳統(tǒng)劇目中過于“簡單”的鐵鏡公主、國舅爺進(jìn)行豐滿處理,添置“小阿哥”這一角色,不斷強(qiáng)化外在環(huán)境的無形壓力,使得楊四郎出場后“假身份”的維持變得舉步維艱,加促楊四郎的忠孝選擇,這種外在環(huán)境情節(jié)矛盾的設(shè)置,彌補(bǔ)了傳統(tǒng)京劇《四郎探母》的多個(gè)敘述漏洞。原創(chuàng)京劇《四郎·嘆》正是從這種細(xì)節(jié)出發(fā),打破京劇臉譜式人物“非此即彼”的程式思維,讓觀眾自己體悟場上人物的內(nèi)心和抉擇,在欣賞京劇藝術(shù)的過程中不再因劇本漏洞問題而影響審美,從而更加深入的欣賞楊四郎在規(guī)定情境中的唱腔之美和人性展示。
為更加豐滿楊四郎的人物形象,《四郎·嘆》在一些細(xì)節(jié)上增加了矛盾沖突,如小阿哥多次“取楊家將首級(jí)獻(xiàn)給太后”嗜血話語、鐵鏡公主“難道你真的是……”隱忍無奈,這都共同反襯楊四郎在命運(yùn)面前矛盾糾結(jié)。尤其是小阿哥,這個(gè)新創(chuàng)作的角色,成為觀眾深層次解讀楊四郎另一面的重要符碼——對(duì)楊四郎來說,再多不堪回首的往事都可用麻痹內(nèi)心的方式去遮擋,但是面對(duì)親子,卻因無法亮出真實(shí)身份,只能眼看著孩子一天天在“遼蠻殺戮”氛圍中長大,聽孩子一遍遍訴說“取楊家將首級(jí)獻(xiàn)給太后”而不能制止,這種外在環(huán)境言語的設(shè)置,使得主人公楊四郎的骨內(nèi)如插鋼刀,不斷“疼痛卻無法進(jìn)行言說”;同時(shí),作為一種藝術(shù)化的抽象處理,小阿哥不僅代表了一個(gè)孩子,更是整個(gè)遼國對(duì)宋人的一種普遍殺戮情緒。楊四郎在這樣的國度中生存十五年,其精神狀況的悲慘很容易引起觀眾共鳴,可以說小阿哥時(shí)刻在提醒觀眾楊四郎的“肉體和精神”正面臨歸宿難抉的危機(jī),他“天真無邪的言語”正是逼迫楊四郎選擇自殺結(jié)局的重要原因。
二、原創(chuàng)京劇《四郎·嘆》中的楊四郎如同“被縛的普羅米修斯”,被“天神派來的獵鷹啄食那不斷長出肝藏”,為觀眾呈現(xiàn)“撕裂-填補(bǔ)-撕裂”循環(huán)往復(fù)的痛苦精神世界。
傳統(tǒng)京劇《四郎探母》第一場【坐宮】,自唱詞“楊延輝坐宮院自思自嘆,想起了當(dāng)年事好不慘然”開始,便引領(lǐng)觀眾進(jìn)入楊四郎的內(nèi)心世界,楊四郎的內(nèi)心情感一直停留在“思老母不由我肝腸痛斷,想老娘淚珠兒灑在胸前。眼睜睜高堂母難得見,兒的老娘啊!要相逢除非是夢里團(tuán)圓”的層面——身在異鄉(xiāng),想念高堂老母,把孝不能盡的心理矛盾凸顯出來——對(duì)老娘無法探望和無法盡孝造成了楊四郎的無奈和苦惱,這是《四郎探母》戲劇故事開展的“行動(dòng)因”,也是戲劇故事最為核心的矛盾沖突。這種矛盾沖突的設(shè)置和處理,放在清末民國初期環(huán)境中,對(duì)滌蕩當(dāng)時(shí)的“忠孝”刻板習(xí)氣具有突出的貢獻(xiàn),彰顯了人的本真,還原真實(shí)人性。但是,時(shí)至百年后的今日,隨著人性深度的不斷發(fā)掘,這樣的戲劇矛盾故事處理就顯得相對(duì)淺顯了。思念母親,這是楊四郎復(fù)雜內(nèi)心的重要環(huán)節(jié),但不是唯一的環(huán)節(jié)——觀眾會(huì)問,難道楊四郎十五年內(nèi)心泛起的忠孝節(jié)義的漣漪僅僅是隨著思念的微風(fēng)緩緩的蕩起來,然后輕輕的止于“思念遠(yuǎn)在宋國的母親”層面?如果不是,那么請問楊四郎“沙灘會(huì)一場敗,只殺得楊家好不悲哀,兒大哥長槍來刺壞,你二哥短劍下他命赴陽臺(tái),兒三哥馬踏如泥塊,我的兒你失落番邦一十五載未曾回來,惟有兒五弟把性情改,削發(fā)為僧出家在五臺(tái),兒六弟鎮(zhèn)守三關(guān)為元帥,最可嘆你七弟他被潘洪就綁在芭蕉樹上亂箭穿身無處葬埋”的國恨家仇哪里去了?難道只有在《四郎探母》第七場【見娘】中,通過佘太君之口說出了當(dāng)年的慘烈,才讓觀眾想到當(dāng)年楊家將的悲壯?如果是這樣,楊四郎十五年為什么不對(duì)個(gè)人“不忠不孝”行為進(jìn)行質(zhì)問和反思?亦或是十五年的心理壓抑是不是應(yīng)該依靠戲劇沖突好好的“發(fā)泄一下”?種種問號(hào),若是串起來,劇情又無法做出解答,那么久而久之便會(huì)在觀眾心中形成一種經(jīng)不住推敲的刻板印象,從而引發(fā)對(duì)《四郎探母》主題的質(zhì)疑,直至影響唱腔藝術(shù)的欣賞。
原創(chuàng)京劇《四郎·嘆》的劇本創(chuàng)作,在框架構(gòu)思上首先肯定并強(qiáng)化了傳統(tǒng)京劇中楊四郎思念母親的哀愁,使得這種思念不再單一而是變得立體豐滿——《四郎·嘆》劇本【第一場】“戰(zhàn)鼓狼煙催人淚四郎身世疑竇生”,通過楊四郎獨(dú)白處理和佘太君、楊四娘兩個(gè)“心理空間”矛盾強(qiáng)化,將人物的哀愁從思念母親“個(gè)人”行為延宕至“國家”集體的思考上,展示出楊四郎作為一個(gè)他人眼中的“叛徒”其內(nèi)心的矛盾糾結(jié),在一種相對(duì)“靜”的戲劇開場中向內(nèi)發(fā)掘,鋪墊了后兩場的“動(dòng)”的戲劇矛盾,展示了楊四郎千瘡百孔的內(nèi)心。站在“人”的角度進(jìn)一步去構(gòu)思劇本,就會(huì)發(fā)現(xiàn)恩典榮耀集于一身、內(nèi)心深處埋藏國恨家仇、有口難言的楊四郎,其出場決不能單純是一種“對(duì)母親思念的無限綿綿且無奈痛苦”,而應(yīng)是把思念作為十五年來“仇恨積壓的導(dǎo)火索”,應(yīng)該給觀眾帶來一種“久困的獵獸對(duì)國恨家仇發(fā)出的勢如波濤的怒吼”,只有這樣的人物心情,才符合十五年持續(xù)內(nèi)心糾結(jié)拷問的戲劇情境,才是歷經(jīng)了“不斷的選擇而無法抉擇”的人物內(nèi)心所應(yīng)該展示的力量。
編劇按照這樣的邏輯構(gòu)思《四郎·嘆》,開篇便散彌漫“火藥的味道”,拉著觀眾進(jìn)入戲劇情景,讓觀眾從心底里去接受這個(gè)十五年來“畏首畏尾、無能無為”的楊四郎,進(jìn)一步剖析他那顆充滿傷疤的內(nèi)心,窺探他心底深處蘊(yùn)含的“人”的真實(shí),引起觀眾心中共鳴。正是在這種構(gòu)思中,編劇繼續(xù)發(fā)掘楊四郎內(nèi)心走向更深層次,向觀眾進(jìn)一步解釋為什么楊四郎在這十五年中不殺蕭太后,不能完成儒家的殺身成仁?編劇此時(shí)從個(gè)體的“人”和國家大義出發(fā),闡釋楊四郎不殺蕭太后的原因:蕭太后提攜之情和不殺之恩讓楊四郎無法下手,這是個(gè)人感情層面;蕭太后推行的休養(yǎng)生息政策讓宋遼邊境共享十五年的短暫和平,這讓楊四郎對(duì)蕭太后的“和平大義”深深拜服,這是國家層面。無論從個(gè)體生命延續(xù)還是從大義角度出發(fā),楊四郎都對(duì)蕭太后報(bào)恩盡孝行為都是成立的,這是他十五年活下來的心理第一層面。
劇本在解決楊四郎內(nèi)心第一層面后,繼續(xù)發(fā)掘,楊四郎內(nèi)心的第二層就浮出水面:十五年來,楊四郎一直憎恨蕭太后,因?yàn)楦感滞劳龅膽K狀歷歷在目,也正是十五年前的戰(zhàn)役(金沙灘),讓楊四郎這個(gè)風(fēng)華正茂的“四將軍”做了“好比籠中鳥有翅難展、好比虎離山受了孤單、好比南來雁失群飛散、好比淺水龍久困沙灘”的“遼國富貴階下囚”。楊四郎在遼國要存活,自要趨附于蕭太后(遼國蕭太后掌權(quán)),無論內(nèi)心深處報(bào)仇的信念多么強(qiáng)烈,一旦與機(jī)體渴望生存的本能發(fā)生矛盾,個(gè)人的選擇就變得“遲鈍”起來,因?yàn)闅⑹捥蟮慕Y(jié)果是楊四郎被遼國殺,機(jī)體死亡;但是楊四郎的“楊家將”家族榮譽(yù)和長期的“忠孝禮義”“殺身成仁”的儒家觀念卻使其精神上備受折磨,機(jī)體存活的現(xiàn)實(shí)壓制殺身成仁的信念,這本身便具有糾結(jié)和矛盾。在和平無戰(zhàn)事時(shí)期,殺蕭太后的念想會(huì)被壓制在意識(shí)深處“雪藏冰峰”,但是一旦宋遼戰(zhàn)事再起,這種念頭便會(huì)迅速“死灰復(fù)燃”,與楊四郎存活的理念相互沖撞,蕭太后在戰(zhàn)場上指揮的每一次勝仗,其前提都是楊四郎的祖國大宋子民的失敗和死亡,看著宋國親人的不斷逝去,楊四郎的內(nèi)心充滿著無限愧疚和痛苦。《四郎·嘆》正是在這個(gè)曾經(jīng)叱咤疆場、如今茍延存活的楊四郎內(nèi)心層面做足文章,把他的人生“捆綁起來”,不論是“思念母親泛起的漣漪”亦或是“國恨家仇澎湃的波濤”,都隨著外在環(huán)境的不斷變化改變著楊四郎糾結(jié)痛苦的內(nèi)心、腐蝕他那曾經(jīng)激蕩的斗志,十五年前的叱咤疆場、十五年后的茍延存活,這樣的戲劇環(huán)境設(shè)置讓楊四郎那顆“雙重矛盾”的內(nèi)心從始至終懸吊在精神斗爭的崖澗邊緣。
三、傳統(tǒng)劇目《四郎探母》與原創(chuàng)京劇《四郎·嘆》因時(shí)代背景及歷史文化不同,出現(xiàn)了楊四郎“生”和“死”兩個(gè)決然不同的結(jié)局,而這兩個(gè)不同的結(jié)局,正深諳不同時(shí)代觀眾的“忠孝節(jié)義”價(jià)值選擇,也是古今觀眾面對(duì)“忠孝矛盾沖突”時(shí)應(yīng)有的本能抉擇。
傳統(tǒng)劇目《四郎探母》中,佘太君“押糧來到雁門關(guān)口”,這讓楊四郎“要相逢除非是夢里團(tuán)圓”變?yōu)楝F(xiàn)實(shí),孝悌之道促使他求鐵鏡公主為其“盜令”后出關(guān),只為“天地為大,忠孝當(dāng)先”,但在“兒豈不知天地為大,忠孝當(dāng)先;兒若不回去,可憐你那番邦的媳婦、孫兒,俱要受那一刀之苦”的道白和現(xiàn)實(shí)中,楊四郎只能“更鼓頻催時(shí)不待,若要逃走莫遲捱,狠心腸別一家回北塞”。楊四郎回歸遼營后,又是在鐵鏡公主的懇求下得到僥幸不死,有了“叩謝太后不斬恩”。這樣的安排,在傳統(tǒng)京劇中的敘事和編排上已經(jīng)算的是凝練——筆墨集中在楊四郎去國懷鄉(xiāng)、心懸兩地的復(fù)雜矛盾性格塑造上,楊四郎的思想斗爭通過“坐宮”、“回令”兩天一夜來體現(xiàn),堪稱傳統(tǒng)京劇劇本當(dāng)中緊湊適度的“樣板”。時(shí)過境遷,這種經(jīng)典劇本敘事在當(dāng)下觀眾認(rèn)知的戲劇故事矛盾構(gòu)建范疇內(nèi)仍存在缺陷——?jiǎng)”咀罱K是楊四郎“盜令探母成功還愿”、“未被斬殺又任大將”,這種略帶荒誕的結(jié)局很難讓人完成審美共鳴,在某些評(píng)論者筆下,大有“有自欺欺人的偽結(jié)局的大團(tuán)圓”之嫌。

傳統(tǒng)京劇《四郎探母》
原創(chuàng)京劇《四郎·嘆》正是捕捉到觀眾的這種“偽結(jié)局大團(tuán)圓”情緒,在繼承《四郎探母》原有精華的基礎(chǔ)上重新構(gòu)建故事結(jié)局,重新界定故事本應(yīng)有的發(fā)展軌跡,讓一個(gè)在十五年前就該戰(zhàn)死沙場卻未死的楊四郎通過再臨戰(zhàn)場對(duì)抗親人、規(guī)勸不能而自刎的方式完成其在精神上的解脫。楊四郎的死亡表面看似是痛苦的,但深層表達(dá)的卻是個(gè)體獨(dú)立的“人”面對(duì)“忠孝矛盾”沖突后對(duì)尊重自我的最佳選擇。

原創(chuàng)京劇《四郎·嘆》
從原創(chuàng)京劇《四郎·嘆》【第二場】“家國人倫難抉擇巧試金湯萬念灰”起,楊四郎無奈接受蕭太后“出兵北天門,手刃楊家將”的命令后,意味楊四郎很快就要與老母、六弟在戰(zhàn)場上互為其主亮刃廝殺。如此殘酷任命和身不由己的選擇將楊四郎的這種本已無歸屬的“身份”延續(xù)擴(kuò)大——熱血男兒當(dāng)“愛國忠義”,但“愛國”愛的是“哪國”?“忠義”忠的是“何義”?【第三場】“血綻沙場命歸陰 可嘆亡魂聚邊關(guān)”,楊四郎選擇通過結(jié)束個(gè)體生命來終止這種無間身份,這也是劇情發(fā)展和人性選擇的必然。因?yàn)榛钤跁簳r(shí)真空中不去面對(duì)忠孝的個(gè)體,一旦出現(xiàn)在社會(huì)歸屬和矛盾現(xiàn)實(shí)的集體面前就應(yīng)當(dāng)也是必須做出選擇。楊四郎最終以個(gè)體的死亡成全和維護(hù)了兩個(gè)軍事集團(tuán)各自的“禮法尊嚴(yán)”,以肉體的消失為兩個(gè)國別洗刷出他們集團(tuán)內(nèi)部不和諧因素——“叛徒”“奸細(xì)”,原創(chuàng)京劇的這樣處理與傳統(tǒng)京劇《四郎探母》楊四郎最后“把守北天門躲過一劫”“兩個(gè)軍事集團(tuán)都明白楊四郎的身份又紛紛釋懷和原諒虛偽大團(tuán)圓”結(jié)局有著本質(zhì)的不同。《四郎·嘆》中以楊四郎無法抉擇忠孝大義的悲劇“結(jié)疤”引導(dǎo)著角色的一步步的行動(dòng),也讓劇中的四郎無時(shí)無刻不在進(jìn)行著“哈姆雷特式”的痛苦抉擇和思考,直至楊四郎自刎,“生存還是死亡”已經(jīng)完全傳遞給了劇場的觀眾,楊四郎的命運(yùn)抉擇仍刺激著觀眾的神經(jīng),從而讓這種宣泄著“只有死亡才是主人公解脫”的終極核心脫穎而出,這最終全劇營造出一種波德萊爾式的“殘酷的詩意”,頗有幾分西方戲劇人物“靈魂手術(shù)”解剖后的悲壯與美感。
弗洛伊德在《戲劇中的精神變態(tài)人物》中談到戲劇時(shí)曾對(duì)情感有過這樣的言論:戲劇的目的在于打開我們情感生活中快樂和享受的源泉,……揭開這樣的源泉卻是理性的活動(dòng)所達(dá)不到的。……在這一方面,基本因素是通過發(fā)泄強(qiáng)烈的情感來擺脫一個(gè)人自己的情感的過程。其中“發(fā)泄強(qiáng)烈的情感來擺脫一個(gè)人自己的情感的過程”頗讓人有所啟迪,或許這句話在整個(gè)戲劇藝術(shù)宏偉篇章面前只是一個(gè)小小單元,但卻成為對(duì)原創(chuàng)京劇《四郎·嘆》氣質(zhì)特征相對(duì)精煉的總結(jié)。忠孝矛盾沖突升級(jí)后,楊四郎個(gè)體心靈陷入無間之地,成為了國家、社會(huì)及家庭中“不該存在的存在”,其悲劇性展開如同徒手剝開一個(gè)形狀并不規(guī)則更是難以去剝的洋蔥,其悲歡無奈充斥在劇場的氤氳氛圍中,釋放出觀眾心靈深處的同情淚水。
原創(chuàng)京劇《四郎·嘆》抓住楊四郎身份問題進(jìn)行創(chuàng)作,彰顯的是人們在面對(duì)“忠孝不能兩全”選擇時(shí)古今共通的焦慮。為了更加的凸出在“忠孝不能兩全”無法抉擇的境遇,《四郎·嘆》的創(chuàng)作重點(diǎn)更在楊四郎的心理結(jié)構(gòu)方面進(jìn)行深層次的刻畫和處理,使得作為一個(gè)具象與抽象相結(jié)合的“叛徒”楊四郎其內(nèi)心深處自第一幕始便處于痛苦難耐且無法歸屬的左右搖擺狀態(tài)中,“殺身成仁是我(楊四郎)楊家男兒的豪氣本色,是我名門忠良一貫血脈正統(tǒng),更是我隱姓埋名、甘作俘虜?shù)恼嬲康模遥遥覅s做了什么……一十五年我無法抉擇,我這心(倉)。手中三尺龍泉?jiǎng)Γ愀嬖V我,我該何去何從,何去何從……”這種處于兩難無間的心情,按照《法華經(jīng)》與《俱舍論》中的佛語解釋,是一種無盡的“Avicinar-Aka”(中文即“心靈的無間地獄”),戲劇環(huán)境不斷惡化和人際關(guān)系的推動(dòng)(鐵鏡公主無奈隱忍、小阿哥嗜血天真、蕭太后陰沉試探、楊四娘凄苦等待、佘太君思念悲哀),使得楊四郎一直陷入“心靈的無間地獄”無法逃脫,一種時(shí)時(shí)困擾和阻斷使得他無法做出選擇卻必須選擇,這最終使得楊四郎的心靈呈現(xiàn)出一種游離狀,這種心靈上游離,加劇了楊四郎“不該存在的存在”本質(zhì),推著楊四郎進(jìn)行悲劇性的選擇。觀眾們明顯感受到這種選擇的推動(dòng),更在等待編劇、導(dǎo)演、演員、舞美如何將這種“游離”一層層撥開,而在慢慢剝開著層層矛盾之后發(fā)現(xiàn),觀眾心靈深處那一股同情的淚水已經(jīng)宣泄了出來。
楊四郎的痛苦不僅止于個(gè)人,更在于群體。楊四郎的悲劇性如同貫穿全劇的一條線,最終勾起的是“劇中所有親人靈魂深處無時(shí)無刻都在忍受的那份抉擇的痛苦”——“楊四郎-鐵鏡公主”“楊四郎-小阿哥”“楊四郎-楊四娘”“楊四郎-蕭太后”“楊四郎-佘太君”“楊四郎-眾人”直至“楊四郎-忠孝”的抉擇。環(huán)境外力將楊四郎推到必須做出選擇的邊緣,也將所有人推至選擇的邊緣——“生存和死亡”“親情和大義”“家庭和國家”“個(gè)人和集體”之間的劇烈斗爭匯聚在一起,使家國成為了戰(zhàn)爭的俘虜,使得參與其中的所有人陷入了戰(zhàn)爭的“無間地獄”中——誰都不能逃脫內(nèi)心對(duì)祖國“忠孝”,誰都不能割舍對(duì)親情的“忠孝”,更沒有誰能夠在戰(zhàn)爭面前獨(dú)善其身,因?yàn)閼?zhàn)爭的本質(zhì)就是盲目、殺戮和別離。至此,沒有任何說教,但是向往和平,批判戰(zhàn)爭的主題已經(jīng)從觀眾心中自發(fā)生起。這種“靈魂”和“內(nèi)心”的拷問和戰(zhàn)爭面前任何人沒有歸屬和棲息的痛苦狀態(tài),讓舞臺(tái)上所有人物形象都變得豐滿起來,這種“無間”狀態(tài)更是構(gòu)成觀眾審美期待,成為激發(fā)觀眾心中潛意識(shí)進(jìn)行自我觀賞和剖析的重點(diǎn)。
結(jié)語
中國社會(huì)重視宗法秩序,推崇“忠孝節(jié)義”倫理道德。但正是“忠孝節(jié)義”倫理道德的沿襲和積累,使得國人產(chǎn)生相對(duì)保守的慣性心理,束縛著國人的審美視野和藝術(shù)創(chuàng)作。進(jìn)入21世紀(jì)以來,京劇藝術(shù)的時(shí)代審美發(fā)生新的變化,人們對(duì)京劇藝術(shù)在展現(xiàn)歷史人文、展示自身品格層次有了新的要求,如何繼承傳統(tǒng),反思傳統(tǒng),認(rèn)知?dú)v史,反思?xì)v史,構(gòu)建富有歷史厚度和人性深度的京劇作品是新的研究課題。而如何更好的豐富京劇內(nèi)涵,延續(xù)國劇“國粹”精髓,更是一項(xiàng)光榮而又艱巨的任務(wù)。原創(chuàng)京劇《四郎·嘆》從劇本構(gòu)思開始,編劇就要讓觀眾沿著楊四郎的選擇繼續(xù)深入思考——如果楊四郎不猶豫,選擇手刃蕭太后,為宋國盡“大義”而犧牲,那么“大義”的概念是什么——是十五年前楊四郎父兄戰(zhàn)死,如今終能痛快手刃蕭太后(岳母),實(shí)現(xiàn)一報(bào)還一報(bào)公道和公平?這算不算大義,如果這算大義,大義之后呢?楊四郎在遼國的妻子鐵鏡公主、兒子小阿哥怎么辦?為大義而犧牲現(xiàn)實(shí)妻兒的生命?如果這種大義成立,那么人性又在那里?為了所謂的“大義”而舍去無辜的親人,這明顯不符合當(dāng)下大眾的審美。原創(chuàng)京劇《四郎·嘆》展現(xiàn)楊四郎十五年來內(nèi)心波瀾,通過四郎串起所有劇中人基于“人”的本性而構(gòu)建的戲劇行動(dòng),引領(lǐng)觀眾體味那份哀嘆情愫,形成一種對(duì)京劇傳統(tǒng)藝術(shù)的獨(dú)立思考,展現(xiàn)出當(dāng)代人對(duì)傳統(tǒng)京劇文化精神應(yīng)有的解讀。
[1]張庚:《中國大百科全書·戲曲曲藝卷》,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3年版.
[2]蘇國榮:《戲曲美學(xué)》,文化藝術(shù)出版社,1999年版.
[3]葉秀山:《古中國的歌—京劇演唱藝術(shù)賞析》,中國人民大學(xué)出版社,201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