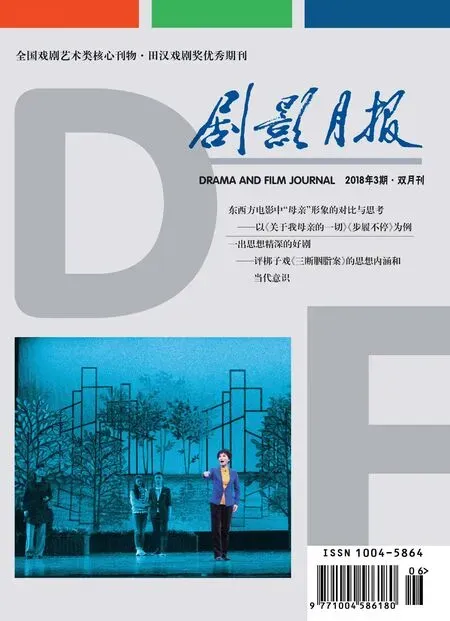揚劇“金派姚腔”的形成
■徐有明
煙波浩渺的瓜州南岸、鐘靈毓秀的鎮江城自古便是一片人文薈萃的沃土,有著層出不窮的藝術名流和傳世名作。解放以后,一代揚劇宗師金運貴先生受邀從上海來到鎮江,將自己的一方戲臺從十里洋場的大上海遷徙至此。自那以后,古老的京口潤州就成為了揚劇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歷史重鎮。時至今日,金先生和她創立的金派藝術依舊是最具知名度的名家和最具代表性的派別。此外,著名揚劇表演藝術家、金先生的嫡傳弟子姚恭林老師可稱為江蘇戲劇屆、乃是整個江蘇文藝界的一面旗幟,他在金派藝術基礎上改良,和潤澤的“金派姚腔”備受幾代揚劇從業者和基層觀眾的青睞和追捧。縱觀當今的揚劇生角人才隊伍,十之八九都是在沿襲著姚老師的創作思路,去嘗試著不同人物的刻畫,金派梳妝臺、金派數板等經典曲牌幾乎會出現在任何一臺揚劇演出中。鑒于此,筆者擬探討在“金派姚腔”形成過程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幾個因素。
經年累月的舞臺實踐過程中,金先生毫無保留地將自己的藝術精華傳授給姚恭林老師,日益豐滿著姚老師的藝術羽翼。正所謂棋逢對手、將遇良才,師徒二人不僅在身段展示、嗓音條件等方面具有著諸多先天的共同特點,而且有著趨同的人生追求和價值取向,這也讓她(他)們能迅速成為亦師亦友的親人和朋友,姚老師的藝術之路也得以越走越寬、越走越迅捷。作為領路人和授業恩師,金先生對姚老師的成長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從《十五貫》到《二度梅》,從《紅樓夢》到《西廂記》,一出出經典劇目的打磨和編排過程,就是姚老師練就自身過硬藝術技能的過程,一個個經典唱段的學習過程,就是姚老師日益提升自己唱腔水準的過程。筆者認為,如果沒有金運貴先生的悉心教誨,姚老師就不能很完美地繼承師傅和最原始的金派藝術,進而就不會有姚老師越來越寬廣的發展空間,更不會在此基礎上形成屬于自己的“姚腔”藝術。
金先生是引領姚老師叩開了藝術之門的伯樂,但姚老師能不負眾望地成為馳騁疆場的千里馬,另一個原因還是源于自身的揚鞭自提。如果說金先生在唱腔上給予了姚老師靈感和點撥,那么對于形體的塑造、對于舞臺表演力的提升,更多的還是姚老師自身的追求和探索。事實上,揚劇作為地方劇種,演職人員更多的還是對唱腔的把握,即如何將大段經典唱腔拿捏得當,進而與原唱相媲美。如何在演唱中既體現出激情,又體現出揚劇的本味等。以金先生為代表的老藝人確實為我們留下了寶貴的遺產,值得揚劇人仔細體會和揣摩。
姚老師能脫穎而出成為大師級的藝術家,更值得贊許的是他在舞臺表演方面的深厚造詣。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姚老師逐漸成為了原鎮江市揚劇團當仁不讓的臺柱子,他一方面豐富和完善著金派的聲腔架構,形成了自身柔潤婉轉的演唱風格,另一方面,他不斷學習舞臺表演方面的知識和技藝,在會唱戲的同時更會演戲,切實做到了唱念做打的全方位進步。筆者認為,這種理想理念和舞臺實踐在揚劇界是一種實實在在的超前和革新,也將揚劇的綜合舞臺藝術水準向前推了一大步,使得揚劇有了一個長足的進步和發展。揚劇從此不僅是耐聽的地方戲,更成為了耐看的舞臺劇。
上世紀八十年代后期及九十年代初期,鎮江揚劇團及整個揚劇都步入了相對蕭條的低谷。種種原因,鎮江市揚劇團經過改制后不復存在,姚老師依然沒有停止對揚劇的傳承和發展。在相關方面的支持下,他和原江蘇省揚劇團的著名二胡演奏家盧小杰、著名揚劇表演藝術家朱余蘭組成了日后被譽為“鐵三角”的創作陣容,為觀眾錄制了《三試浪蕩子》《孟姜女》《貍貓換太子》《梁祝》《庵堂相會》《孔雀東南飛》《韓湘子戲妻》等大量經典作品,在姚老師的揚劇生涯,書寫了濃墨重彩的一筆。“鐵三角”時期的姚老師正直藝術生涯的巔峰,唱、做能力都已達到了省內無出其右的境地,加之盧小杰、朱余蘭兩位省團藝術家珠聯璧合的烘托與配合,彼時的作品本本都是經典、出出都值得回味、句句都體現著姚老師對揚劇與眾不同的認知和領悟。
戲曲是角兒的藝術,支撐角兒的毫無疑問是那些享譽內外的作品和最具代表性的唱段。姚老師在他輝煌燦爛的舞臺生涯,橫跨數個行當,留下了不勝枚舉的人物形象。但最讓姚老師聲名鵲起的,毫無疑問還是《珍珠塔》和里面的主要角色方卿。每個劇種、每個藝術家或許都會留下彪炳史冊的名劇和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但如姚老師這樣將一個人和一個角色劃上等號的真的很難能可貴。盡管《珍珠塔》里方卿的扮演者數不勝數,盡管“三年前”這樣的唱段被一次次的傳唱,但觀眾提及《珍珠塔》,提及“三年前”時,腦海里只會出現姚老師一個人的身影,這就是角兒的魅力。能達到這樣的成就,在整個江蘇乃至整個華東的藝術圈中也為翹楚。正是有了這樣一臺戲,這樣一個深入人心的角色,“金派第一小生”的美譽才不再浪得虛名,“金派姚腔”的說辭也就顯得是那么的順理成章。
姚老師和他的“金派姚腔”藝術,是在漫長的歲月中積淀而成的,是觀眾和一線演員自發選擇的,與任何的評獎評優無關,與任何的虛名無關,這是姚老師半個世紀艱辛付出的一種回報,值得我們所有青年演員學習和敬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