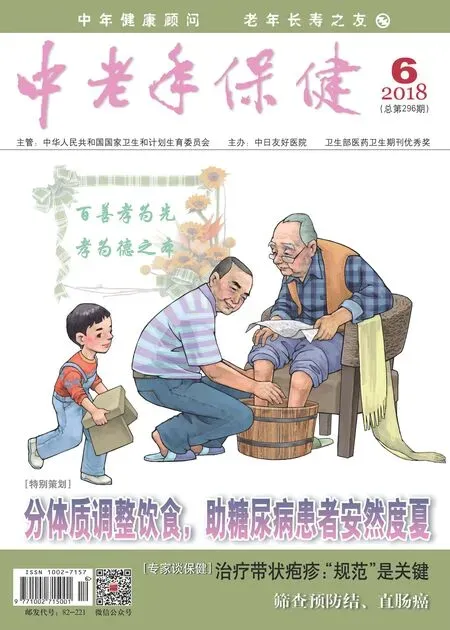非甾體類消炎藥,不能再這樣吃了
文/中日醫院疼痛科主任醫師 樊碧發 主治醫師 劉波濤 圖片提供/壹 圖
5年后的復查
張大爺膝關節疼痛有5年了,當初去醫院看病的時候,就診斷是“膝關節退行性骨關節炎”,醫生開了一些止痛藥讓張大爺先吃著,并囑咐他兩周以后去復查。張大爺吃了這些藥以后,覺得膝關節疼痛明顯緩解,就懶得去復查了。這以后,只要膝關節一出現疼痛,張大爺就跑到藥店,照著原來的藥方買藥回來自己吃。吃幾天就沒事了,張大爺也就習以為常了。
這一晃就是5年過去了,張大爺慢慢發現有點不對勁了:原來吃止痛藥,也就是兩天,疼痛就明顯緩解了,可現在連續吃5天也沒有顯著改善,而且隨著吃藥時間的延長,上腹部總是有些隱隱約約的不舒服。張大爺一琢磨,這個事情不能再不重視了,他趕緊去醫院的疼痛科,把晚了5年的復查補上。
疼痛科的門診醫生詢問了張大爺的情況,對他的膝關節進行了詳細的檢查,并復查了膝關節X線片,考慮是膝關節骨性關節炎有進展,但還沒有到需要手術的地步,所以接下來還是要以藥物治療為主。藥物的選擇主要是非甾體類消炎藥(NSAID)和氨基葡萄糖等。張大爺以為這次和5年前一樣都是拿藥方去取藥就可以了,可是拿到手的卻是一張化驗單。張大爺有些納悶,不是說要繼續吃藥嗎?怎么還要做檢查呢?

門診醫生看出來張大爺的疑惑,趕忙和他解釋其中的原委。原來,這些年,“精準醫學”的理念已經在臨床上得到了廣泛的認可,特別是藥物治療,已經有很多藥物可以做到針對個體特征進行準確用藥。所以給張大爺開的化驗單,就是為了預先估測服用某種NSAID后的療效和不良反應發生的情況,以便對患者進行個體化的用藥指導。
精準醫學的概念
精準醫學是指在大樣本研究獲得疾病分子機制的知識體系基礎上,以生物醫學(特別是組學數據)為依據,根據患者個體的基因型、表型、環境和生活方式等各方面的特異性,應用現代遺傳學、分子影像學、生物信息學和臨床醫學等方法與手段,制訂適用于個體的精準預防、精準診斷和精準治療方案。
這其中,精準藥物治療是精準醫學體系中與臨床工作關系最密切、最富于實際臨床意義的部分。精準藥物治療是根據人體基因的特征和差異,確定患者對某種藥物的適應證、適宜劑量、療效差異、不良反應風險及干預措施等,從而針對個體進行準確的藥物治療。
基因測序的現實意義
對于出現骨性關節炎、痛風或網球肘等慢性疼痛的老年患者而言,在治療過程的某個階段需要長期服用NSAID,比如氟比洛芬、吲哚美辛、雙氯芬酸鹽、布洛芬、萘普生、塞來昔布等。而我們已經知道,如果長期服用這些藥物,必須高度警惕消化道出血的風險。怎樣才能在患者服用這些藥物前就預測患者出現消化道出血的風險,并根據可能出現的療效來選擇合適的藥物和劑量呢?以往的解決方法是無差別地提醒每一位患者服藥后注意預防消化道出血,那么有些患者就因為對于這種潛在風險的恐懼而放棄服藥或減量服藥,造成鎮痛效果不佳。現在通過基因檢測就可以避免出現這樣的情況。接下來,就以治療骨性關節炎常用的塞來昔布為例,來說明基因檢測是如何在精準藥物治療中發揮作用的。
塞來昔布是昔布類非甾體抗炎藥,可以特異性地抑制環氧酶-2,阻止炎性前列腺素類物質的產生,達到抗炎、鎮痛及解熱的作用。該藥的主要不良反應就是持續使用可以增加血栓、心肌梗死、腦卒中和嚴重胃腸道不良反應的風險。目前已經發現的和塞來昔布相關的基因有9種,這其中對CYP2C9(細胞色素酶CYP450第二亞家族C成員9)的相關研究較多,實驗證據也較充分。CYP2C9是人體重要的藥物代謝酶,而塞來昔布主要由CYP2C9代謝,CYP2C9酶活性下降會導致塞來昔布在體內蓄積,從而導致血藥濃度升高,出現不良反應的風險也相應升高。CYP2C9有3種基因型:AA型、AC型和CC型。AA型的患者發生消化道出血的風險較低,一般維持正常劑量即可,該分型在中國人群的分布頻率為89.4%。而AC型的患者發生消化道出血的風險增高,需要減少劑量,該分型在中國人群的分布頻率為10.6%。還有就是CC 型,這樣的患者發生消化道出血的風險進一步增高,需要進一步減少劑量,值得慶幸的是,該分型在中國人群的分布頻率為0。
一般而言,對于已知或懷疑為CYP2C9慢代謝(AC型和CC型)的患者,服用塞來昔布時需要減少50%的常規劑量或換用其他的治療方案,或者起始劑量為最低推薦使用劑量的1/2,最大劑量則為100mg/天。總而言之,就是對CYP2C9慢代謝患者來說,為了減少使用塞來昔布的不良反應,應該使用最小劑量,盡量縮短用藥時間。另外,由于抗真菌藥物氟康唑可以抑制塞來昔布的CYP2C9代謝,使其血藥濃度升高,因此同時接受氟康唑治療者應給予塞來昔布的最低推薦劑量。
所以說,根據相關基因與藥物療效及不良反應的關系,以及在中國人群的分布頻率,在使用塞來昔布前,主要是檢測CYP2C9*3基因型,以指導塞來昔布的精準治療。當然,還有一個CYP2C9*2基因型,但目前證據顯示它在中國人群中無突變,所以不用特意去檢測。
后續
聽完門診醫生的介紹后,張大爺覺得自己還是比較糊涂,就記得用塞來昔布前要檢測一個特殊的基因。門診醫生聽了張大爺的感受后,笑著說這是正常的情況。因為精準醫學這個概念的提出,是2011年的事情,所以在臨床上被患者接受也是需要一個過程的。但精準醫學和循證醫學(傳統標準化治療、臨床路徑等)并不矛盾,它們是基于不同醫學證據模式的兩種不同臨床決策執行路徑。精準醫學在臨床決策上,更加依賴于受治者的個體化基因信息差異而不是施治者的經驗決策能力。
張大爺聽到這里,突然想起自己的街坊李大媽來,李大媽是肺癌伴骨轉移患者,持續性胸背部疼痛讓她痛不欲生,醫生診斷她是癌性疼痛,給她開的藥物中就有塞來昔布,看來得讓她也來檢測一下自己的基因是不是屬于CYP2C9慢代謝型。不過,她還吃著另一種藥物,好像叫鹽酸羥考酮,不知道這個藥物是否能檢測基因型。各位對此感興趣的讀者,如果想知道李大媽是否也能接受精準藥物治療,請關注我刊后續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