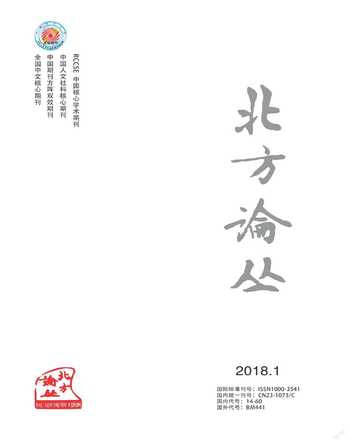現實的詩化展開:戰后臺灣現代詩的生活美學
柴高潔
[摘要]臺灣現實主義詩潮于1970年代再次興起,于詩壇外部而言是對當時臺灣內外交困歷史的反映,于詩壇內部而言,是對佶屈聱牙的現代主義詩風的反叛與糾偏。現實主義詩潮于臺灣現代詩而言并不如現代主義詩潮“風起云涌”,但作為一種潮流,卻與現代主義一起成為戰后臺灣現代詩發展的兩個重要線索與路向,且在互相對抗與學習中絞合出臺灣現代詩的詩美盛宴。站在百年新詩發展的結點回望戰后臺灣現實主義詩潮的群體構成,追索與日據時期新詩的歷史淵源,挖掘梳理其詩學維度、審美視域,以及在1980年代的變化等,或有助于窺探臺灣現代詩在歷史、政治、民族、文化等影響下生長變動的軌跡。
[關鍵詞]戰后臺灣現代詩;生活美學
[中圖分類號]1206.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3541(2018)01-0039-05
中國新詩已走過百年,臺灣現代詩作為中國新詩的重要組成部分,且因其不斷受特殊的歷史、政治、民族、文化等影響源的纏繞,表現出多元融合又特立獨行的藝術格局而備受關注。說起臺灣現代詩,撲面而來的印象總被現代、藍星,以及創世紀等詩社的現代主義詩風所左右,而往往會忽視現實主義詩歌。現代主義和現實主義雖然僅有一字之差,但內蘊所指卻風馬牛不相及。戰后臺灣現代主義者為擺脫政治上白色恐怖的壓制而不得不在精神領域“另辟蹊徑”,希冀借意象在繆斯國度自由舒展人的生命沖動;而現實主義者,則持續關注民眾、社會、土地等現世周遭,并且篤定生活的原貌實為美之根本,詩人詩寫應該具體呈現現實并給予批判,要繞開“虛無縹緲”以最直接的方式進入讀者內心,以情感細膩與映現典型引起社會共識。
戰后臺灣現實主義詩潮的崛起,可以說是繼承了日據時期臺灣本省人士的抗爭精神,只是抗爭的對象在此時變為超現實主義詩人的佶屈聱牙以及國民黨的集權統治,甚至多少還隱含著臺灣本省人與外省人之間因為歷史原因結下的芥蒂。首先,臺灣現實主義詩潮內部因為對“現實”解讀的差異也多有分支,或是把現實直接對等為臺灣,彰顯“臺灣意識”;或者是立足臺灣但并不局限于臺灣,以更為廣闊的眼光關懷現實。其次,在表現手法上,有的詩作不經由意象,在樸素直白中對臺灣的草木人事傾注全部熱情;有的精神上仍堅持寫實,但在筆法上巧妙汲取“現代”的營養,游刃有余地穿梭于現實與超現實之間,批判性與盎然的詩味交相輝映。最后,在內容上或放逐在城市,或鐘情于鄉村,書寫空間的差異性選取帶來的是對臺灣全方位的展示。
一、在反抗中“浴火重生”:臺灣現實主義詩學的兩個維度
對臺灣20世紀五六十年代現代主義詩潮的反叛與糾偏,應該是現實主義詩潮在詩學意義上興起的直接原因。其時的臺灣詩壇,內傾性是以超現實主義為代表的臺灣現代詩的主要特征,而眾所周知的原因,詩人群體向內轉是為了躲避和扦拒政治上的迫害而不得不為之。這本無可非議,但現代主義一路引吭高歌的后期卻嘩眾取寵,過分“炫技”使得詩作佶屈聱牙、艱深晦澀,最終導致詩學美感喪失且不再相融于時過境遷的時代環境。以此,臺灣本省詩人在被壓抑近二十年后揭橥而起,重申詩學奧義,以期匡正詩壇路向。白蔌自述其離反創世紀詩社的原因實為最好的佐證:“我退出‘創世紀詩社,是因為‘創世紀的朋友們引進了‘超現實主義和‘純詩,作品主題荒謬,受到‘存在主義的強烈影響,強調虛無、孤獨、異國情趣,和臺灣現實關聯薄弱”。也正是因為詩學立場和詩美標準的差異,臺灣現代詩壇慢慢分化成兩個陣營:以大陸來臺詩人為主體,摸索并實踐超現實的現代前衛詩風;以笠詩社等本省詩人為主體,則錘煉明朗、質樸的詩質。當然,臺灣現代詩壇如此分化和轉型,既是詩歌內部發展規律的自我修正,也恰巧印證著臺灣現代詩內里存在“兩個根球”,比如,笠詩社所秉持的寫實詩“浴火重生”,就是對日據時期臺灣新詩傳統的接續。
既然是“拒抗”與“重生”,那么對超現實主義的“撥亂反正”就成為笠詩社的首要任務。于此,笠詩社開始強調詩的時代性與真摯性,并以之對抗“現代派”個人化的“夢囈”寫作。趙天儀在《現代詩的暗礁》一文中,對當時詩壇的“逆流”和“流行病”做了近乎露骨的批判。他認為,詩壇中詩人沒有抱持精神獨立的操守和詩人本該有的個性,并且指出一味跟風是造成詩之“偽現代”泛濫的癥結所在,所以,趙天儀呼吁要重視詩之真摯性,“我認為真實性并非落伍的玩意,文學貴在表現的真,而不在事實的真;我所說的真實性,就是指表現的真”。這同樣是笠詩社詩觀的核心之一,也就是說,詩應該是詩人對現實的凝視與提煉,對現實的感受與創造,如果總是鐘情于遠離生活此在的意象,那么詩作流于晦澀、片面將不可避免。文學批評家盧卡奇認為,作家最可貴的地方不是有什么樣的世界觀和政治立場,而在于作家那份敢于正視現實的真誠和勇氣。也就是說,作家、詩人要忠實地反映社會,要執持真摯性的創作原則,而這也就是笠詩社等臺灣本省詩人的詩學觀念。此外,與真摯性詩觀相輔相成的就是在創作實踐中對現實的藝術復現。當詩人面對繁亂的生活周遭時,要不貶低同時也不夸大生活本身,用腳踏實地的態度去描繪普通的人和事。真摯有關感情的積聚和醞釀,但并不是感情用事,因為如此會制約作品的語言和形式,所以,現實主義詩潮的勃發,就不僅僅是與現代主義的“針鋒相對”,更為重要的是代表了一種新藝術力量的集結。
至于現實主義的批判性,顧名思義,既要著眼于現實,又要立意在批判,所以,在表現內容上多以個人與社會的對立作為主題,偏向于揭露社會的黑暗與罪惡,且表現出對底層人物的同情與憐憫。相對于中國大陸而言,批判現實主義在臺灣并不是那么順風順水,直到1970年代中后期才慢慢嶄露頭角,但毋庸置疑的是,批判性在臺灣現實主義詩潮中占有絕對重要的席位。追索其產生的原因,自然離不開國民黨的集權統治和現代詩人“逃避”現實的寫作。所以,當時代允許的時候,有良心、熱愛鄉土的詩人自會對百病叢生的臺灣痛心疾首,淤積的情感形諸筆墨,帶有褒貶意蘊的詩歌自然萌生。1980年代以后,政治詩、生態詩、社會詩的出現,更是把批判現實的詩作推向高潮。諸如簡政珍《火》、馮青《一婦人》、劉克襄《女工之死》《知識分子》等。
其實,不可否認,在臺灣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現代主義詩潮中,也有批判性的詩作存在,并且部分文本堪稱典范,不僅統籌現實與超現實,還兼顧了藝術與批判。“九月的夜晚,列車交媾著城市,/夜總會已經開門,專管區已經下班,/閃爍的電子呼吁著顧客……/可愛的荒淫!白玫瑰刺流氓的名字的乳房……/且狂吹薩克斯風,且如打七種樂器的鼓手,/放手玩過今夜!”(大荒《幻影·佳節的明日》)大荒的這些詩行,雖然“現代”意味頗為濃厚,但一幅幅的畫面仍然帶出曲折的現實指向。首先,列車交媾城市,無厘頭的組合其實暗含了一個巧妙的隱喻,如果把城市想象成一個由一圈又一圈的環城路包圍的巨大圓形空間,那么列車朝向城市的行駛,就活現了一個逼真的意象。其次,“交媾”意象與節尾的“放手玩過今夜”相呼應,中間加上“荒淫”“白玫瑰”“流氓”“乳房”等意象的點綴,對城市燈紅酒綠、荒淫無恥的揭露含蓄又深刻。同時,列車輸送旅客的意義,也暗含了人們對都市現代文明的追逐,殊不知“圍城”里的景象“別有洞天”。還有痖弦《棄婦》《馬戲的小丑》《瘋婦》等都屬此列。但是,這些少數的連帶現實的詩作,或許更多的是從詩人自身的處境出發,至于批判意識和道德目的,當時可能并不是其主要目的。
二、土地、情愛、意義:現實主義的審美視域
臺灣的現實主義詩作,多是基于對臺灣土地的情感而表現為對現實的關注。渡海來臺詩人因為“家”在遙遠的對岸,放逐的心態使他們多少難以認同腳下的土地,所以,有關“現實”的詩作大都表現在笠詩社詩人群和戰后生長于臺灣的新世代詩人群里。如果以詩社而論,笠詩社的詩路無疑與現實主義最為接近。在“笠詩社學術研討會”中,這一點也成為共識,正如林盛彬所說:“盡管‘現實主義不等于《笠》的現實詩學,個人認為從一個廣義的現實主義美學觀點來解讀‘笠詩社的主要詩想,仍不失為一種最直接而有效方法。”笠詩社對現實的堅持,其實來源于他們對“傳統”的肯認,即“永遠堅定地站在生我育我的母親‘臺灣這塊土地上,寫它的生命之美麗,它的哀愁,它的每一個歷史時期的面貌,以及它富有前瞻性的未來”。經過笠詩社前行代詩人的不懈努力和堅持,1970年代以后,秉持現實主義書寫的作品,如雨后春筍般快速增長。然而,相對于現代主義光怪陸離的技藝方法,現實主義顯得創新不夠,這多與現實詩的目的論與追求強烈的社會價值有關,但在一些個體詩人的詩作中,或彰顯技巧,或凸現情感,綻放了現實之美。
圖像詩人林亨泰的知性與現實于此就結合得非常巧妙。詩人林亨泰的詩路歷程,不僅可以看到由“銀鈴會”到現代詩社對臺灣新詩傳統銜接的努力,還可從現代詩社到笠詩社的“跳槽”,體會本省詩人的轉變與跨越,所以,呂興昌總結道:“林亨泰之‘起于批評——走過現代——定位本土的創作歷程,正是臺灣新詩發展的一個典型縮影。”現實主義精神貫穿了林亨泰三個時期的作品創作,即使在現代詩社,雖然其在文本中融入知性的思考、現代的技巧,以及運用形銷骨立的語言,但以現實為基礎的態度始終沒有改變,反而在“現代”與“現實”的結合中,內化了多元的思考。例如,其《進香圖》一詩:
這是林亨泰擅長且典型的圖像詩,他在單純的句式與簡練的語言中,融入有象征意義的符號,并借助句段的有形排列搭建“詩意的進程”。從語言上來說,這是一種巨大的破壞,詞匯除了傳達其應有的含義以外,并沒有過多的深層所指,只是對存在進行繪畫般的還原。然而,也只有在這時候,語言才能滌蕩雜質,把現實無損又直接地呈現出來,達到詩質的晶瑩剔透。從思想層面而言,《進香圖》除了在語言上去除浮華累贅的語詞,還拋棄了情緒意向,做到零情感切入,體現了林亨泰的知性思考。詩中以“旗”“蠟燭”串起“善男”“信女”,使讀者或者感受到進香隊伍的虔誠,或者滑稽于蕓蕓眾生寄托之虛無縹緲。詩人零情感的不介入,反而使讀者產生多元思考、多向體會的可能。另外,圖像詩不僅可以從語言、思想等層面分析,還會在視覺上帶來美感。由眼的直觀感受到腦意識的深度感知,再從腦的分析還原到眼所觀所看的過程,改變了詩歌傳統的欣賞路徑,美感疊生。此外,《風景》系列、《農舍》等圖像詩,也都體現著林亨泰關懷現實的詩觀。
而被譽為時代鼓手的鄭炯明,則在詩作中融入更多的情感和批判。鄭炯明的詩有一種知識分子深刻的自省意識,但又不同于一般知識分子自省以修身,他是以自省而“醒人”,所以,詩作在充分反映臺灣現實的基礎上,不僅包含詩人對悲苦人世的關愛以及對鄉土的擁抱,更重要的是對現實社會的不公平給予嚴厲的諷刺。對臺灣威權體制的諷刺和批判,是鄭炯明現實詩作的獨到之處。能在“解嚴”前不懼壓力,不觀風向,特立獨行地在詩作中開展凈化社會和心靈的工作,足見其真心和勇氣。《五月的幽香》運用各種反語結構詩篇,稀飯可口是因為有“眼淚”,公文包輕了是因為“賬單”,連尿布都有幽香,而“我”仍是孤獨的小丑享受小丑的孤獨和悲哀,把社會對人的壓抑盡顯筆端。《乞丐》通過活著的時候“沒有人看我一眼”與死之后“卻吸引成群看熱鬧的人”的對比,挖掘人性的弊端。這幾首都是鄭炯明前期的作品,文本批評有余但詩質不厚。詩人顯然并沒有止步于此,稍后的作品融入更多知性內涵,筆調也更精約沉郁。《狗》借用一直被主人戴上口罩的狗的心聲,“在我心底深谷里吠/從天黑一直吠到黎明”,控訴臺灣當局對言論自由的層層阻撓。又如,《番薯》《給獨裁者》等,都是閱讀和分析鄭炯明詩作不可遺漏的作品。鄭炯明的詩作以批判和反諷之特性,代表著臺灣現實詩的一個主要路向,即思考性強于抒情性,不追求稠密的意象,以免時代的危機感稀釋在朦朧的形式中,對時代的歌哭貫穿始終,這也是標簽其為時代鼓手的原因。
臺灣繼承現實的詩人,還有諸如對腳下土地不離不棄,因為持續關注鄉音、鄉人、鄉情而開一代鄉土詩詩風的吳晟;從心靈出發,以一股濃郁的情愛狀寫離鄉游子的詹澈;李敏勇詩作用字簡潔、節奏明快、意象清澈,環繞其間的是哀愁與美,語言魅力與批評性格特色顯著;而跨越四個詩社的白蔌,其優卓的操縱語言的能力與勇于嘗新創新的精神,使其詩作以鮮活的意象、深刻的意義享譽詩壇,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詩人們共同的努力,促成了現實主義詩潮的形成與發展,并在此后形成與現代主義、后現代主義并駕齊驅的一個大方向。然而,需要指出的是,1970年代許多現實詩作,在擁抱現實肯認本土的同時,遠離了藝術性,更有甚者,幾近情緒宣泄的感嘆與抵抗現實的吶喊,毫無詩味。審美空間的淪喪,與1970年代臺灣社會矛盾重重,而詩人又急于借詩改變現實有關。幸運的是,這種情況,到了1980年代有所改觀,一批能兼顧藝術和現實的詩人和詩作填補了1970年代留下的空白和遺憾。
三、反映與反應:臺灣現實主義詩學的深化
臺灣現實主義詩學雖然蓬勃于1970年代,但爬梳這段歷史,卻并沒有詩社與詩刊正面提出現實主義的口號,直到1980年代,才出現真正將現實主義主張明朗化的詩社。《春風》在其創刊號上明確提出:“在內容上,秉承優秀的寫實主義傳統,及其抗爭精神,勇邁前行。并認識社會的動因與方向,仔細觀察省思現代社會的人民處境,從而表現人民的心聲,傳達文學力量。”經過1970年代的社會動蕩以及文學界各種大論戰,1980年代之后,隨著政治的解凍,臺灣現代詩漸漸能成熟地面對現實的社會情景,政治詩、生態詩、社會詩、都市詩、臺語詩開始爭奇斗艷。在詩人結構方面,1980年代真正使詩切入生活周遭此在的是新世代中青年詩人。一方面,他們多出生在戰后臺灣,他們面對的就是有血有肉的現實生活環境,而少有“前行代”詩人對海峽對岸的情思繾綣;另一方面,經過1970年代的詩學試練,他們已經羽翼豐滿,有些已然博得“功名”。1980年代相對開放和穩定的環境,使他們可以大展拳腳,但這同樣也是一個挑戰。新世代詩人在關懷現實之時,既不愿意復制“前行代”詩人已就的題材和風格模式,也不想重蹈1970年代意識形態吶喊式寫作的覆轍,所以,他們另辟蹊徑,著力于語言的調整,在現實與想象之間搭建虹橋,借助新的題材和技巧,延展美學深度。
相對于1970年代,1980年代的現實詩強調如何用語言調變現實而非復刻現實,也就是以心靈觀照的真取代肉眼所見的實,詩要源于生活,但不僅僅是反映現實,而是詩人對現實的反應,此中,彰顯著詩人的睿智和詩美的魔力。
首先,他們的詩從現實出發,經由意象的凝練和轉換,再回歸現實,可以說糅合1960年代和1970年代的長處,于意象和現實的虛實中,投入自我意識和外在世界的整合辯證,既非漫無節制的奇思異想,也不用直白的語言裸露現實。簡政珍于此可謂爐火純青,臺灣社會的林林總總在簡政珍的詩中呈現為生命與生命的碰撞、靈魂與靈魂的對視,很少飽經憂患的頹唐姿態,也沒有聲嘶力竭的悲憤吶喊,而是以巧妙貼切的想象映襯現實真真假假的風景,于無聲處揭露社會的病態。寫于1988年的《火》,構思高妙精巧,用火勢蔓延的邏輯視角觀察社會并勾連起五個故事,以蒙太奇的手法對不同著火樓層的掃視,融合于一體竟給讀者遞交一份臺灣社會問題白皮書。午夜著火的一樓,面對升學壓力“甫剛睡眠的國四學生”在“火”的面前呆頭呆腦,還不知道“怎么安排心情”;二樓嫖娼賣淫的一對男女以為警察臨檢,驚慌失措裸身出逃;三樓生活無著的單身媽媽抱著嬰兒茫然失措;四樓沒有人跡,“墻上的掛鐘停下來”,默哀悲劇的發生;五樓退伍老兵在戰火與晚霞的夢中爬梳記憶;只有小偷逃出了橫禍,投入夜色。五個畫面的簡單組合隱喻著詩人對整個社會的思考,“火”意象的選取實指火的災難,也影射城市繁榮背后的虛假丑陋。詩歌取譬精準且不失張力,意象選擇樸實又不失韻味,詩人在敘事中刻意沉默無聲,反而使語言充滿無為的力量,而由此延伸出的對人與人、人與城市關系的辯證,不僅承載了詩人詩思的重量,還把讀者的思緒引向詩外。
其次,“都市”作為一個意象和實際生活空間,它在臺灣現代詩表現的軌跡呈現為從逃離到擁抱。在臺灣“現代化”初具規模的1960年代后期,城鄉差距及其矛盾開始進入詩人的視野。此時的都市書寫往往被置于鄉土的對立面,即邪惡對比善良、骯臟對比純潔、地獄對比桃花源。如黃勁連寫于1960年代末的《悵悵臺北街頭》,“阿弟我們回去吧/回去向阿爸說/所謂‘臺北/沒有什么/只有一些櫥窗/一些霓虹燈”。現代文明的價值于詩人看來不值一哂,只不過是一些“櫥窗”和“霓虹燈”。表現此類或歸鄉、或批判都市的主題在當時臺灣詩壇為數不少,例如,黃樹根《讓愛統治這塊土地》,把望鄉的辛酸表現得淋漓盡致,“幾把辛酸也都/也都溶入故鄉塵埃的覆蓋里”;葉笛《醉酒的人》,傳達了城市人與人之間的冷漠;等等。1980年代,更年輕一代詩人的作品,多少脫離了此前“現代派”及“鄉土派”舊有的都市觀,他們對都市除了批判以外還有擁抱,除了整體觀照以外還有局部的體驗。相比于“前行代”和1940年代出生的詩人,都市對于新世代詩人來說就是“我們生活面對的現實”(林耀德語),“都市的發展不僅改變著物質景觀,同時也使作家的審美趣味和美感標準發生變化,它的文化形態改變了作家的時間、速度、距離感,使他們將這種受洗后獲得的都市精神融入詩學實驗”。林耀德堪稱都市寫作的佼佼者,其詩集《都市終端機》《都市之甍》以成為標簽其為都市寫作者的典范,他善于選取散落在都市各個角落的站牌、紅綠燈、公園、廣場、道路等物質符號,并從這些物質符號出發,引申出都市人精神世界的焦慮意識,甚至把觸手巧妙延伸到臺灣社會、政治、經濟等問題上。“紅燈/愛國東路/限速40公里/黃燈/民族西路/晨六時以后夜九時以前禁止左轉/綠燈/中山北路/禁按喇叭”(《交通問題》),乍看之下,詩人排列的冰冷的紅綠燈和路名符號毫無意義,讓人不知所云。但細讀之下,透過路牌和交通燈的標示和變化的對比,會驚詫于詩人巧妙至極的隱喻。“愛國”與“紅燈”,“民族”與“黃燈”,“綠燈”與“孫中山”等的搭配,詩人主觀的批判呼之欲出,并逗引出臺灣社會現實的困境。
總而言之,臺灣現實主義詩學的發展不可謂不崎嶇,從出現到壯大,大致經歷在詩作中還原生活的現實到借助語言進行重組、創新,表現具有美學韻味的局部現實的轉變。現實詩在形象塑造上囊括臺灣的方方面面,或者專注人物速寫,或者留意于歷史,或者筆觸在自然,更重要的是詩作中融入沉重的情感。詩人們注視現實生活中活生生、具有鮮明個性的人或事物,在真誠與真知中,在現實與想象的辯證中,完成一幅深具美學韻味的畫卷。
[責任編輯 吳井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