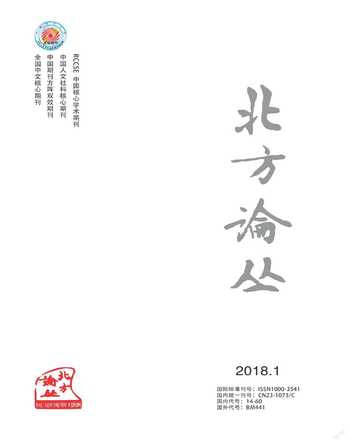土改文學視野中的知識分子形象
蘇奎
[摘要]20世紀四五十年代的土地改革是一場自上而下的社會運動,而中國共產黨的土改政策路線是依靠深入鄉村的土改工作隊來執行的。土改工作隊在改變鄉村的同時,也受到土改運動的影響,這主要體現在土改工作隊員在此過程中的鍛煉與改造,尤其是知識分子出身工作隊員。土改運動不僅僅是社會運動,更是一個觸及人思想的運動,各階層人物在外力的沖擊下,都要改變慣性意識的運行軌道。土改文學的豐富性就在于對身處其中的人物思想意識及其演變的展現,這在對知識分子的描寫上體現得尤為鮮明。
[關鍵詞]土地改革運動;土改文學;知識分子
[中圖分類號]1206.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3541(2018)01-0072-07
一、知識分子:需要改造的“異類”
近代以來,從傳統向現代轉型的中國知識分子,一直以自身的努力參與并推動社會進程。對于要進行啟蒙與救亡的中國社會來說,知識分子的作用與價值是不言而喻的。不論為啟蒙的宣傳,為救亡的吶喊,還是建立現代民族國家,都是知識分子的自覺行為,而且也只有知識分子的參與,這些訴求才能成為現實。1939年,毛澤東在《大量吸收知識分子》一文中,強調知識分子對于民族解放的價值,批判實際工作中對知識分子重要性的忽視,以及存在的排斥知識分子的現象,號召大量吸收知識分子加入革命隊伍中,“共產黨必須善于吸收知識分子,才能組織偉大的抗戰力量,組織千百萬農民群眾,發展革命的文化運動和發展革命的統一戰線。沒有知識分子的參加,革命的勝利是不可能的”。這是對知識分子力量的肯定,也體現了中共對于知識分子之于革命運動價值的理性認識,因為“所有當代的群眾運動千篇一律是由詩人、作家、歷史學家、學者、哲學家之類的人為其前導”。對于知識分子作用的正確估量與有目的的吸收,是中共領導革命走向勝利的重要因素。但是,這并不意味著在中共的話語體系中,知識分子天生具有適合革命要求的素質;相反,他們需要通過實踐的改造,才能成為真正為革命所需的一員。雖然承認“在中國的民主革命運動中,知識分子是首先覺悟的成分”,但是“知識分子如果不和工農群眾相結合,則將一事無成……真正的革命者必定是愿意并且實行和工農民眾相結合的”。
“改造”是中共關于知識分子問題的主題詞。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集中體現了中國共產黨對知識分子改造的價值目標,即作家要與工農結合,文學要為工農兵服務。當然,與強調知識分子對于革命的價值相比,《講話》更側重了對這一群體改造的必要性的闡釋,因為知識分子思想意識中有需要過濾的東西,“拿未曾改造的知識分子和工人農民比較,就覺得知識分子不干凈了,最干凈的還是工人和農民,盡管他們手是黑的,腳上有牛屎,還是比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都干凈”。“不干凈”的思想意識既是改造的內容,也是改造的起點,所謂“不干凈”是由知識分子個性化思考與革命需要思維整齊劃一之間的矛盾造成的。“一般來說,各個人的教育和知識越高,他們的見解和趣味就越不相同,而他們贊同某種價值等級制度的可能性就越少”。知識分子的獨立思考與政治要求的分裂與沖突,使執政黨必然會采取有利于陣營穩固的方法,而唯一能夠解決這個問題的,只能是改造掉知識分子“不干凈”的思想。
相對于其他領域的知識分子,中國共產黨更看重作家對于革命的價值,強調文學對革命的宣傳效應。正因為如此,從左翼文學開始,作家的創作自由逐漸受到約束,主流意識形態越來越強調文學對革命的宣傳鼓動效果。周揚曾明確地闡述了作家、文學與階級斗爭之間的關系,“無產階級文學是無產階級斗爭中的有力武器。無產階級作家就是用這個武器來服務于革命的目的的戰士”。《講話》明確指出作家如何成為能夠服好務的革命戰士,“我們知識分子出身的文藝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為群眾所歡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來一個變化,來一番改造。沒有這個變化,沒有這個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一切革命的文學家藝術家只有聯系群眾,表現群眾,把自己當作群眾的忠實的代言人,他們的工作才有意義”。對工農群眾的建構與表達只能在規定性的前提下進行,要表現出群眾對革命的積極性,描述他們身上值得知識分子學習的先進之處。在按照政治要求聯系群眾、表現群眾的過程中,作家的思想必然會與所展現的對象有所趨同。
解放區作家對《講話》精神的回應是積極的,他們一方面檢討自我脫離群眾的傾向,如周立波這樣自我批評:“我也曾經到過延安的鄉下,但沒有和農民打成一片,對農民的語言,生活和勞動,不懂和不熟,像客人似的呆了五十天,就匆匆地回到了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圈子里。”另一方面,作家們用創作來表達向群眾學習的必要性,這也使知識分子改造成為解放區文學的一個鮮明主題。思基《我的師傅》是這方面比較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小說開門見山地交代了敘述主題:“我是一個知識分子……我決心要改造去。”然而,“四體不勤、五谷不分”的知識分子,對于勞動是絕對的外行,“我到這里來學的是拉大鋸。對拉大鋸,我是什么也不懂的,什么事都得從最初的基本動作開始”。“我”的師傅年齡比“我”還小,但不論是在技術上,還是在生活上,都比“我”有經驗。“我”名義上雖然是來改造的,但內心還是有抵觸的,一意孤行的勁頭依然沒有改變。“我”的這種思想狀況在一次事件之后得到了校正,因為沒有聽師傅的勸告,“我”執拗地穿著單薄的衣服去勞動而感冒,師傅跑了十幾里山路為“我”去買藥。“我”為自己的病累了師傅而不安自責,“我想:‘人家會把我看成什么人呢?我骨子里充滿著美諦克(美諦克是法捷耶夫的小說《毀滅》里的一個知識分子——作者注)的壞血液,將天天被人嘲笑!美諦克,這是多么卑微的形象呵!滾開,我要健全的生活!”接著,作家表明“我”的心跡:“我決定明天要干干凈凈洗過澡,一切都向師傅談清楚,像他一樣生活……”“洗澡”這個意象生動而形象,對于知識分子來說,改造就是在洗澡,雖然在聯系群眾的過程中,衣服會變臟,但靈魂確實得到了洗刷——“干凈了”。知識分子的改造是通過否定自我,肯定工農的方式實現的,改造的結果就是作為個體存在的知識分子消失了,而以集體一員的身份重新登場。正如孟悅、戴錦華所說:“解放區的知識分子思想改造乃是一種消除文化差異的運動,結果是知識分子們與鄉土大眾以沒有區別的平等的方式隸屬于社會及文化權力結構。”
二、土改:改造鄉村與改造自我
土地改革無疑為知識分子聯系群眾、與工農結合提供了很好的機遇。在土改過程中,進入鄉村發動組織領導的土改工作隊中往往都有知識分子,像趙樹理、丁玲、周立波、馬加等作家,都曾經親歷過土改。對于土改,《講話》精神指引下的知識分子有著參與的渴望,馮亦代曾談及自己當年參加土改的熱情,“當我知道我可以參加政協土改二十團到廣西去土改時,我的情緒之高昂,簡直沒有語言或文字所能妥帖表達”。之所以如此興奮,是因為他完全接受了主流的宣傳和倡導,“向工農兵學習,像鳳凰涅柴”,獲得“新生”。知識分子希望能通過土改改造自我的思想,以符合主流的需要。周立波說:“經過……特別是經過毛澤東同志親自主持的延安文藝座談會,我從理性上認識了自己的脫離群眾、脫離實際的嚴重傾向,很想到火熱的斗爭中去長期地鍛煉自己。”事實證明,土改確實改造了周立波們。錢理群指出:“《暴風驟雨》的寫作,對于周立波來說,是一次自覺地與‘過去告別的努力,他一反自己的精美的藝術趣味,有意追求農民式的粗獷、質樸的美。”
中國共產黨號召并動員知識分子參加土改運動,這樣既可以增強土改的領導力量,又可以借機使知識分子與工農結合,從而實現改造后者的目的。“1949年底到1951年底,有幾十萬知識分子參加了土地改革工作隊。參加土地改革運動是許多知識分子思想的一個轉折點”。土改對知識分子構成了強烈的沖擊與改造,也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這一群體的人格、價值立場產生深刻影響。美國學者拉爾夫·林頓將人格分為兩個層次——基本人格和身份人格,基本人格就是人類所共有的人格因素,而身份人格則強調個體特定的外在反應,而且“無論在哪種情況下,那賦予人格身份最重要的社會意義的,是特定的外在反應。只要個體有了這些反應,他就能成功地運用他的身份,不論他是否有與之相關的價值觀……社會施加于這些反應的壓力是不變的,遵行者得到回報,違反者必受懲罰。即使某種特定的反應模式與個體的某一價值體系發生內在沖突,也無關緊要。雖然最先的可能很強烈,可是當反應變作自動而無意識的時候,沖突就會漸漸變小而最后消失”世紀40年代以來的中國知識分子,經歷改造的外在要求與精神獨立堅守之間的困惑沖突,在有可能被群體排斥的壓力下,認同主流的自我改造是知識分子的整體性選擇。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后親歷過土改的知識分子,紛紛表達了土改對于自身思想的沖擊,強調了這場鄉村革命對知識分子精神改造的價值意義。朱光潛在參觀土改之后的文章中說:“二十年來我的活動只限于學校的窄狹圈子,把自己養成一個‘井底蛙。這次參加了西北土地改革參觀團,有將近一個月的工夫,在鄉村里和干部與農民生活在一起,親眼看到土地改革這個翻天覆地的大變革,算是從井底跳出,看見一次大世面。”朱光潛談及的已經不僅僅是知識分子對于土改的認知與感受,而更像是一份深刻的檢討書,用土改運動與勞動人民的偉大來反襯自己的渺小。“我愿意繼續努力學習,努力糾正我的毛病,努力趕上時代與群眾,使我在新社會中不至成為一個完全無用的人”。這樣的“檢討”類的文章在當時比較流行,而且模式也比較固定——否定自己的道路,認同土改、人民的偉大。蕭乾在《在土地改革中學習》一文中說:“這是我第一次放下知識分子的臭架子,把鋪蓋搬到一個貧雇農家中,和農民一只鍋吃飯,一個床困覺。在那十來天中,我不止一次感到過去的三十幾年是白活了。”楊朔也通過與群眾對比來否定自己:“搖搖筆桿子寫點東西,比起人民創造歷史的偉大斗爭,渺小得連肉眼都看不見,有什么值得夸耀的?”這些檢討般的自我否定與質疑,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對知識分子的批判話語基本沒有差異。
對于知識分子來說,土改就像一面鏡子,映照出他們精神的“毛病”與靈魂的“渺小”。在這個時代的表態文章中,他們都不約而同地承認土改運動對于自我的救贖——土改使自己成為一個“有用的人”。楊朔反復強調是“人民改造了我”,“我知道我是永遠離不開他們了”。林庚認為改造知識分子正是土改的主題之一,“土地改革所以是一個大熔爐……非特改造了農民,而且也正改造著我們這些知識分子”。一些知識分子在幾十年后回憶土改的時候,依然強調其對自我的改造意義,“參加土改,對我來說是人生的重要轉折,也是一次深刻教育”。通過土改認識到,“群眾的智慧,高于個人的智慧,也在各種斗爭的場合中,表現得非常透徹而明顯,因此小資產階級那種自高自大的心理,在群眾的偉大力量之前,也就由減低以至于消失了”。甚至有人說:“土地改革運動……對參加這次運動的大批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所起的作用,是怎么估計也不會過分的。”當然,并不是每一個人都抱著接受改造、爭取做一個“有用的人”的思想去參加土改的,“我當時是抱著好奇的心理,反正苦也就苦半年的心情,高高興興的出發了”。“對于年輕幼稚的我來講,雖然興高采烈地報了名,但總還多少抱有好奇和好玩的心情”。然而,不論參與土改的動機有何差異,但知識分子受到教育和影響是一定的,差別也僅僅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作家不但被要求參與土改運動,而且他們還要以文學的方式對土改進行闡釋與建構。也就是說,在這場運動中,作家不但要通過土改改造自我,而且要在文學創作中表達知識分子的改造問題。相對于知識分子改造結果的難以檢閱衡量,文本中知識分子的改造卻是可見可聞的。所以對于作家來說,他們的文學作品就是他們的“表態”文章,不論土改主題小說、戲劇還是詩歌,都與朱光潛、蕭乾等人的“檢討書”存在同構的對應關系。與當時知識分子的“檢討書”主要表達自我改造過程與改造趨勢所不同的是,土改文學更側重對知識分子諸如“脫離群眾”等弱點的呈現與否定。這種情況的出現大體源于兩個方面的原因:一方面通過批判性的描述可以表達作家對知識分子弱點認識的深刻,以及堅決改造掉“舊我”的決心。就像丁玲對與自己一樣因文章“惹禍”的王實味的批判一樣,其目的是通過如此“表態”來拯救自己。另一方面,主流意識形態對知識分子的形象建構也有著規定性,《講話》明確表達對當時知識分子表述的不滿,“他們在許多時候,對于小資產階級出身的知識分子寄予滿腔的同情,連他們的缺點也給以同情甚至鼓吹”。不允許同情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所以,作家對他們就必須表現出強烈的批判態度,“對于知識分子形象的歪曲,實際上是作家對某種并不明確的理論的自覺印證和演繹。出于對政治偶像的極度崇拜和對具體政策的循規蹈矩,他們無法以公正的眼光正視自己,當然也無法客觀地審視他人”。作家在使自己的創作服從一種理念的時候,其文本不可避免地表現出絕對化與過度化的傾向,對知識分子否定性的價值判斷與書寫取向,是20世紀四五十年代土改文學的整體性行為。
三、“文采”模式
丁玲《太陽照在桑干河上》中的文采,是20世紀四五十年代土改文學中最為典型的知識分子形象,“文采這個人物體現了毛澤東對‘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想象和定義”。作家對文采所持的是徹底的批判否定的態度,在《(太陽照在桑干河上)俄譯本前言》中,丁玲說:“文采不是一個堅定的共產黨員,他是尚未克服小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知識分子。他的書呆子作風顯得非常可笑。他滿懷良好的愿望從事土改,卻成了教條主義的俘虜,犯了右傾毛病,找不到接近群眾的門徑。我自己在農村工作時就曾遇到過這樣一些黨員,這甚至還是在毛主席批評了知識分子的這種毛病之后的事情。”作家強調文采這一形象是有其現實原型的,然而,在小說中,丁玲對文采的塑造卻存在過度化傾向,“在書中知識分子的身影背后,彌漫的是丁玲這個知識者對知識分子的強烈‘蔑視欲望,這使她沉迷在對知識分子進行丑化的游戲中而無從自拔,導致的直接后果便是知識分子形象的丑化與平面化、單一猥瑣化”。知識分子可能確實有文采那樣的缺點,但不太可能會存在一個一無是處的知識分子,方方面面都表現得幼稚而無能。對文采的極端而徹底的否定,可以看作丁玲迅速與“舊我”劃清界限的一種努力。
在小說中,丁玲拿出三節的篇幅來專門描述文采,通過三個角度來展現這個工作隊長的缺點:一是直接描述他自身脫離實際脫離群眾的情況;二是將其與工作組中楊亮和胡立功進行對比;三是借革命干部章品的雷厲風行的作風進行反襯。革命要求知識分子深入群眾,聯系群眾,與群眾結合,這一倡導的前提就是對知識分子思想、行為脫離群眾傾向的判定,所以在土改文學中,著重敘述的就是知識分子脫離群眾的言行心理。從這個角度來看,文采絕對是一個具有典型意義的形象,丁玲突出表現了知識分子文采脫離群眾的個性特征。在“六個鐘頭會”上的發言,文采用足了氣力,不過從實際效果上看,這個只注重理論,不考慮農民接受實際的長篇發言,卻適得其反地打消了農民本以高漲起來的積極性與革命熱情。如果說文采開會發言脫離群眾,是因為不熟悉農民實際的客觀原因造成的,那么他不深入群眾,甚至厭煩蔑視群眾,則完全是他主觀上脫離群眾所致。第二十三節標題是“下到群眾里面去”(原文就是有雙引號的),比“六個鐘頭的會”更直接地表達了對文采脫離群眾的批判。在與劉教員的聊天中,文采覺得很不耐煩,懷著迫不及待的心情離開了學校;之后,與合作社主任任天華的交談也是中斷了;遇到只顧發泄憤懣情緒的劉滿,“文采覺得這人有些神經失常的樣子,便不再問下去,一直往回走”。在與群眾“接觸”的整個過程中,文采也只與狡猾的張正典有比較深入的交流,因為張正典說的,都是他比較愛聽的。輔仁大學校長陳垣在土改期間的自我批評文章,正應和了作家對文采的否定:“我們知識分子的通病,就是自高自大,覺得自己了不得,架子搭起半天高,平日看不起廣大的工人農民,拿起筆來就說‘販夫走卒、引車賣漿之流不識字。其實多識幾個字,多念幾部書,有什么了不得。”
丁玲還設置了胡立功、楊亮這兩個土改工作隊員,來與文采的思想行為進行對比。胡與楊不是高高在上地夸夸其談,而是采取切實有效的工作方式深入群眾走訪調查,掌握了暖水屯的實際。他們的存在體現了土改工作隊整體上的正確性,文采這樣的人只是這個群體中的個例,土改并不會因為文采這樣的脫離實際的知識分子而改變路徑。章品是工農出身的干部,他存在的意義與胡、楊相同,作家意在通過章品的有力領導來反襯文采的無能。這個雷厲風行的縣宣傳部長的到來,馬上改變了文采領導下遲遲打不開的斗爭局面。這個對比不但進一步否定了知識分子的軟弱無力,而且同時肯定了工農出身的干部的能力。雖然《太陽照在桑干河上》在當時被廣泛認可與肯定,但與其后出現的土改文學比較來看,這部小說并沒有成為土改書寫所效仿的模板,因為《太陽照在桑干河上》所描述的土改發動組織過程,與中共對土改運動的規定性步驟和程序存在很大出入。然而在20世紀四五十年代的土改文本中,對知識分子否定的取向,卻是《太陽照在桑干河上》所確立下來的。這一表述傾向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后的土改文學所承繼下來,成為此類文學的一個基本的敘事模式,我稱其為“文采”模式。
王西彥《春回地暖》中的工作隊長肖一智,也是那種需要改造的知識分子。與文采的缺欠比較起來,肖一智顯然更難符合土改運動的需要。王西彥對肖一智的形象塑造顯然受到丁玲的影響,在肖一智身上有著非常鮮明的文采的影子。比如,他開會講話冗長,不符合農民的領悟水平,不考慮分別地對待演講對象,等等。雖然沒有像文采那樣,把會開了6個小時,但他也整整講了兩個半小時;他往往只注重理論而不聯系實際,雖然把《列寧主義問題》讀了五遍,但在實際中還是一無用處。肖一智的行為引來工作隊員的紛紛指責。在受到農民和工作隊員屢次批評后,肖一智情緒失去了控制:“我肖一智不要當這個組長!”“你們看不起我,沒有關系,我就不干這個組長!”當然,這些話一出口又招來了新的指責——因一己之私而置革命大義于不顧,作為工作隊長的這種言行勢必給土改運動帶來影響。沒有人懷疑肖一智是懷著獻身精神下鄉參與土改運動的,他也檢討自己:“例如在工作上缺乏主動性,也還不能完全密切聯系群眾——這些我都承認。”然而,他同時在追問:“為什么他們對人抱成見呢?為什么要那樣不尊重像我這樣的知識分子呢?”一方面是他的言行使別人產生對他脫離群眾的認識;另一方面,革命時代的風尚之中,暗含了一種對知識分子有缺點需要改造的這樣先入為主的觀念。所以,肖一智稍有不慎,其知識分子身份很容易成為被批判的靶子,甚至一些無關知識分子的弱點,也會統統歸結于此。
如果說脫離群眾的缺點還可以通過接近群眾、聯系群眾來克服,那么在革命中敵我不分的錯誤就不僅是工作方式問題,更牽扯到個人的階級立場。在這方面,《春回地暖》對知識分子的否定,顯然要比《太陽照在桑干河上》走得更遠。肖一智對待地主家庭出身的女人羅佩珠的態度,也是他備受批評之處,肖一智同情羅佩珠,后者也看準了這一點,經常以他為突破口來躲避批斗。當羅佩珠被清理之后,肖一智還找領導為她說情。雖然他對羅佩珠有自己的看法:“地主出身和地主本人是兩個不同的概念,不能混為一談;其次,她的娘家是不是地主呢?婆家的地主成分,是不是已經完全確定了呢?都還是問題。”如果用現在的眼光來看,肖一智這種衡量人的標準和方式毫無疑問是正確的,但在階級斗爭呈現出非理性態勢的時代,他的這種思考必然會受到質疑。在階級斗爭語境下,知識分子肖一智很難逃避被否定的命運,所以,他不斷遭受各個方面的批評。在這樣的情勢下,被人詬病的知識分子的軟弱性又體現了出來,肖一智無論思想行為都與群體、革命運動不合拍。最終他以自己的胃病為借口而申請回城,逃離了這個失意之地。畏難之后的逃避被區委書記做了定性:“我看主要不是胃病問題!”“主要是沒有解決好自己的立場。”至此,小說完成對肖一智這個知識分子的由表及里的批判,他的問題已經不僅僅是脫離群眾、脫離實際那么簡單了。
知識分子存在備受質疑的兩面性——參與革命的積極主動與革命受挫折后的消極、逃避,茅盾在《蝕》三部曲中對此有經典的表述。在中國共產黨改造話語中,當然包括對知識分子軟弱性的改造,旨在使他們像工農干部那樣信念堅定,而不為一時的失利而動搖。作家正是從這個角度對知識分子進行深入的批判和否定,因為對于革命來說,任何動搖和軟弱都可能會影響斗爭走向。肖一智面對“困境”的軟弱與逃避,是不為革命話語所允許的,他的身上有比文采更加致命的弱點。
當然,并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后的每部土改小說中的知識分子都像文采、肖一智那樣“冥頑不化”,不可改造。土改文學在對知識分子的弱點進行批判展示的同時,也要表達出這一群體向符合主流要求轉變的趨勢。土改運動不僅要完成土地的再分配,還承載著改造社會的功能,尤其是對知識分子的改造,所以,文學必須展現出知識分子的“改頭換面”,以此迎合主流的改造話語。毫無疑問,衡量知識分子轉變的標準是唯一的,那就是看他們是否能融入群眾,能否與工農群眾的思想行為保持一致,“革命的,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青年之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實行同工農民眾相結合”。文采和肖一智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被否定的,而土改文學更多地則表達出知識分子改造成功的大趨勢。陳學昭《土地》中的土改工作隊員李明是個大學生,他身上顯然有著文采的影子。然而,李明與文采不一樣的地方在于,他對自我的改造有著主動性,“他自己參加土改,也是渴望在這一偉大的群眾運動中得到思想改造”。改革掉舊有的生產關系容易,但“改造”好人的思想顯然沒那么簡單,而決定能夠改造成功的,首先是知識分子是否有自我否定的主動與自覺。在這一點上,李明顯然比文采、肖一智更有“優勢”,這也預示了李明的改造必然會取得預期目標,他“的確已經沉在這個村子里了,他已經變成了這個村子里的一分子”。知識分子被肯定的轉變,是以放棄自己的思想意識,而迎合農民的價值判斷為代價的,只有李明完全按照農民的喜怒愛憎去思考問題,他的改造結果才是合格的。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中共對知識分子的改造,就是使知識分子與大眾達到最大限度的趨同。那些沒有“改造”好的知識分子,就是自始至終都沒能與人民群眾“打成一片”。
土改文學對知識分子的展現經歷由單一到豐富的發展過程,如果說《太陽照在桑干河上》《暴風驟雨》《土地》等小說中的知識分子還是作為單一個體出現的話,那么陸地的《美麗的南方》則是對知識分子的整體性展現。《太陽照在桑干河上》等小說,對知識分子批判與改造的敘述相對來說并不多,他們還只是書寫土改的附屬闡釋,而不是作品的主題。然而,在《美麗的南方》中,對知識分子的表達成為與土改并置的另外一個主題——檢驗并改造知識分子與土地的重新分配一樣重要。陸地1955年開始創作《美麗的南方》,1959年完成,在此期間,中國共產黨對知識分子不但延續了“改造”政策,而且1957年的“反右”運動更是將知識分子作為首要的批判對象。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土改文學涉及的知識分子改造敘事必然要更鮮明,以迎合主流意識形態,這也應該是作家在文本中突出知識分子的直接動因。陸地在小說的后記中談及寫作動機,除了表達土改、農民翻身的主題以外,“也想讓讀者看到,在這新舊交替的時代,一部分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怎樣通過與工農群眾的同甘共苦,通過斗爭和勞動的實踐而得到了真理的啟示,終于修正了原來的階級偏見,精神上獲得了新生”。顯然,作家有意識地把知識分子的改造作為小說的主題,而非僅僅是土改文學敘事的衍生品。
在《美麗的南方》創作時,土改已經結束有幾年的時間了,如果僅僅敘述土改的組織發動及其給農村帶來的變化,那么這部小說也只能是對《太陽照在桑干河上》《暴風驟雨》等作品的簡單重復,沒有太大的價值。如何能超越丁玲、周立波等人的土改書寫,同時使小說具備新的時代意義,這是陸地在創作之初首要考慮的,所以《美麗的南方》塑造的眾多知識分子以及他們不同道路的選擇,都是作家創作動機的最直接體現。而且相對于知識分子形象表述,土改反而變成小說的次要主題,甚至僅僅只是背景。雖然對于土改主題的這種處理并非陸地本意,但過于關注知識分子問題使他很難再突出土改。不過,《美麗的南方》體現出來的土改對知識分子的改造效果,卻與作者創作的意圖相左,也就是說,在這個敘事中土改并沒有對知識分子產生整體性的改造效果。小說中除了像錢江冷這樣通過土改實現成功改造的形象之外,其他知識分子受到土改的影響微乎其微。楊眉、徐圖、俞任遠等人的思想行為,在土改前后基本毫無變化,而杜為人、傅全昭等人在參加土改之前就已經克服掉了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毛病,土改對他們同樣沒有影響。從這個角度來看,文本效果與作者寫作意圖之間是分裂的,知識分子在個體受土改影響程度以及群體的改造效果上,都是值得懷疑的。
四、人道主義、個人化思考與批判精神
20世紀80年代以來,土改文學敘事逐漸擺脫先在的政治規定性,知識分子也從“不干凈”的認定中解脫出來,價值得到重新估量與認定。作家與文學中的知識分子形象得到雙重的解放,被主流話語壓抑近四十年的知識分子群體,不再是批判的靶子、需要改造的對象了。
參加土改運動的知識分子基本都是鄉村的外來者,他們的思想意識、價值理念與農民差異甚大,更為根本的是,他們與農民的利益取向并不一致。外來的知識分子,既是響應號召參加并領導土地改革,也是要在這場運動中接近大眾以改造自己。雖然他們肩負著解放農民、解放農村生產力的職責,但土改對于他們來說,并不能帶來直接利益。所以,在這場運動中,即使知識分子最大限度地按照政治要求接近群眾,他們也不可能完全站在農民的立場上去思考問題,也就是說,知識分子最主要的角色是土改的旁觀者,他們比身處運動中的農民多了一份清醒。同時,在知識分子的思想意識中,人道主義觀念是根深蒂固的,雖然身處階級斗爭中,但他們往往還是以人道主義來衡量人事,也更習慣從是否符合人的價值尊嚴的角度來看待問題。知識分子被要求在土改中改造自我,消除自身不適合革命要求的特性,達到與工農群眾言行的趨同;同時知識分子也希冀通過土改實現自我更新,以便徹底地融入大眾。然而,僅僅靠一場運動來實現思想的改造是不太現實的,新時期的土改文學正是從此人手,試圖還原土改運動中知識分子的精神心理。
在新時期以來的土改小說中,知識分子不是以一個批判符號與改造對象出現的,而是既擺脫了政治束縛的作家,也打開了文本的知識分子身上的鐐銬。土改文學不再批判否定知識分子脫離群眾、貪圖享受、錯誤不斷等諸多弱點,而是將他們身上知識分子的獨特性表達出來。在20世紀80年代以來表述知識分子的作品中,尤鳳偉的《諾言》、胡正的《重陽風雨》是比較有代表性的文本,這兩篇小說展現了與20世紀四五十年代截然不同的知識分子形象。如果說知識分子改造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后土改文學的一個主題,那么主流的改造與知識分子的拒絕改造,則是新時期土改文本顛覆性表述的基本內容。《重陽風雨》中的青年知識分子何舒瑩,在土改的過程中因為同情地主,而被認定為階級不純潔并被清理出革命隊伍。對于何舒瑩來說,她在土改當中所犯的錯誤,只不過是沒有無條件地認同主流的價值判斷,堅持了自己獨立的立場觀點。何舒瑩認為對地主牛佑良的斗爭,“太不講政策了,太沒有人性了,太不人道了”,因為“他們不但讓牛佑良的兒子和父親劃清界限,還給牛佑良用鐵絲穿上鼻子,讓他兒子拉上游街”。這個依然從人道主義來審視階級斗爭的知識分子,必然會被土改領者認為是同情異己階級,而這種跨越階級鴻溝的同情,顯然不利于迅速而“徹底”地推進土地革命。何舒瑩被排除在革命集體之外,正是因為她的思想觀念與土改現實之間的沖突,無法被改造的人道主義立場與殘酷的階級斗爭水火難容。何舒瑩拒絕了改造,集體拒絕了她,一個逃離家庭追尋理想的青年人,恰恰被她向往的革命否定掉了。知識分子話語與革命話語之間的沖突,正是中共倡導知識分子改造的出發點,我們從何舒瑩對斗爭地主的非議中看到,這種改造要求的合理性與必要性。通過土改對何舒瑩的改造教育失敗的書寫,作家顛覆了土改文學關于知識分子改造的既定敘事。同樣面對土改,農民為了土地等現實利益,在宣傳鼓動下完全可以放棄自己固有的價值立場,轉而攻擊自己的鄉鄰。但知識分子一方面沒有現實利益的誘惑;另一方面,他們的教育經歷使他們很難放棄所認同的諸如人道主義等價值觀念。何舒瑩的悲劇遭遇,不過是整個時代知識分子命運道路的縮影而已,更多的人選擇了隱藏自我真實感觸而順應政治要求。
丁玲在《太陽照在在桑干河上》深刻批判了文采身上種種知識分子的小資產階級特性,然而,直到最后,文采也并未擺脫自身局限而成為真正的戰士,土改對他的改造無疑是失敗的。我們不否認《太陽照在桑干河上》是一部偉大的作品,但是,丁玲對對文采過于符號化的處理卻傷及了小說的藝術性。正如劉增杰所說:“嚴格地說,作者對文采的把握卻不能說是分寸適宜的。在特定的時代氛圍中,政治上對知識分子弱點的過分責備,有可能使作家在描寫知識分子時過于拘謹,以致連丁玲這樣的現實主義作家,在塑造文采形象時也不免有夸大缺點、失去了分寸的現象。”新時期作家無須演繹某種理念,知識分子不再是主流批判的對象,體現在土改文學敘事中,知識分子從符號轉而成為有血有肉的人,在土改中有著個體判斷、個性化行為與超越性的思考。在《諾言》中,土改工作隊長易遠方是知識分子出身,他沒有按照主流的要求去用階級理論來發動組織農民群眾,只是以自己的眼光來打量著村莊,看待地主與農民之間的關系。易遠方沒有像蕭祥那樣去深入群眾發動群眾,也沒有像文采那樣想接近群眾而不得其法,他確確實實做了一個鄉村的外來者,始終都沒有把自己與群眾、與土改運動結合到一起。
易遠方身上有兩方面的特征體現得尤為明顯:一是人道主義觀念,二是個人化言行。這既是主流極力否定的東西,也是知識分子改造的重點。如果按照階級斗爭理論來看,易遠方與地主女兒李朵之間無疑是敵對的,屬于兩個階級陣營。然而,易遠方對李朵有著深刻的同情和憐憫,在后者遭難時,他毅然出手相救,他甚至想放走還鄉團來完成自己對李朵的承諾。同時,易遠方始終以個人化的眼光來看待土改中的鄉村,在人事紛紜的背后有著他冷靜的思考。面對混進革命隊伍的流氓地痞李恩寬,易遠方對他的批評更多是出于自己的超越性思考:“你是個品行惡劣的家伙,你把革命和邪惡連在一起,你在打擊壞人的時候自己也在變成壞人。”李恩寬這樣的“積極分子”正是土改工作隊用以打開鄉村保守局面、推進斗爭進程的人,雖然李恩寬們會假土改以謀私利報私仇,但是作為支持窮人鬧革命的土改工作隊,一般會對他們采取寬容態度。從這個角度來看,易遠方對李恩寬的批評顯得不合時宜,并不符合土改組織與發動的工作需要,而李恩寬的問題起碼要等到土改復查的時候才可能被提及、處理。
馮亦代在《靖西鄉土改雜憶》一文中談到自己在土改過程中的復雜情感,“憑良心講,這種仇視是暫時的,每逢斗地主看到他們可憐巴巴的樣子,我的心便軟下來了。我討厭自己的‘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的人性論在作祟。可我無法左右自己的這種情緒”。楊沫在土改日記中也記載了她對被斗爭地主的同情心理,“平時,我也恨陳家,但是當看到他們忽然沒有家了,那么破落了,我競有點不忍心似的不安起來。我經常提到,這是我階級立場不夠堅定,無原則的憐憫心太強,對階級敵人不夠狠之故。我不知為什么總是這么心軟……一看吊打地主更加不敢看。這是一種怎樣軟弱的思想感情啊!”按照階級斗爭理論,對地主決不能有半點同情,這也是知識分子改造的指向,即站穩階級立場,然而知識分子身上的人道主義觀念,使他們對地主的遭遇必然產生深刻的同情。由此來說,易遠方這個知識分子形象是真實可信的。易遠方也以個人化的思考來追問土改運動的合理性問題。貧農主席申富貴原本富有,按照階級劃分的標準可以定為富農,但他在土改之前卻破產了,這使他由富轉貧,本應是階級敵人卻成為貧農主席。易遠方對申富貴的財富與身份前后的變化很迷惘:“該如何看待申富貴幾乎是一夜之間的興衰與階級更遷?財產與人的本性究竟是怎樣的關系?”這樣的思考與疑惑,本身就是知識分子未曾被改造的明證。
在易遠方這樣的人身上,知識分子身份與土改工作隊長身份一直沖突著。在個人言行與集體話語之間以及人道主義與殘酷斗爭之間,易遠方更多地偏向前者,對于工作隊長這個身份,他一直是游離的。我們要看到,易遠方對于土改工作隊長身份的選擇是被迫的,他更愿意按照知識分子的價值理念來處理問題,但顯然這并不被允許。雖然他同情李朵,并且想履行承諾,但土改工作隊長身份卻并不允許他這么做,最終他還是帶領人消滅了還鄉團。參加土改的知識分子,要經歷自身價值觀與現實之間的沖突,“知識分子在奔赴革命時,一方面是真誠急切地希望為人民為國家尋求出路,懷著火一般熾熱的情感與信念,另一方面則必須放棄文化教養培育起來的敏感個性與各種價值標準。在兩者的沖突中,自然引起深深痛苦的靈魂激蕩”。成千上萬篇認同土改的表態文章背后,隱藏著無法被壓抑的獨立判斷和理性思考。相對于20世紀四五十年代作家放棄自己思考絕對服從并按主流要求建構土改來說,新時期作家則在表達著對土改的反思與質疑。易遠方有悖政治功用的言行與個性化思考,典型地體現了新時期文學對既往土改文學敘事的解構、顛覆與追問。
[責任編輯 吳井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