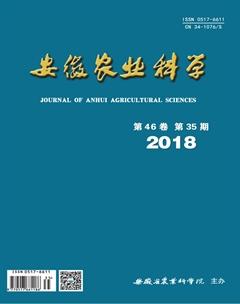京津冀玉米比較優勢時空分布特征研究
陳琪 楊再潔 李奇峰 刁興良 于景鑫 張馨 鄭文剛 史磊剛
摘要?基于京津冀184個縣的玉米面積和產量數據,利用綜合比較優勢指數法和空間聚類分析法測算和分析京津冀玉米種植綜合優勢及時空分布特征,結果表明:京津冀玉米種植規模處于大(>1×104 hm2)、中(0.1~1×104 hm2)和小(<1×103 hm2)水平的縣占總體比例分別約為70%、20%和10%,規模優勢區分布在中南部;京津冀玉米單產處于高產(>6 750 kg/hm2)、中高產(5 250~6 750 kg/hm2)、中產(3 750~5 250 kg/hm2)和低產(<3 750 kg/hm2)水平的縣占總體的比例分別約為30%、40%、20%和10%,效率優勢區集中在環京津中東部地區;綜合比較優勢指數在大于1.5、1~1.5和小于1的縣區數量分別占比約為15%、30%和55%,綜合優勢區分布于北京以南,太行山以東。近10年,玉米大型種植規模區縣的數量增加了約6%,中等規模區縣區數量基本不變,小規模區縣的數量減少了約5%;玉米單產呈波動上升趨勢,相對于2005年,2015年高產水平縣區的數量增加了12.92%,而低產區縣的數量下降了1.34%;玉米綜合優勢的主要優勢和劣勢區沒有發生顯著變化。
關鍵詞?京津冀;玉米;比較優勢;空間分布
中圖分類號?S513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0517-6611(2018)35-0004-05
農作物時空比較優勢是種植結構調整的基礎,明確京津冀各個區縣糧食作物的比較優勢是落實《京津冀協同發展規劃綱要》和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體現[1]。京津冀地區是我國重要的農產品基地和保障我國糧食安全的重要區域之一。在糧食生產方面,京津地區有技術優勢但是糧食不能自給,而河北糧食生產技術落后但糧食人均占有量遠遠超過人均消費[2]。在京津冀協同發展作為國家重要的發展戰略背景下,通過分析京津冀地區各區縣比較優勢并進行比較,明確玉米種植優劣勢區域,有針對性地進行種植結構調整,實現京津冀玉米種植結構優化,對京津冀糧食生產協同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關于玉米種植優勢的研究尺度多為省域或全國層面[1-5],以京津冀作為整體研究對象,系統分析玉米種植比較優勢的研究較為缺乏。馮雪芹[2]通過對河北省主要農作物生產現狀描述,運用綜合比較優勢指數法,對全省糧食作物和經濟作物的種植比較優勢進行實證分析;羅善軍等[3]在國內外現有研究的基礎上,運用綜合比較優勢指數分析的方法,從效率優勢、規模優勢和綜合優勢3個方面對我國各主產省份的馬鈴薯進行生產優勢差異分析;于麗艷等[4]利用灰色系統評估方法,基于比較優勢理論,對我國20多個玉米主產區生產的比較優勢進行測算,分析不同省份比較優勢的形成原因。
該研究將京津冀作為一個整體,基于近10年的縣域玉米產量和面積,利用綜合優勢比較法和時空分析方法,研究京津冀各縣區玉米種植業的生產優勢與不足,進一步明確玉米種植規模、單產和綜合優劣勢敏感區域,以期優化京津冀玉米生產布局、建立京津冀農業生產力與資源環境承載力相匹配的農業發展新格局[5]。
1?數據來源與研究方法
1.1?數據來源
選取的數據均來自于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統計年鑒。由于部分地區缺失相應數據,故該研究將其列為無數據區。通過改進傳統綜合比較優勢指數算法,對京津冀的玉米種植進行優勢區域劃分及分析,同時利用ArcGIS軟件將玉米種植各項優勢指數變化在地圖上進行空間表達。
1.2?研究方法
區域玉米種植的比較優勢受很多因素的影響[6],比如自然條件、政府政策、市場區位等。傳統的綜合比較優勢指數法是一種較理想的比較優勢測算方法,該指數具備一定的可擴展性,可相對科學、客觀地反應區域某農作物在自然資源稟賦、區位條件、科學技術以及市場需求等因素對區域農作物比較優勢的影響[7]。該方法已經被國內研究者廣泛應用于各地農產品的比較優勢研究[8-10],該研究根據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統計年鑒數據,對傳統的綜合比較優勢指數算法進行改進,通過相對值來表達區域某農作物的優勢指數。在計算過程中,避免因農作物熟制問題造成農作物播種總面積發生顯著變化,從而提高結果的可比性。具體計算方法如下:
1.2.1?規模優勢指數(SAI)。
規模優勢指數反映一個地區某一作物生產的規模和專業化程度,它是市場需求、資源稟賦、種植制度等因素相互作用的結果。計算公式如下:
1.2.2?效率優勢指數(EAI)。
效率優勢指數反映作物的效率比較優勢,體現該地區自然條件、技術水平、物質投入等綜合因素條件下某種糧食作物生產能力[11],其計算公式如下:
1.2.3?綜合優勢指數(AAI)。
綜合優勢指數是效率優勢指數與規模優勢指數的綜合結果,能夠較為全面地反映一個地區某種作物生產的優勢[12],其計算公式如下:
2?結果與分析
玉米生產區域比較優勢是各區域生產自然稟賦、種植制度、社會經濟條件、要素投入情況、國家政策支持及市場需求等多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13]。選取體現綜合因素作用結果的玉米單產、播種面積作為測定中國玉米生產比較優勢的關鍵因子,在比較優勢評價指標的基礎上構建玉米生產規模優勢指數、玉米生產效率優勢指數和玉米生產綜合優勢指數,并測算京津冀各區縣玉米種植各項比較優勢指數值。
2.1?規模比較優勢指數
針對京津冀各縣區玉米種植面積進行分類,對各分類縣區數量統計計算,京津冀玉米種植規模在京津冀玉米種植大規模區、中等規模區、小規模區的縣區數量分別約占70%、20%和10%,在2005—2015年,大規模區的縣區數量上升了6.35%,小規模區的縣區數量下降了5.07%。中間水平的縣區數量略有波動,上下波動范圍小于4%,幾乎沒有變化。由此可以得出京津冀的玉米種植規模在此10年間呈持續增長趨勢。
由上述公式計算京津冀各區縣規模比較優勢,通過ArcGIS軟件作2005、2010、2015年各年及3年匯總規模優勢分級圖,并進行比較。
在空間分布上,規模優勢較大的區域主要集中于河北省中東部地區和北部部分地區,劣勢較大的區域主要集中于河北省西北部地區。較2005年,2015年京津冀北部地區優勢區有所增加,中南部地區優勢度有所下降,中東部和南部規模優勢指數大于1.5的縣區數量有所減少。
10年間,北京市的玉米種植面積下降了49.4%,天津市下降了7.3%,河北省上升了3.9%;河北省的玉米種植面積始終遠大于北京和天津,面積差大于200萬hm2,河北省的種植面積10年呈持續增長趨勢,2010年北京和天津種植面積最高,2015年種植面積降至低于2005年。
分析其原因,一方面,具有規模優勢的地區主要分布在各市區的郊區或下屬縣區,市中心建筑較為密集,很難具有規模優勢,另一方面,京津冀中東部地區相對于西部及南部部分山區縣而言平原較多,土地肥沃[14],所以種植面積較大,且受近幾年政策影響,為響應國家政策,調整種植結構,北京、天津的玉米種植面積均有所下降[15]。
2.2?效率比較優勢指數
針對京津冀各縣區單產進行分類,對各分類縣區數量統計計算,可以看出2005—2015年單產水平高產區縣區數量上升了12.92%,中高產區下降了7.77%,中產區的縣區數量2010年最低,占比13.02%,相比2005年下降了8.45%,2015年較2005年上升了0.27%,低產區的縣區數量上升了1.34%,幾乎無變動。
通過計算京津冀各區縣效率比較優勢指數,通過ArcGIS軟件作2005、2010、2015年各年及3年匯總效率優勢分級圖,并進行比較。
2005年和2015年具有效率優勢且效率優勢指數大于1.5的地區多集中在河北省中部及東北部、北京和天津等地區,劣勢地區主要分布于京津冀西部及北部地區,2010年指數較2005年及2015年優勢表現為整體偏低;由效率優勢變化GIS圖可以看出,具有效率優勢的地區主要分布于河北省中部、南部和東北部部分地區,劣勢區主要分布于西部和西北部地區,北京、天津及周邊地區處于波動區。
2005年和2010年單位面積產量排序為天津>河北>北京,在2015年排序為北京>河北>天津;10年間北京的單產水平上升了19.7%,生產效率發展速度較快,天津在2005和2010年單產水平均屬于中高產水平,但2015年驟降至4 998.44 kg/hm2,較2005年下降了20.35%,由京津冀產量最高降為最低,河北省在2010年產量達到了6 468.20 kg/hm2,較2005年上升了10.71%,但在2015年又降回5 902.43 kg/hm2,較2005年上升了1.03%,河北省單產水平在2010年有所提升,但2015年較2005年沒有顯著變化。
分析其主要原因,首先在技術指導上,北京和天津有玉米崗位專家、綜合試驗站和田間學校,在玉米生產產業鏈的育種、栽培、植保、機械、生產技術等全方位的技術指導,但河北并沒有像北京這樣的生產技術科學化指導,生產技術相對落后,在地理地形方面,河北北部地形以山區為主,機械大規模作業比較困難,因此河北難以實現規模化生產的增產增收[16];其次在人才資源上,河北省人口眾多,勞動力資源豐富,但人才資源相對較少,而京津地區整體發展水平高,具有人才優勢。北京、天津的區位優勢、資源優勢吸引了大量高素質的農業人才,這種“虹吸效應”使得河北省缺乏高端的農業科技人才,所以具有效率比較優勢的地區主要集中在北京、天津及周邊部分地區[14-16]。
2.3?綜合比較優勢指數
通過計算京津冀不同綜合比較優勢指數縣區數量所占百分比,綜合比較優勢指數大于1.5的縣區數量在2010年最高,占比29.69%,2005年和2015年所占比例分別為6.28%和7.61%,相差1.33百分點,差異較小,綜合優勢指數在1.0~1.5的縣區數量2010年最低,占比15.10%,2005年和2015年分別占比38.22%和36.41%,相差1.81百分點,變動不大;綜合比較優勢指數小于1.0的縣區數量分別占比55.50%、55.21%和55.98%,基本無變動。
由上述公式計算京津冀各區縣綜合比較優勢,并通過ArcGIS軟件作2005、2010、2015年各年及3年匯總綜合優勢及分級圖,并進行比較。
在空間分布上,綜合優勢區主要集中在北京以南、太行山東部地區以及河北省北部部分地區,劣勢區主要集中于京津冀西北部,指數大于1.5的優勢區分布較為分散且數量較少,但較為穩定,指數在1.0~1.5的優勢區分布較多,北部地區在2010年優勢區數量有所下降,指數小于1.0的劣勢區10年間變化不大。
河北省中東部地區與北京市、天津市相比地勢較為平緩,平原較多,建筑物密集度相對較低,且土地肥沃,更具有規模優勢,另中東部地區距離北京、天津較近,科技、人才、機械化發展水平受北京、天津滲透,水平相對較高,規模比較優勢與效率比較優勢兼備[15-16],且近幾年國家對京津冀地區的農業發展政策傾斜較多,所以具有綜合比較優勢,且優勢穩定的區域主要集中于北京以南、太行山以東地區。
3?討論
基于近10年京津冀玉米面積和產量數據,利用改進后的作物綜合比較優勢方法,評價京津冀玉米種植規模、單產及綜合優勢的敏感區域,研究結果與姜修勝[5]利用數據包絡分析法測算的京津冀玉米生產技術效率結果趨勢一致,北京和天津的玉米生產效率大于河北省。前人多利用傳統的作物綜合優勢指數法,評價四川、遼寧和陜西等某個省域的主要糧食作物的比較優勢[17-20],一般需要全國、省和縣三級數據,由于區域跨度較大,種植規模和單產波動區間增加,空間上比較優勢規律性會有所減弱,該研究利用改進后的玉米綜合優勢指數法和空間分析法,僅需要縣域玉米種植面積和產量數據,計算過程更加簡潔,測算的玉米優劣區結果突出,空間規律與界線更加精準,能夠有效地指導區縣的種植結構調整。河北省的藁城、鹿泉、欒城和正定等縣玉米種植同時具有規模優勢和效率優勢,這些區縣應該優先保證,重點扶植;北京的朝陽區和海淀區,以及天津的濱海新區和西青區等,玉米種植既不具有效率優勢,也不具備規模優勢,建議減少玉米種植;僅具有效率優勢的區域,可以適當增加規模;僅具有規模優勢的區縣,應該適當減少種植面積,并通過引進先進技術來提高玉米產量。
此外,由于北京特殊的地理位置與行政地位,通過擴大生產規模提高玉米生產技術效率比較困難[15-16],但是北京玉米生產技術要比天津、河北先進,尤其是北京有玉米專家團隊的技術保障支持,使北京玉米生產水平處于全國領先水平[21]。河北雖然幅員遼闊,耕地面積廣闊,但是河北的玉米生產技術相對低下,農民根據自己的生產經驗進行玉米生產。建議用資源節約型技術取代資源消耗型技術,實現由“資源依存”到“科技依存”的轉變[21-22]。通過北京玉米生產結構化改革,減少北京玉米種植面積,實現北京玉米生產技術向天津、河北輸出,玉米生產向更適合規模化生產的天津、河北等優勢產區轉移[20-23]。
針對京津冀各區縣玉米種植進行綜合比較優勢分析,雖有算法上的改進,但關于人文、科技、政策、社會等諸多因素的影響還需深入思考。
參考文獻
[1] 楊慧蓮,王海南,韓旭東,等.我國玉米種植區域比較優勢及空間分布:基于全國18省1996-2015年數據測算[J].農業現代化研究,2017,38(6):921-929.
[2] 馮雪芹.糧食主產區種植業比較優勢及結構調整思考:基于河北省的實證分析[J].河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43(2):103-109.
[3] 羅善軍,何英彬,羅其友,等.中國馬鈴薯生產區域比較優勢及其影響因素分析[J].中國農業資源與區劃,2018,39(5):137-144.
[4] 于麗艷,穆月英.我國玉米生產地區比較優勢研究[J].安徽農業科學,2017,45(28):236-239.
[5] 姜修勝.京津冀玉米生產技術效率比較分析[D].北京:北京農學院,2017.
[6] 李曄,申廣榮.上海市主要糧食作物的比較優勢分析[J].上海交通大學學報(農業科學版),2016,34(1):63-68.
[7] 陳春燕,杜興端,熊鷹,等.綜合比較優勢指數法評估四川茶葉產業的競爭力[J].貴州農業科學,2016,44(2):199-202.
[8] 宋晨,馬新明.河南省三大糧食作物生產比較優勢分析[J].中國農學通報,2011,27(20):141-145.
[9] 陳瑤,蔡廣鵬,韓會慶,等.2001-2013年我國麻類作物生產比較優勢變化分析[J].貴州科學,2018,36(2):32-37.
[10] 雷波,唐江云,向平,等.四川農產品比較優勢綜合分析[J].中國農學通報,2015,31(3):282-290.
[11] 張紹波.基于綜合比較優勢指數法的云南省主要糧食作物生產優勢分析[J].云南農業,2016(11):55-57.
[12] 陳振,曹林納,陳祺琪,等.河南省18市主要糧食作物生產比較優勢分析[J].河南農業大學學報,2013,47(3):351-357.
[13] 肖池偉,劉影,李鵬.近20年江西省水稻生產優勢與時空變化分析[J].農業現代化研究,2015,36(5):727-735.
[14] 楊春河,劉愛秋,白蘭,等.京津冀農業協調發展的歷史沿革[J].天津農業科學,2014,20(8):72-74.
[15] 孫芳,劉明河,劉立波.京津冀農業協同發展區域比較優勢分析[J].中國農業資源與區劃,2015,36(1):63-70.
[16] 王健,解聰,張悅玲.發揮京津冀資源優勢加快現代農業發展[J].天津農業科學,2015,21(10):34-38.
[17] 唐江云,雷波,曹艷,等.四川省主要農產品比較優勢分析[J].南方農業學報,2014,45(8):1507-1513.
[18] 張先葉.遼寧省主要農作物區域比較優勢差異分析[J].廣東農業科學,2013,40(1):216-219.
[19] 李鳳.中國蘋果產業區域比較優勢分析[J].江蘇農業科學,2012,40(6):397-399.
[20] 曲興罡,張應良,伏小明,等.吉林省主要糧食作物比較優勢分析[J].西南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5(5):66-69.
[21] 劉玉,蒙達,周艷兵,等.京津冀地區糧食產量變化及其作物結構分析[J].經濟地理,2014,34(8):125-130.
[22] HOEN A R,OOSTERHAVEN J.On the measurement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J].Annals of regional science,2016,40(3):677-691.
[23] ANDERSON K.Changing comparative advantages in China:Effects on food,feed and fibre markets[M].Paris:OECD,1990:2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