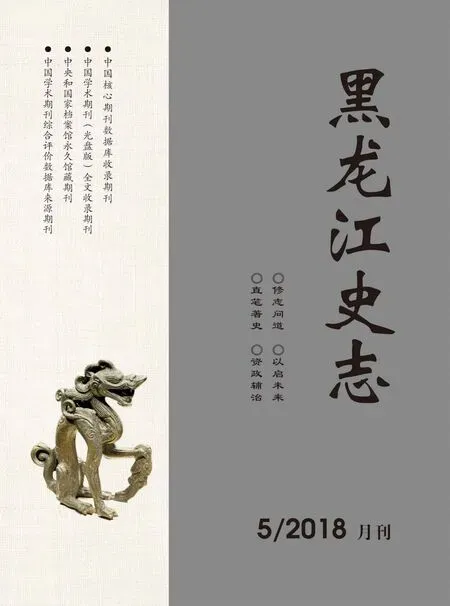近年來全國方志館研究概況及若干思考
潘捷軍
(浙江省地方志辦公室 杭州 310025)
近年來,隨著全國各地對文化事業的高度重視,方志館建設方興未艾。本文擬對近年來全國方志館研究情況作一簡要梳理分析,同時對今后方志館研究和建設管理工作提出相關建議。
一、近年來研究情況梳理分析
據不完全統計,近年來全國方志界公開發表的關于方志館建設的論文近50篇。這些成果的關注重點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1]:
(一)方志館發展史研究
方志館發展史是學界始終關注的一個熱點。以歷史發展為序,主要有楊軍仕的《明代志局(館)淺議》,林璜的《明清〈廣東通志〉的編纂與通志館的演變》,張安東的《清代修志機構的人員設置和資料來源——以清代環巢湖方志為例》,呂志偉的《民國時期上海修志人收集志書資料的方法——以上海市通志館為例》,江貽隆的《劉文典致安徽通志館佚書六則及其價值》等等。
例如楊軍仕的《明代志局(館)淺議》[2]認為:“明代是修志活動比較寬松和活躍的時期,也是修志活動逐步走向規范化、制度化的時期,其中突出表現就是志局(館)這種臨時性修志機構的大量出現。”特別“處于中后期的嘉靖、萬歷兩朝設立志局(館)的數量偏多。”他在分別重點分析了當時“志局(館)運作”和“志局(館)作用”等問題后指出:“設立志局(館)編修志書,也為后世創立了基本的修志模式,即政府主持、學者參與、眾手成志。”同時他還指出了明代志局(館)書成即散的弊端。
林璜的《明清〈廣東通志〉的編纂與通志館的演變》[3]則細致入微地分析了明清時期廣東六次建立通志館的曲折歷程:戴 一己之力的艱辛甘苦,黃佐家族弟子合力而為的眾手成志,郭 注重質量的學者主修模式,金光祖亂世修志的草率從事,郝玉麟注重行政而相對忽視質量的官修模式,直到阮元因天時地利而集大成,作者對由此而產生的方志私修官修、時間長短、人員結構等等各種因素都進行了比較分析,是一篇質量較高且很有見地的力作。
(二)當代方志館功能分析
方志館功能定位等與建館、管館直接相關的現實問題無疑是研究的重點,主要有劉玉宏的《論方志館的性質與功能》,馬小彬的《方志館設施建設立項研究——以省館建設為例》,蔡金良的《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發展過程中的方志館建設》,李志瑜的《北京方志館公共文化供給能力調查報告》,以及侯宏興、黃小晶、杜金華、吳一峻、王慧卿、楊獻 等作者從不同角度所作的情況介紹及相關分析。
例如劉玉宏的《論方志館的性質與功能》[4],文章從方志館建設背景、方志館建設的必要性、方志館的性質與定位、方志館與其他場館的區別和方志館的主要功能等五個方面,作了提綱挈領式的概括,系作者長期從事全國方志館建設領導管理工作的經驗總結,也是全國方志館建設的重要導向。
馬小彬的《方志館設施建設立項研究——以省館建設為例》[5],則以省方志館建設為例,側重于領導與管理視野,對全國已建、在建方志館基本情況進行了系統梳理,從館舍面積、投資規模、可行性研究等各個技術性操作層面進行了分析提示,揭示了其中存在的若干缺陷,對各地建館實踐具有較強的現實借鑒意義。
李志瑜的《北京方志館公共文化供給能力調查報告》(未刊稿)系全國方志館業界最早也是最規范的調查報告之一。作者選擇北京方志館為特定對象,具有典型示范意義。同時以調查報告這種獨特形式,以新穎的問卷、翔實的數據、規范的圖表等多種手段,圍繞方志館“公共文化供給能力”這一主題作了認真細致的調查分析,所取樣本客觀可信,所提對策建議中肯可行,對方志館建設特別是開館后的運行管理具有直接借鑒意義和參考價值。
(三)多學科多視角探索
近年來,方志館這一新型文化形式不僅在方志界,而且已開始引起其他學界的關注。這方面成果較有代表性的主要有劉迪的《公共文化場館陳列的觀眾審美心理探源》,王克松的《論方志館與少數民族非物質文化遺產資料的搜集整理——以水族非物質文化遺產為例》,林子雄的《論方志館的文化根基——以廣東方志館為例》等等。
例如劉迪的《公共文化場館陳列的觀眾審美心理探源》[6]從觀眾的懷舊傾向、陳列空間的陌生化和展示的驚奇性等問題入手,對文化場館陳列的觀眾心理要素、審美心理期待和審美心理過程作了系統闡述,對在建方志館規劃布展很有參考價值。
總之,上述成果或側重于歷史或側重于現實,或側重于宏觀或側重于微觀,或側重于學術或側重于實務,應當說各顯千秋,各具特色。限于篇幅關系,不再一一列舉。另外,筆者還曾以《全國各地的方志館建設與運行管理》為題,在《中國地方志發展報告(2017年)》作過專門分析。[7]但從總體上看,無論是成果的數量還是研究的質量,都還落后于當前各地方志館的建設實踐,亟待強化深化。
二、若干分析和思考建議
基于上述分析,結合筆者近年在廣西南寧、浙江麗水等全國方志館業務培訓班和江蘇、福建、貴州等地方志業務培訓班的講課,以及在浙江湖州、海南省方志館等建館中的指導實踐,主要從研究角度對當前和下一階段工作提幾點思考建議。
2017年5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曾強調指出:“不忘本來、吸收外來、面向未來”,同時這也是去年1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下發的《關于實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的意見》所提的一個重要原則,我認為這同樣也是全國方志館建設的根本遵循。
(一)“不忘本來”就要深化確立方志館的建設理念
如果說不忘“本來”,那么,什么是方志館的“本來”?或者說什么是我們建設方志館的“初心”?一言以敝之:方志,即方志館應以展示和弘揚方志文化為宗旨要義,方志是方志館的“根”和“魂”。
那么這種理念是否可行?能否應驗?此處僅舉一例,曾被中指辦領導稱為全國最好的縣級方志館——于2013年建成開放的杭州余杭方志館,其主要設計者的理念是:既然稱之為“方志館”,那么其所展示的一切都應以志書為主題主線,即“史”須源自“志”,“展”須圍繞“志”,言必有“志”,并力求收放有度,“放”以志書記載的內容為邊限,“收”以方志文化為準繩,凡是志書中沒有記載的一般不予展示。因而該館所展示的區域歷史和綜合地情并非始于歷史發端(盡管區域內有著名的“良渚文化”等歷史遺跡),而是以有志書記載的歷史為發端;同樣,入館人物也非不作選擇地來者不拒,而是必須有相應的歷史典籍著作為依據,即志書中未記載的傳說等人物概不入館。
其實這種理念在學界早有淵源。如朱希祖先生早就明確指出:“有文字而后有史”。他在《中國史學之起源》中闡明:“司馬遷作《史記》,《本紀》起于黃帝。而其《貨殖傳》又云:‘夫神農以前,吾不知已。’ 亦以有文字而后有史,故起黃帝。神農以前為結繩之世,故謂不可知。”[8]當代知名學者嚴建強也認為:志書是文字形成以后的產品,有文字以前的歷史可以進入博物館(如神話、傳說等),但一般不能進入志書,同樣也不能進入方志館,這也是方志館一個重要的范域界定。因此,“方志館”不能離方志太遠,否則就有本末倒置之感。我認為這就是我們方志事業的“本來”,也是我們建設方志館的“初心”,更是方志館的根基和靈魂。只有不忘“本來”,恪守理念,才能實現“初心”。
(二)“吸收外來”就要妥善處理方志館的關系定位
一方面,方志館如何在當今各類文化場館格局中獨樹一幟?這首先涉及到建館必要性的問題。實際上各地在方志館立項規劃等前期工作中,都會遇到不少政府主管部門從資源合理配置、注重提高效益等方面所提出的置疑。這方面,筆者在《中國方志館》一書中已作了充分對比分析,特別山東省地方志系統堅持推進“三全目標”的實踐可供全國方志系統借鑒,同樣英國倫敦在全國普及各類博物館的經驗也可給我們以啟迪。
倫敦目前約有200多家各種類型的博物館,系世界擁有博物館最多的城市。當初針對反對布局過多、要求資源共享等不同聲音,政府堅持按城市居民人口數量布局建設各類博物館。據悉其規劃建設理念是:各種類型的博物館是小眾產品,未必人見人愛,也不必都去追求經濟效益和轟動效益。但公眾是由不同知識水平、不同文化需求構成的,因此政府就要善于通過建設不同類型的博物館滿足人們不同的需求,特別要讓少年兒童從小通過耳濡目染而潛移默化,以培養其不同的興趣情感,從而達到逐步提高其素質水平并造就不同專業人才的目的。
黨的十九大報告強調指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這是基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所作出的新的科學判斷。筆者體會:與以前“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與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相比,“社會生產”相對偏重物質,而“美好生活”顯然兩者并重,或者說更注重文化,更有文化蘊味,“美好”的要求也更高。因此,“美好生活需要”顯然既包括物質生活,同樣也包括精神生活。而且從目前恩格爾系數在全國變化情況看,更應注重精神生活。因此,這個“不平衡”“不充分”既有類型形式的廣度,也有內容的深度和創新方式的新意。特別當全國各地(尤其是一些沿海發達地區)經濟社會總體水平達到今天這樣的高度時,黨委政府更應該有這樣的意識,這一點倫敦的經驗足以引發我們思考。因此,中華民族精彩紛呈的方志文化顯然是“美好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在緩解“不平衡不充分”矛盾方面,各地方志館應大有可為,也完全可以大有作為。當然,在建設過程中確要注意資源共享、合理配置,力求提高效率水平,這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此處暫不贅述。
另一方面,方志館“綜合地情館”的定位不能動搖(注:綜合地情館的來歷在《中國方志館》中也有詳細記述分析)。需要指出的是,“方志館”不等于“志書館”,強調方志館以方志文化為本與建設綜合地情館并不矛盾。因為國務院《地方志工作條例》規定得非常清楚:方志應當全面、客觀、系統地記述一地自然、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的歷史與現狀,這其實就是“綜合地情”。既然如此,以再創作的方式,全面客觀系統地展示志書所記載的綜合地情,當然是方志工作題中的應有之義。
還要看到,在計算機等現代傳播手段出現以前,傳統場館主要用于存放紙質文獻,不可能出現當代意義上的方志館。但這并不意味著“方志館”就簡單等同于單一的紙質志書館。在人類已進入21世紀的今天,“志”(記錄、記載)的手段事實上已不限于單一的紙質形式,我們完全可用各種現代化手段“志”人、“志”事、“志”物。因此,我們應當以這種與時俱進的思維來認識和建設當代意義的方志館,力求實現王偉光同志提出的“從紙質平面到立體呈現”的要求。
而且恰恰正是由于這種定位,我們才能在場館林立的當代文化事業發展大格局中獨樹一幟。如與博物館相比,展示“歷史”顯然是其獨特優勢,但展示“現狀”(如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的建設發展成就)卻是目前全國各地展館行業所普遍忽視的一個問題。為此我曾與某地文博部門的領導探討過此問題,他的回答是:因展館面積等條件所限,文博界現有文物都無法充分向外界展示,更無精力關注現當代事物。當然,從深層次看,文博界還普遍存有一種“厚‘古’薄‘今’”的潛意識。同樣,以珍藏孤本、善本等為重點和優勢的圖書館、檔案館等場所也不同程度有此傾向,我以為這恰恰為我們方志界騰出了發展空間,也是方志館的優勢所在。而且對大多數觀眾來說,恰如劉迪在《公共文化場館陳列的觀眾審美心理探源》所分析的那樣,越是遙遠的歷史他們會越感陌生,往往敬而遠之,而對自身親歷的歷史卻越具有特殊親近感。這也是綜合地情館獨特的優勢所在。在這方面,沈陽中國工業博物館,北京、廣州等地的方志館都有很值得借鑒的成功經驗。特別今年恰逢改革開放40周年,明年將喜逢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按方志“詳今明古”原則,我們有很多工作要做。
因此,在方志館建設過程中,我們既不能妄自尊大,要注意“吸收外來”;同樣也不能妄自菲薄,要有我們方志人自身特有的自信與定力,正如中辦、國辦《實施意見》中所明確指出的那樣:“以我為主、為我所用,取長補短、擇善而從,既不簡單拿來,也不盲目排外”。要通過精心策劃、精準發力來建設好方志館。
(三)“面向未來”就要與時俱進拓展方志館發展前景
首先,“面向未來”就必須與時俱進。方志館不但是一種新生事物,同時還具有展館業“一次性消費”的特點,即除專業人士外,觀眾大多不會作多次選擇。因而良好的開端只是成功的一半,我們要按照黨的十九大“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要求,以創新意識使方志館建設“永遠在路上”。相反,如果開館后滿足于坐井觀天、孤芳自賞,可能很快就會落入“門前冷落鞍馬稀”的尷尬境地。因而要十分關注開館后的良性運行機制和綜合效益問題。例如,要像北京館那樣,力求預留空間作為臨時展廳,以常開常新方式對觀眾始終保持一種新穎的吸引力,使方志館始終保持旺盛活力和持久的生命力。
其次,“面向未來”就不能僅停留于現有形式甚至滿足于傳統手段,而要充分借鑒運用現代化手段,不斷延伸展示鏈,不斷創新辦館的技術手段。如常州方志館、浙江舟山市網上“虛擬方志館”、新建廣州方志館等都是典型實例。
最后,“面向未來”還必須拓寬視野,拓展領域。例如,中宣部和國家廣電新聞出版總局已于2015年發文(“新廣出辦發〔2015〕45號”)指出:“地方史編寫與地方志工作密切相關”“具備條件的,可將地方史編寫納入地方志工作范疇,統一規范管理。”這對我們又是一次千載難逢的發展機遇,同樣也會大大拓展方志館的建設空間和展示舞臺。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為此建議已建方志館應抓住機遇注重轉型升級;在建或新建方志館應未雨綢繆與時俱進,通過重新審視調整方案,讓史志有機結合,使方志館在中華民族文化傳承傳播過程中發揮更為重要的作用,為文化強國建設作出更為重要的貢獻。
注釋:
[1]主要系對《中國地方志》雜志、《中國方志館研究(第一輯)》、《首屆全國方志館館長論壇材料匯編》等資料所作的統計統計。本文“近年來”系指對筆者主持的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中國方志館研究》結題及《中國方志館》一書于2016年出版以來的情況梳理。
[2]楊軍仕:《明代志局(館)淺議》,《中國地方志》2015年第4期。
[3]林璜:《明清〈廣東通志〉的編纂與通志館的演變》,《中國方志館研究(第一輯)》,方志出版社2017年版(下同)。
[4]劉玉宏:《論方志館的性質與功能》,《中國地方志》2018年第1期。
[5]馬小彬:《方志館設施建設立項研究——以省館建設為例》,《中國方志館研究(第一輯)》。
[6]劉迪:《公共文化場館陳列的觀眾審美心理探源》,《中國方志館研究(第一輯)》。
[7]潘捷軍、呂克軍:《全國各地的方志館建設與運行管理》,《中國地方志發展報告(2017年)》,方志出版社2017年11月版。
[8]朱希祖:《中國史學之起源》,《朱希祖文存》第100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