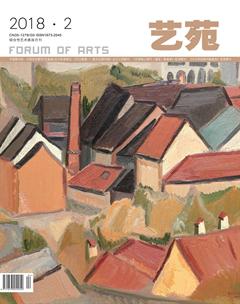閩江長流水 武夷不老松
葉黃晨

【摘要】 第八屆“京·滬·閩當代音樂創作研討會”于2017年12月8日至11日在福建師范大學音樂學院隆重召開,各地作曲家和音樂理論家集聚一堂,對近年來各自新近創作的音樂作品展開深度研討。對福建省作曲界名宿郭祖榮先生的音樂創作進行專題研討是研討會的第一項議題,與會專家、學者圍繞著郭先生對“京·滬·閩”研討會所做的貢獻,郭先生70多年來的音樂創作生涯、創作精神以及他在音樂教育領域所做的無私奉獻等問題展開了熱烈討論。
【關鍵詞】 當代音樂創作;京滬閩;郭祖榮;社會活動家;作品出版
[中圖分類號]J60 [文獻標識碼]A
第八屆“京·滬·閩當代音樂創作研討會”于2017年12月8日至11日在福建師范大學音樂學院隆重召開。來自中央音樂學院、上海音樂學院、中國音樂學院、中央民族大學、人民音樂出版社、中國藝術研究院、中國廣播藝術團、《人民音樂》雜志、中國文聯出版社、日內瓦音樂學院、臺灣輔仁大學、臺灣新竹交通大學、臺灣屏東大學、浙江音樂學院、天津音樂學院、四川音樂學院、福建省音協等單位和機構的作曲家、音樂理論家與福建代表共80余人集聚一堂,對近年來各自新近創作的音樂作品展開深度研討。本屆研討會參會人員在以京、滬、閩三地作曲家為主的基礎上,增加了來自臺灣和其他省市以及美國、加拿大、歐洲、澳洲的作曲家、理論家代表,為會議增添了更濃郁的多地域、國際化色彩。歷屆研討會對當代音樂創作中的美學觀念、作曲技法、形式內容、民族化、時代性等問題的探討,已成為國內作曲界的一個風向標。本屆研討會的第一項議題是對福建省作曲界名宿郭祖榮先生的音樂創作進行專題研討。研討會由高為杰老師主持,他慨嘆郭老真誠執著、鍥而不舍之精神乃是中國作曲家的楷模。短短兩個多小時的研討,與會專家、學者圍繞郭先生對“京·滬·閩”研討會所做的貢獻,郭先生70多年來的音樂創作生涯、創作精神以及他在音樂教育領域所做的無私奉獻等問題展開了熱烈討論,讓我們飽享音樂文化之盛宴。
一、“京·滬·閩當代音樂創作研討會”的發展歷史
研討會上,年近90的郭祖榮老師向我們講述了“京·滬·閩”研討會的發展歷史。1987年正值改革開放伊始階段,從北京吹來了一股新潮音樂風,當時從師大調任到福建省藝術研究所工作了兩年的郭老師認為新音樂沒有絲毫美感,便與章紹同老師商量,規劃召開一個關注當代音樂創作的研討會。經過兩年的籌備,1989年在武夷山召開了第一屆“滬·閩音樂創作筆會”,共有11人參會。與會人員一起聽作品、談創作,三天三夜意猶未盡,深感會風嚴肅、收獲頗豐。之后,章老師因工作調動離開了福建省音樂研究所,郭老認為研討會應該繼續辦下去,于是請自己的學生以及各地的宣傳部、文化局幫忙,于1990年11月7日在福建東山島舉辦了第二屆的“滬閩音樂創作筆會”。郭老說“京·滬·閩”研討會從一開始就跟野孩子一樣,早上在海島上玩,下午、晚上開會。前三屆我們“滬閩”開過,“京閩”也開過,以后便可舉辦“京滬閩”了。于是,在1992年10月第一屆“京·滬·閩”研討會在福建福鼎太姥山舉辦。這一屆研討會學術氛圍非常濃,白天談晚上也談,開著圓桌會議面對面地談。大家一起討論如何幫助福建作曲的提高,定下了“圓桌會議、沒有大小、人人平等”的規矩。此后,又分別于1995年7月31日在廈門鼓浪嶼(第二屆)、1998年10月在福建廈門(第三屆)、2009年7月在福建永安(第四屆)、2011年10月7-9日在福建省連江縣(第五屆)、2013年10月18-20日(第六屆)和2015年12月11-13日(第七屆)在福建師范大學音樂學院舉辦了共七屆研討會。
郭老指出,“京·滬·閩”研討會的逐步發展得到了許多專家、學者的支持與幫助,也得到《人民音樂》的關懷,金湘老師曾建議今后無論有多少作曲家來參會還是稱“京滬閩”。盡管福建有那么多搞交響樂創作的人,但我們不搞“福建樂派”,我們可以稱“福建樂群”。郭老強調我們京滬閩不要“變色”,主要以嚴肅音樂、高雅藝術創作為主,由福建師范大學音樂學院牽頭做。最后,郭老還提出兩個問題:一是到底中國要不要我們自己民族的交響音樂?二是我們自己的交響音樂到底該怎么寫?他希望下一次京滬閩可以集中討論,也希望今后京滬閩就在他的母校福建師范大學一直辦下去,期望北京、上海的作曲家能多幫助福建年輕作曲家提高,也期望青年一代的作曲家盡快茁壯成長,滿懷著一位福建老音樂人的深情厚誼。
二、作曲家與“社會活動家”
研討會上,劉念劬先生代表上海作曲界就“中國作曲家的終極人文關懷”提出了自己的觀點。在他看來,作曲家的人文關懷第一條便是“我們都是為了藝術而被判處了終身服役的人”。他認為“京·滬·閩”研討會這樣高大上的作曲家研討平臺,第一點值得肯定的是“貴在堅持”。他從美國回來后,發現有些對音樂毫無研究的人在不熟悉的領域成為專家,而“京·滬·閩”研討會這個平臺則發揚了北大精神,是一個保護創見與個性的平臺,能誕生真正有獨特民族風格的音樂。他指出中國音樂可以多元的存在百花齊放,小眾藝術、大眾藝術、各種各樣的作品風格都可以存在。同時,他提出作曲家也應該成為社會活動家,我們的作品必須要有聽眾的反應,否則會很寂寞,譬如章紹同、奚其明就是社會活動家。
杜曉十先生用“堅守”兩個字來形容郭老:一是郭老堅守了70多年的音樂創作事業,從剛開始寫完作品卻沒有聲音一直堅守到今天,他的作品越來越被大家認識和認可非常不易;二是郭老一直堅守在福建,研究福建音樂、從中吸取營養,再把福建音樂元素放到作品中,他堅持不受現代音樂、流行音樂的沖擊,但也不固守陳規,不斷加入新元素,這一點值得我們敬仰;三是郭老始終堅守在教育崗位,自己創作、自己帶學生,對學生點點滴滴、言傳身教,如今活躍在音樂屆的吳少雄、劉元、溫德青、宋瑾、王耀華等都是郭先生培養出來的,尤其是譚革勝更是郭老師手把手培育出來的。希望大家能夠把郭先生作為研究的課題,因為他值得研究和推廣。
楊通八先生認為“堅守”是最重要的,堅守的可貴之處在于甘于寂寞、甘于奉獻,如此才能做出精品,而不是要成為音樂社會活動家。他深感今天的會議受到郭老一番話的影響,大家都愿意講真話,對于做精品音樂的人而言,天生就要自甘寂寞,一輩子耕耘,必成正果。無疑,這是一種高尚的精神境界,“京·滬·閩”研討會的舉辦正體現了作曲家的精神境界。
陸培先生表示堅守是因為喜歡,因為有話要表達。作曲家們為自己而寫,有感而發,這就會感染他人,不是堅守可以概括的。“因為熱愛,我寫,我就想寫,我就想這么寫,有沒有演出無所謂。”他認為郭老的作品有一種美,蘊含著郭老所理解的中國音樂,有形式美、內涵美,是由民間得來的感受。他認為作品中有自己的看法才能稱為作曲家,作曲家同時成為社會活動家是為了推廣自己的作品,比如作曲家譚盾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顯然,謙虛是必要的,但如果沒人知道你是誰也不行。高為杰先生認為作曲家有兩種,一種為自己活著,一種為他人活著,郭先生就是為他人活著的活動家,他讓“京·滬·閩研討會”越辦越好,這就是活動家,同時他也得到了大家的認可,讓大家受益。但是,顯然郭先生進行創作的時候是很寂寞的,而這并不矛盾。陸培指出郭先生就是一個大活動家,寫出作品來很寂寞,但一個作曲家,沒有聽眾什么都不是,我們寫作品,聽眾越多越好,才能傳達思想。
三、作曲家、教育家之愛
田剛先生回憶了十年前在杭州師大的一堂課上他聽到郭老師十二音和五聲音階融合的一個作品片段,覺得作品非常棒,而當時任課的李吉提老師認為郭老師不僅作品棒,人品更棒。郭先生寫作品,沒有音樂會,沒有比賽,只為喜歡而寫,他熱愛自己的事業、認真鉆研、辛勤耕耘、鍥而不舍,這是一種精神,不僅需要我們繼承,更是中國作曲家的楷模和榜樣。
郭老的學生鄭長鈴先生整理了郭老的第一本書《音樂的徘徊》,當他整理到郭老小時候立志寫音樂時,他邊寫邊哭,郭老的家國情懷和對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關注深深打動他。會上鄭長鈴提出了自己的困惑:其他藝術門類很容易從國家層面拿到支持來發表自己的感受,作曲界卻很少很難。郭老師的“默默”可能更多是因為社會環境、時代造成,現在是否還這樣值得商榷。作曲家能跟這個時代脫離嗎?完全屏蔽在自己的個人世界嗎?作曲家需要以作品表達感受,期待不久的將來,能把時代的聲音和作曲家內心的表達融合在一起,呈現在大家面前。
賈達群先生指出,他一直在思考所謂的“愛樂人”中又有多少真正熱愛音樂、全身心投入的呢?在他看來,所謂“愛樂人”,首先要很“純粹”,作曲家不能太功利,不能犧牲音樂的品格;其次,作曲家對音樂要有“敬畏”,音樂作品是最豐富的情感和最高智慧的體現,顯然須認真;再次作曲家要“真誠”,所有的藝術都不能虛假,作品應該是藝術家的心聲;最后,作曲家要通過作品來講“文化”,作品要有引領性,文化和精神的引領,產生社會效應。據此看來,通過理解郭老的作品,均能得到以上幾點的解答,郭先生乃是名副其實的“愛樂人”。
梁茂春先生談到在創作方面,郭老從未違約,從未因任務而創作,他勤奮耕耘了幾十年,是所有音樂人的榜樣。他的作品體裁豐富,成果豐碩,最早的鋼琴作品、藝術歌曲為推動中國藝術歌曲的發展做出了貢獻。其次,在音樂教育方面,許多活躍在世界上的音樂家都是郭老的學生,這一點很像臺灣的許常惠老師。第三,對戲曲音樂的貢獻,郭老師幾十年耗在里面,戲曲音樂像血液融化在音樂中,非常值得總結。再者,郭老師在音樂理論方面的建樹也應該研究,他的和聲與普通人不一樣,比傳統和聲豐富得多。
于慶新先生提出,為什么福建的作曲家會有這樣的成就?因為封閉的環境能夠安靜搞創作,帶出了學生,有利有弊。福建之所以在音樂方面有這樣的成就,郭老師功不可沒。在他心目中,朱踐耳、羅忠容、郭祖榮是作曲界的三座豐碑。郭老師在音樂教育方面,確實有奉獻精神,不僅不收學費,還請學生吃飯,這樣的情況在當前社會越來越少。在藝術作品高尚追求,在人品上的高尚品格,沒有郭老師就沒有這個座談會,“京·滬·閩”追求真正的藝術精神,故而成為音樂界一個響亮的品牌,這種優秀的藝術傳統我們須代代相承。
四、作曲家應關注作品出版相關問題
來自臺灣的陳茂萱先生認為臺灣和福建的文化往來不能切斷,他對剛剛出版的郭老師的創作手稿深深打動,很佩服中國政府賣力地保存作曲家的資料,也佩服文聯出版社能做這個事。他感到郭老師的作品突破了絕對音樂的方向,在他的發展部辯證方式有新的改變,要有后輩繼續努力研究和繼承。
來自文聯出版社的曹軍軍編輯分享了他為郭老出版作品的感受,即“熱愛、崇敬、擔當、回歸”。他認為從事與音樂相關的職業需要有更多的人熱愛與懂得作曲,他呼吁青年朋友們學習作曲,但不必拘泥于一定要成為作曲家,但需要很多“活動家”,即有效的傳播者。他結合與郭老師的出版合作,談了幾點感想:一、收集。音樂的創作圈缺乏能夠集腋成裘的平臺,出版人需要有版權意識,作曲家與音樂人共同建立好的版權機制與平臺機制。二、制譜。打譜的校對工作實際上需要很高的音樂修養,郭老提到“用手稿出版的效果最好”,說明出版社這方面做得不盡人意,給作曲家帶來很大的負擔。同時,整個音樂圈在制譜方面也呈現出一種“懂的人不做,做的人不懂”的怪象。三、錄音。郭老師出版的作品中,目前的音像錄音等工作做的很貧弱,數字化傳播的效果也不到位,人才急缺。四、編制。在出版郭老師作品過程中,他曾問郭老師:“好像您的作品編制不大,雙管編制比較多。”郭老師笑道:“那是因為樂團沒有強大的能力能夠演奏大的編制。”這值得我們反思,好的演繹者與集體的匱乏限制了作品的呈現。五、推廣。其實郭老師的許多作品是被歷史耽誤了,比如他于今年在北京上演的一部鋼琴協奏曲,這部作品在創作完成60年后才首演,錯過了推廣的最好時代,這就影響了作品的階段性歷史地位。
最后,研討會經過幾番激烈討論梁茂春老先生講了一段語重心長的話很受鼓舞:郭祖榮老師的作品體現出深刻的人文關懷、悲憫的情懷,他的創作是從大樟溪開始的,就像閩江一樣洶涌奔流、充滿活力,他贊譽郭老似“閩江長流水,武夷不老松”。大家愿景著在郭老師90周年誕辰時,在郭先生的母校福建師范大學再舉辦一次更為大型的研討會,來總結、提煉和傳承郭先生的藝術精神。
結 語
第八屆“京·滬·閩當代音樂創作研討會”的參會人員在以京、滬、閩三地作曲家為主的基礎上,增加了來自臺灣和其他省市以及美國、加拿大、歐洲、澳洲的作曲家、理論家代表,為會議增添了更濃郁的多地域、國際化色彩。對福建省作曲界名宿郭祖榮先生的音樂創作進行專題研討是本屆研討會的第一項議題,會議中對“京·滬·閩當代音樂創作研討會”的發展歷史;作曲家與“社會活動家”;作曲家、教育家之愛;作曲家應關注作品出版相關問題等,展開了深入的討論達成諸多深度交流的看法。郭祖榮先生德藝雙馨似“閩江長流水,武夷不老松”,他的作品體富有深刻的人文關懷、悲憫的思想情懷,他的人品謙虛善仁、育人不倦、虛靜堅守,他的創作思想和教育思想值得我們總結、提煉與傳承,他是福建愛樂人一面光輝不朽的旗幟。歷屆研討會對當代音樂創作中的美學觀念、作曲技法、形式內容、民族化、時代性等問題的探討,已成為國內作曲界的一個風向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