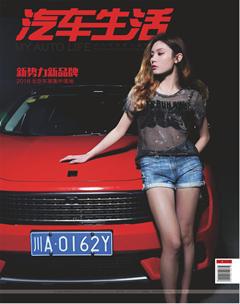歷史廓圓、晝始夜弭:莎士比亞與英國人的文學情結
鄭詩雨
早前求學英倫,曾供職BBC和澎湃新聞等國內外新聞媒體機構,跑過創業投資、公共外交、汽車產經等多條線,現為國家公派博士、外方全獎得主,研究領域為新媒體、受眾參與、全球影視、跨文化傳播、文化政策等,兼有社交運營官、專欄作者、自由撰稿人多重身份。
正如英語是當今世界使用最廣泛的語種,威廉·莎士比亞(Shakespeare William)是英語文學世界最偉大的代表。后世感念其在文學、戲劇領域做出的杰出貢獻以及表達對他的崇高敬意,親切地稱其為莎翁(同時諧音姓氏“威廉”)。今年的4月23日是莎士比亞誕辰454周年,位于英國埃文河畔的莎士比亞故鄉——斯特拉特福德(Stradford upon Avon)迎來了一年中最重要的日子,慶祝莎翁誕辰。而身處英國的我有幸參與其中,更是從多個維度了解莎翁其人和作品。
文學與戲劇的跨界閃耀
說起莎士比亞,大家最先想到的是他作為戲劇家最為人所周知的四大悲劇《哈姆雷特》、《李爾王》、《麥克白》、《奧賽羅》。特別是《哈姆雷特》中的名句,令人耳熟能詳。而很少有人知道,莎士比亞的四大悲劇包孕了深層次的文化母題,分別對應原罪、寬恕、審判和謊言,這些文化母題,恰如其分地反映了當時社會和時代的需求。只要稍加留意,就能發現,在莎翁的戲劇作品中,無不滲透著文化和戲劇的跨界互文、深層內涵。當今英語世界的文學主義,都能在莎翁作品中找到對應的“源頭”。由于時代的特殊性,在莎士比亞之前,英語被視為“低等”、“粗俗”,世界上沒有人能夠用這門語種創作出如此優雅的文字與藝術,英文也為歐洲大陸天主教共同圈的文化人所恥笑。而莎士比亞用通俗的表現形式,融合英文語言藝術的魅力,給了歐洲大陸的文人以一記重擊:原來英國人也可以締造出如此偉大和優美的作品,并不只有所謂“正統”的法語和拉丁語才能寫出高雅的文字。莎士比亞的作品讓英國的文學從此在歐洲大陸挺直腰板,站立起來。時至今日,當提到英國的文學創作,英國人無不追溯并認同莎士比亞作品為英國現代文學之濫觴。我的博導感慨,莎士比亞是英國最偉大的戲劇家、詩人、文學家,沒有之一。
語言與詩歌的遙相輝映
稍加了解莎士比亞作品的人都知道,除了戲劇以外,莎士比亞的十四行詩(英文Sonnet,又譯作“商籟體”)堪稱是英語詩歌中的經典。同樣地,在莎士比亞之前,十四行詩已經蜚聲歐陸,意大利詩人彼特拉克的創作使其臻于完美。而莎士比亞的改良,使商籟體在英語世界得以立足。莎士比亞的創作,使得詩歌節奏抑揚頓挫、音韻獨特起承轉合、詩歌內涵形象生動,在那樣一個特定的環境下,莎士比亞借詩言志,表現了新興階層的情懷和理想。記得我初學英文之時,學校就專門開設了莎士比亞英語的研修課,當時的導師告訴我,想要成為英語大家,讀懂了莎士比亞英文原著,才是真正精通英語的個中高手,而這一點對于母語為英文的學習者都難度極大。因此直到今日,不少大學依然傳承并開設了莎士比亞英文研究的課程,其中就包括了牛津大學、開放大學等頂尖學府,英國國家廣播公司(BBC)更是有一檔專業的英語學習欄目,講述莎士比亞的語言藝術(Shakespeare Speaks)。可以看到,英國人對莎士比亞語言創作的研究熱衷,從未中斷。
精神與思想的長久慰藉
任何徒有形式虛乏內容的創作,都會隨著歷史的淘沙而湮沒無聞。而莎學之所以能成為西方世界唯一一個以作家之名締造的獨立學派,更多的是其背后的精神引領。很多人以《麥克白》中的名句“無論黑夜怎樣悠長,白晝終會到來”作為自己人生的座右銘,或是將《哈姆雷特》中的“生存還是毀滅,這是一個問題”奉為圭臬。終其一生,莎士比亞都在不斷通過文學探索和思考人生的終極母題,希望解惑當下的生存困境,給世人以長久的啟迪。在通達凝練的文字中,傳達出不朽的思想。這也是為什么,當如今的我們通讀莎士比亞著作,仍能感受到相似的歷史之慨,人性之悲,譬如“身份焦慮”、譬如“都市孤感”。江畔何年初見月,江月何年復照人?莎士比亞出生和逝世于同一日,這似乎是一種偶然,又似乎是一種暗示。生與死,存與滅,仿佛是一個輪回,紡織了時間,締造了永恒,似玲瓏的圓,如佛頂的光,在這歷史廓圓中,晝始夜弭。讓今人讀莎翁著作,通古人靈犀,讓莎翁著千年煌作,解今人之惑。至此,莎翁不僅凝結了英國人的文學情結,更傳承為舉世精神、令后世仰觀鼻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