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圖反對藝術(Art)嗎?
——柏拉圖的技藝(technē)思想和古希臘的自然(phusis)
尹德輝
眾所周知,柏拉圖批判了繪畫和影像的虛假性,而且要把詩人從理想國中驅逐出去,又由于和亞里士多德的“技藝”觀的比照,就給人形成了他是反對藝術的直觀印象。但是,由于在柏拉圖的古希臘時代,從概念上來說并沒有“藝術”(Art)而只有“技藝”(techn
ē),而“技藝”概念中既有后來的“藝術”(Art)也有“技術”(skill, technique)的含義,又由于在我們今天的理解中,“藝術”和“技術”是既相關聯又相區別的,那么,柏拉圖在他的時代對“技藝”的批判以及對詩人等藝術家的驅逐就不能僅僅用我們今天的“藝術”概念來解讀。在歷史上,柏拉圖之前的古希臘人,甚至更早的古埃及人,或多或少都有一些涉及藝術或美的記載。比如,據第歐根尼·拉爾修(Diogenes Laertius)的記載,德謨克利特寫過“論趣味”“論色彩”“論不同的形狀”“論變化中的形狀”“論節奏與和諧”“論詩”“論散文的美”“論諧和音與不諧和音”“論荷馬”“論歌曲”“論詞語”“論繪畫”等(Graham523);還有,其后的高爾吉亞在“海倫頌”中有對語言表現力的論述,更早的在畢達哥拉斯學派的數學研究中對音樂理論的啟發、對柏拉圖美學的影響,阿納克薩哥拉最早地論述了透視原理(Bychkov3-4),等等。

一、 柏拉圖的技藝二分法與古希臘術語“技藝”的哲學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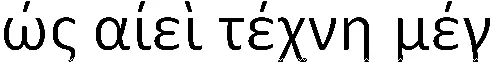
techn
ē是關于繪畫者的“技巧、手藝”(craft)的意思(Graham359),在德謨克利特的殘篇(DK68B59)“技藝和智慧都是經過學習而獲得的”(Graham663)中,techn
ē是泛指的“技藝、藝術”(art)的意思,等等。然而,到了柏拉圖的著作中,techn
ē在他的多數文本中則有了大量的出現,如“斐德若篇、法篇、高爾吉亞篇、智者篇、政治家篇、國家篇、歐緒德謨篇、伊安篇、美諾篇、普羅泰戈拉篇、會飲篇、泰阿泰德篇、伊庇諾米篇、大希庇亞篇、小希庇亞篇、斐多篇”等。在柏拉圖所討論問題的不同語境中,techn
ē的含義主要有這樣幾種: (1)抽象性的技藝、藝術,如“技藝及其前提、技藝的衰退、技藝與機會、技藝與經驗、技藝中的假象、模仿的技藝、技藝與知識、技藝與本性、技藝與美德”等等;(2)具體性的技巧、技術,如“農業的技藝、摔跤的技藝、拳擊的技藝、梳毛的技藝、計算的技藝、陶器的技藝、馭手的技藝、笛子的技藝、合唱的技藝、染色的技藝、繪畫的技藝、雕塑的技藝、滌罪的技藝、統帥的技藝、講演的技藝、商貿的技藝、稱重的技藝”等等;(3)特指的某些策略、方法,這一種往往和“技巧、技術”的含義相混雜,偶爾有貶義的傾向,但并不多見,以在“理想國”和“法篇”中最為明顯。可見,“技藝”(techn
ē)在柏拉圖的所有文本中,作為一個否定性概念出現的情況實際上并不多;同時,與其出現在前蘇格拉底哲學殘篇中時相比,其顯著的不同之處在于,柏拉圖已經將“技藝”作為一個哲學性的術語來對待,并作為構建其整個哲學體系的關鍵性概念之一。P.E.彼得斯認為,柏拉圖在“智者篇”和“政治家篇”中,開始將techn
ē作為一個專門的哲學術語(Peters190)。在“智者篇”中,柏拉圖對“技藝”做了多種方式的兩分法。開始,他以捕魚人為例,將“技藝”分為“生產性的”和“獲取性的”技藝(柏拉圖219B-C)。之后,他將“生產”也分為兩種,一種是神的生產,一種是人的生產,其中,神和人的生產又被縱向地分為兩個部分。在神的生產中,一部分是原物的生產,包括人和所有有生命的東西,以及自然物的元素如火、水,以及其他類似的東西,另一部分是影像的生產,包括睡夢中的形象、光照下的影子、視覺中的映像等等;它們都是神工的產物。在人的生產中,也包括原物和它的影像的生產,比如建造的房子和畫家繪制的房子的圖畫(265—66)。此處,單從“技藝”本身來看,柏拉圖顯然并沒有把“技藝”僅僅局限在技術、技能(skill)和復制、模仿的含義中,而是含有創造性的意味。——人和自然界,人造的各種事物,分別是神和人生產的“原物”(production of originals)(Plato290),都是創造性“技藝”的產物,而各種影像和模仿才是處在次要地位的。柏拉圖對“技藝”的這種分類,實際上是對“技藝”本身的創造性與摹仿性的關系說明,并不涉及他對任何一種“技藝”所持的否定態度。同時,“智者篇”中還包括關于“技藝”的另一種二分法。柏拉圖通過對“技藝”的層層分割,發現了“智者”的本質,即“智者的技藝是制造矛盾的技藝,來自一種不誠實的恣意的模仿,屬于制造相似的東西那個種類,派生于制造形象的技藝。作為一個部分它不是神的生產,而是人的生產,表現為玩弄詞藻。這樣的血統和世系可以完全真實地指定給真正的智者”(268D)。這里,在“技藝”與“智者”的關系中,“智者”的諸如“制造矛盾、制造相似、制造形象、玩弄詞藻、恣意的模仿”等等技藝就處在了一種被柏拉圖所批判的否定語境中。這表明柏拉圖換了一種方式,是從倫理的角度來對“技藝”進行分類。但很清楚的是,在上述“智者篇”通篇所論及的各種“技藝”中,柏拉圖并不是把所有的“技藝”都定性為是否定性的東西。柏拉圖對“智者”的“技藝”的否定,并不是對總體的或其他各種“技藝”的全部否定,這使得作為概念的“技藝”獲得了一種在否定和肯定含義的對立與共在之中的辯證統一性。
柏拉圖在“智者篇”中對“技藝”從不同角度做出的不同的“二分法”,體現了柏拉圖在概念的運用中,對同一個概念的不同方面含義的總體性肯定。就是說,如果要把“技藝”一分為二,那首先要在邏輯上把“技藝”作為總體的“一”,然后才能在這個總體的“一”的基礎上再分為“二”,所以,這個作為總體的“一”的“技藝”實際上就是一個同時包含著多與一、抽象性與具體性、肯定性與否定性的“技藝”概念。這和前蘇格拉底哲學中對“技藝”的個別性的運用是不同的。比如,在恩培德克利的殘篇(DK31B23)中,繪畫者的“技巧”指的只是具體的某一種技藝,而在德謨克利特的“技藝要經由學習獲得”,以至更早的繆塞俄斯“技藝通常勝于蠻力”中,“技藝”則是與具體的技藝無關的完全抽象性的概念;在前蘇格拉底哲學家當中,還沒有人能像柏拉圖一樣從不同的方面去運用這同一個“技藝”概念。
因此,由于有了在“智者篇”中對“技藝”的各種劃分和列舉,柏拉圖的“技藝”概念就成為一個包含著“多與一”“抽象與具體”“肯定與否定”的共在關系的包含著辯證對立關系的哲學性術語。
如果說柏拉圖在“智者篇”中用分割的方式捕獲了否定性的“智者”的技藝,那么,他在“政治家篇”中,則用分割的方式反過來發現了“政治家”的肯定性的“技藝”。在“政治家篇”中,柏拉圖通過和紡織技藝所做的類比,來說明政治家的技藝就是對“溫和型”與“勇敢型”的完美編織(311C),而且,“政治家”的“技藝”是“一門控制所有技藝的技藝”,“它是一種一般的技藝,所以我們用一個一般的名稱來稱呼它。這個名稱我相信屬于這種技藝,而且只有這種技藝才擁有這個名稱,它就是‘政治家的技藝’”(305E)。當然,在這個作為結論的表述中,柏拉圖沒有更進一步具體地說明“政治家的技藝”與其他的各種“技藝”有什么本質上的不同,但在整個“政治家篇”中,和在“智者篇”中一樣,柏拉圖同樣列舉了各種技藝,如醫生、計算、建筑師、傳令官、零售商、喂養、紡織、礦工、木工、耕作、打獵、體育、烹飪、屠宰、祭司、航海、軍事、法官、音樂、演講的技藝等等,那么,當柏拉圖強調“政治家的技藝”是“控制所有這些技藝的技藝”,及其與所有這些技藝的不同之處在于“政治家的技藝”的“一般性”,且是唯一的一種“技藝”之時,可以說,柏拉圖在“政治家篇”較之在“智者篇”中,在各種“技藝”和“政治家的技藝”的關系中更明確地指明了“技藝”(techn
ē)概念中的多與一、具體與抽象、肯定與否定的辯證統一關系 :“政治家的技藝”既是和所有其他技藝一樣的一種具體性的技藝,但又是和所有其他技藝不同的一種一般性的技藝,就像人和動物雖然都是動物,但人在具有動物的具體性之時,還能將各種動物的所有具體性都在自己身上表現出來。并且,在“政治家篇”中,柏拉圖還通過與度量(measurement)(Plato326)技藝的類比,揭示了“技藝”這個術語中存在的本體論關系。“如果兩個相關聯的命題是成立的,那么兩個命題都成立,如果它們是不成立的,那么兩個命題都不成立。第一個命題是: 技藝存在;第二個命題是: 過度與不足的可度量性不僅相對于不同事物而言,而且也意味著標準或適度的實現。這樣一來,如果第二種意義上的尺度存在,那么技藝也存在。反之,如果技藝存在,那么第二種意義上的尺度也存在。否定了其中的任何一個,也就否定了二者”(284D)。顯然,柏拉圖在此是在埃利亞學派的“存在”(coming into being)(Plato327)意義上討論“技藝”,“技藝”與“技藝的標準”如同前蘇格拉底哲學中的“本質”(phusis
)與“自然”(phusis
)的關系一樣,是在一種互相依存的頡頏關系中的共在關系。這與柏拉圖在“智者篇”中對“智者的技藝”的否定和對總體“技藝”的肯定中尚未明晰顯現出來的“技藝”的辯證關系相比,已經接近于對“技藝”(techn
ē)的本體論存在的直接表述了。因此,在后期著作的“智者篇”和“政治家篇”中,柏拉圖在“智者篇”中對“技藝”的局部否定與總體肯定的統一,與他在“政治家篇”中對“技藝”的局部肯定與總體肯定的統一,從兩個方面集中而全面地表述了他的“技藝”觀念,其“技藝”概念的內涵已經遠遠超越了前蘇格拉底哲學中的“技藝”,把古希臘的“技藝”(techn
ē)概念提高到一種哲學術語的思想高度了。這是柏拉圖的藝術思想歷經中世紀和近代美學、藝術哲學、藝術學的發展而影響至今的哲學基礎。二、 柏拉圖對“技藝”倫理批判的形而上學基礎

phusis
作為概念的自身同一性所帶來的矛盾,即“在phusis
(自然/自然界)中尋找phusis
(本質/本性)”的邏輯悖論,因為古希臘的“自然、自然界”(phusis
)和“本質、本性”(phusis
)在形式上是同一個概念。同時,從具體的方面來說,他們也無法解決比如作為萬物本源的“水”和江河湖海等現實世界中的水,這兩個“水”之間究竟具有怎樣一種邏輯關系的問題,所以,他們的包括宇宙、萬物在內的整個世界就無法形成一個邏輯統一的有機整體。因此,正如柏拉圖在“斐多篇”中所指出的,蘇格拉底曾經被探索自然(historia
peri
physe
ōs
)所吸引,但失望于從事這種研究的哲學家并不能給出一個合目的論的解釋,雖然阿納克薩哥拉假設了一個神圣的“努斯”(nous
,心靈、理性),但他忽略了表明“努斯”怎樣產生秩序以使萬物有序(斐多篇96B;97C;97D)。可見,柏拉圖對前蘇格拉底哲學家們的無神論和多元論(萬物的本原是水、氣、阿派朗、數、火、土、原子等等)是不滿意的。安東尼·普羅伊斯(Anthony Preus)指出,在古希臘哲學中,“自然”和“技藝”是兩個相互關聯的重要概念。當“自然”與“技藝”相對立時,“自然”在任何情況下都是指沒有人干預的自然,“技藝”在任何情況下都是指人的技藝。當然,古希臘的“自然”和“技藝”之間也存在一致性(continuity)的可能: 如亞里士多德在《物理學》中所說,一般說來,技藝在有些情況下完成自然所不能做到的,其他情況下則摹仿自然(Preus204; Barnes32)。實際上,“自然”和“技藝”的關系,在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那里,其觀點是有所不同的。安東尼·普羅伊斯這里所說的“自然”和“技藝”之間的直接對立,以及它們之間的相對統一,是在亞里士多德為“自然”和“技藝”做出明確的定義性闡釋和限定之后才出現的情況(Peters191),而在其之前的柏拉圖這里,作為概念的“自然”和“技藝”,還仍舊處在與前蘇格拉底哲學家們相近似的語境中,當然,與前蘇格拉底哲學家們有所不同的,是柏拉圖通過在“技藝”和“自然”之間做出對比,以“技藝”為中介,在“技藝”的二分法中最終走向了與前蘇格拉底哲學的無神論相對立的有神論立場,并構建了他的有神論的一元論的哲學體系。
如前所述,柏拉圖在“智者篇”和“政治家篇”中把“技藝”作為一個哲學術語來對待,并提升到一種接近于存在本體論的高度。而且,柏拉圖在“生產性的技藝、獲取性的技藝,神的技藝、人的技藝,肯定性的技藝、否定性的技藝”等等所有的“技藝”二分法中,就已經把“技藝”和“自然”的關系潛在地包含于內了——這是說,“神的技藝”的產物當然是“自然”的,而且“人的技藝和心靈”的產物也未必就一定是“不自然”的。
我們知道,前蘇格拉底哲學家一方面在事物中探尋本質、本性(phusis
),另一方面在本質、本性的發現中逐步發現總體的自然(phusis
),就是說,他們在phusis
(自然)中發現phusis
(本質)的矛盾悖論中,逐步擴大了“自然”的范圍和深化了對“自然”的認識。到了柏拉圖這里,在他的術語體系中,由于有了“技藝”的介入,前蘇格拉底哲學中的“自然”所本有的兩個基本含義就獲得了進一步的推進,并在柏拉圖的哲學中得到了體系性的轉換。首先,對前蘇格拉底哲學家來說,他們是在對事物的本質、本性(phusis
)的探索中,發展出對“自然、自然界”(phusis
)的認識和把握,所以,對前蘇格拉底哲學家們來說,他們對事物的認識和事物本身是渾然一體的(Lloyd101)。由于他們的事物不像在之前的神話中那樣,完全是一個有堅固的實體性外殼的外在性存在,因而,他們的“自然”就具有一種徘徊于實體和認識之間的中間性。但是,柏拉圖將“自然”作為神的“技藝”的產物,就一方面使“自然”又回到了和古希臘神話中相類似的那種實體性,同時另一方面,而且也是最主要的,這種實體性較之古希臘神話中多神論中的實體性,比如對日、月、海洋、江河、植物、動物、人等個別的自然對象來說,少了幾分在日神、月神、海神等等,這些各自相對獨立的神的主宰下所集合而成的無機的匯合性,而多了幾分由日、月、海洋等各個部分在一神論的統一中所構成的有機的整體性。柏拉圖對全部世界的這個有機的整體性是特別強調的,如他在“蒂邁歐篇”中指出,“就可能性而言,我們可以說這個生成的宇宙是一個由神的旨意賦予靈魂和理智的生物。因為這個宇宙一開始就包含一切理智的存在于自身,恰如這個世界包含我們和其他一切可見的生靈在內一樣。由于神想要把這個宇宙造得與最美好、最完善的理智的存在最為相像,因此就把這個宇宙建構成為一個包含所有本性上同種的生物于其自身之內的可見的生物。既然如此,我們說只有一個宇宙”(30C)。“為了使這個宇宙成為惟一的,與那完善的生物相似,創造主沒有創造兩個宇宙或無數個宇宙,而只創造了這個獨一無二的宇宙和天,他現在是惟一的,將來也是惟一的(31B)”。這是說,作為單一的神的“技藝”產物,“自然”本身不僅包含了各式各樣的具體性的事物,而且“自然”作為這些實體性的事物的總體也被柏拉圖賦予了包含內在目的性在內的整體統一性,因而成為一個實體性而且是有生命特征的有機的“自然”。
nomoi
)在內,歸根結底也要依賴于神的律法。這個思路不僅使得“技藝”和“自然”在概念的轉換關系上具有了統一的自洽性,而且使蘇格拉底的倫理學和在他之前的自然哲學得以完全統一起來,這符合古希臘哲學發展的內在邏輯。之后,斯多噶學派哲學家就繼承了這個觀念并做了進一步發展。“對他們來說,神完整地存在于所有的自然之中,造成自然的所有發展過程;實質上,神是‘技藝之火’(pyr
technikon
);同時,自然法則和神的法則是同一的,并且構成了物理法則和道德、政府的律法,所以,自然(phusis
)、技藝(techn
ē)和法律(nomos
)都包含在神之內”(Preus205)。顯然,“技藝”和“神”是柏拉圖繼承和改造古希臘前蘇格拉底自然哲學的兩個轉換樞紐,柏拉圖沒有任何理由要去否定“技藝”,他只是把“技藝”分為神的“技藝”和人的“技藝”,僅僅是在人的“技藝”創造中才出現了柏拉圖所要否定的“技藝”。如果把被柏拉圖所否定的這一部分“技藝”放到前蘇格拉底哲學的語境中,它們只是那些“不具本質或有違本性”,即,有違于事物的phusis
(自然)的“技藝”,就是說,柏拉圖所要否定的“技藝”(包括詩歌、繪畫等我們今天的藝術在內)都是“不自然”的“技藝”。這樣,從形而上學的角度來看柏拉圖對“技藝”(包括藝術)的否定性,他對那些有違于“理式”的,即“欺騙的(國家篇598C),無理性的、無益的、懦弱的(國家篇604D),多重詭計、相互傷害和作惡的(法篇679E)”等等技藝的否定,也就是對違背于前蘇格拉底哲學中的“自然”(phusis
)的技藝的否定,這最終保證了他從之前的古希臘哲學家們那里發展出來的統一的包括“自然”在內的全部世界的有機性和整體性。總體地看,和古希臘神話相比,柏拉圖揚棄了赫西俄德和荷馬的多神論,但發展出了神存在的一元論,并將神話中的人格神轉換為哲學中的抽象神。和前蘇格拉底哲學家們相比,如果說前蘇格拉底哲學通過“自然”概念否定了古希臘神話中的多元論世界觀,那么柏拉圖則繼承了他們的這個“自然”(phusis
)一元論,并通過術語“技藝”(techn
ē)揚棄了“自然”概念中的內在邏輯沖突,同時以“神”的最高存在賦予了包括宇宙和人類社會在內的全部世界以有機統一的整體性。三、 柏拉圖所反對的“技藝”和現代藝術中的“庸俗藝術”
雖然術語“技藝”在柏拉圖的思想體系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他只是以一種“非術語”(nontechnical)和“通俗”(popular)的方式運用這個術語(Peters190)。盡管這沒有給柏拉圖造成太多的麻煩,但其不可避免的影響在于,對后世的研究者,尤其是十八世紀“美的藝術”出現之后的研究者全面理解他的“藝術”哲學,留下了一個復雜糾結的理論障礙。或者說,柏拉圖的“技藝”概念的內涵是豐富而全面的,足以包容其后所有與“藝術”有關的各種現代概念,但是,由于柏拉圖使用“技藝”(techn
ē)這個術語的“非術語”和“通俗性”,就造成了在古希臘術語的寬泛性與各種現代語言的具體性之間的非對應性。在現代的研究者在忽視甚至漠視這種非對應性的情況下,當他們將一些現代術語及其含義直接代入到柏拉圖哲學的語境中時,就直觀地認為柏拉圖反對藝術和藝術家,這不可避免地影響到對柏拉圖藝術哲學的全面理解和準確把握,以至反過來再影響到現當代的藝術哲學。如上所述,柏拉圖所否定的并不是全部的“技藝”,而只是“技藝”中的一部分,并且,柏拉圖所否定的那一部分“技藝”,在現代藝術中也是存在的,因此,如果能說明柏拉圖所反對的那種“技藝”在我們今天的現代社會中也存在,并且被我們當作藝術,是不被反對的,那么我們就可以承認柏拉圖是反對“藝術”的,但是反過來,如果柏拉圖所否定的那一部分“技藝”并不是近現代社會中被作為“藝術”的那一部分,那么,柏拉圖就不能被認為是反對藝術(Fine Arts/Art)的。
那么,如果這種詩歌或藝術就是和自18世紀以來的“美的藝術”(Fine Arts)或20世紀后的“藝術”(Art)所指的一樣的詩歌,我們就可以接受一般所說的,柏拉圖所反對的“技藝”就是現代的“藝術”,但顯然,不僅“美的藝術”或“藝術”并非是那種滿足“無理性的、無益的、與懦弱聯系在一起”的本性的“技藝”,而且這種柏拉圖所要驅逐的詩歌恰恰也正是與“美的藝術”或“藝術”相對立的應該受到批判的藝術。比如,二十世紀初的俄國形式主義者什克洛夫斯基認為,“那種被稱為藝術的東西的存在,正是為了喚回人對生活的感受,使人感受到事物,使石頭更成其為石頭。藝術的目的是使你對事物的感覺如同你所見的視象那樣,而不是如同你所認知的那樣;藝術的手法是事物的‘反常化’手法,是復雜化形式的手法,它增加了感受的難度和時延,既然藝術中的領悟過程是以自身為目的的,它就理應延長;藝術是一種體驗事物之創造的方式,而被創造物在藝術中已無足輕重”(什克洛夫斯基等6)。再如,二十世紀中期的美國藝術批評家格林伯格在《先鋒派與庸俗藝術》中指出,在工業革命的背景中,農民和小生產者進入城市成為小市民階層,他們由于工業生產的需要而掌握了一定的文化,在喪失其原有民間文化而又需要某種文化消費的條件下,庸俗文化(Kitsch,也譯為“庸俗藝術”)應運而生。這種庸俗文化“專門為了那些對很正統的文化價值無動于衷而又渴望著某種文化娛樂的人。庸俗藝術把真正文化所貶斥和程序化了的形象用做原材料,助長和培養了這種遲鈍感覺,這正是它可以獲利的源泉。庸俗藝術是程序化和機械的,是虛假的快樂體驗和感官愉悅。它是我們時代生活中一切虛假事物的縮影。[……]庸俗藝術是一種欺騙。當然,它也有不同的層次水平,有些庸俗藝術水平高到足以對那些真理之光樸素的探尋者造成危害”(周憲194—95)。可見,柏拉圖所要驅逐的藝術是這里格林伯格所界定的庸俗藝術,即那種僅供消遣的、滿足人的“審美經驗自動性”的藝術。二十世紀后期的藝術評論家蘇珊·桑塔格將之看作一種藝術中的享樂主義,“人們離開了音樂廳后還能哼得出某段旋律帶來的那種快感,人們能夠識別、認同并按現實主義心理動機加以剖析的小說或戲劇中的某個人物帶來的那種快感,描繪在畫布上的一片美麗風景或一個戲劇性場景帶來的那種快感”(350)。顯然,柏拉圖所批判的那種詩歌或藝術,不僅不是18世紀以來的“美的藝術”或20世紀后的“藝術”中的詩歌或藝術,而且直接就是它們的對立面,即滿足“審美經驗自動性的、庸俗的、享樂主義”的詩歌或藝術,它們才是與柏拉圖所批判的那種“無理性的、無益的、與懦弱聯系在一起”的“技藝”是如出一轍的同一種藝術。


實際上,研究柏拉圖的藝術思想,必須要充分考慮到的一個基本前提就是,在古希臘不僅并不存在“藝術”概念,而且被稱為“藝術思想”的那樣一種東西也不是明確地存在的。但是,盡管如此,關于柏拉圖是否肯定或否定藝術,即,柏拉圖對藝術的反對,以及柏拉圖對藝術的肯定,及至古希臘的哲學術語“技藝”和近現代美學中的“藝術”概念之間的具體而確切的相互關系,對這些問題的探討既有助于柏拉圖的全部思想研究,也有助于現代藝術理論、藝術史和藝術批評研究,對美學基本問題的深層次探討具有重大的理論意義。
注釋[Notes]

The
Greek
Concept
of
Nature
一書中指出,古希臘人的“自然”觀念中已經包含著自然界與人類社會的統一性問題。如David Hahm在對該書的評論中所說,“納達福不把前蘇格拉底哲學純粹看作是對自然科學的探索,而是獨辟蹊徑地在社會政治語境中,將其作為新的城邦政治秩序的理論基礎。他認為,宇宙世界作為一個整體,不僅包括自然界,人類,而且包括人類社會,所有的前蘇格拉底哲學都圍繞著一個‘三重架構’(three part schema)而展開,即宇宙起源學、人類起源學和政治起源學,在時代政治因素的影響中,它們在一個完整統一原則的支配下發展。實證主義歷史學者可能不滿意于納達福的觀點,然而納達福的觀點并不能被輕易否定,因為大的歷史語境可以為其提供一定程度的可信性。”David Hahm, Gerard Naddaf. “The Greek Concept of Nature.”Isis
. 97.2(2006), p.344-45. See also, Gerard Naddaf.The
Greek
Concept
of
Natur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5) p.5.③pyr
,即赫拉克利特作為萬物本源的“火”。斯多噶學派將“神”描述為pyr
technikon
,即擁有創造事物的技藝的能力。當神同化萬物于自身時,宇宙呈現為燃燒之火,繼而萬物始于此。See, Anthony Preus.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Ancient
Greek
Philosophy
. p.228, 259.④ 文章得到了外審專家的指正和修改建議,在此表示衷心感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