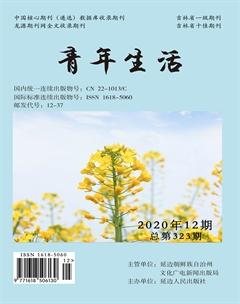淺談建筑施工混凝土裂縫的處理
張兆強(qiáng)
摘要:本文對(duì)混凝土的特點(diǎn)進(jìn)行詳細(xì)了解,找到混凝土裂縫的原因,確保設(shè)計(jì)的合理性,加強(qiáng)施工方面的控制,嚴(yán)格控制混凝土的材料等。針對(duì)實(shí)際施工情況,采取切實(shí)有效的措施,對(duì)混凝土裂縫進(jìn)行嚴(yán)格控制,實(shí)現(xiàn)良好的施工效果,提高建筑工程的質(zhì)量。
關(guān)鍵詞:建筑施工;混凝土裂縫;預(yù)防和處理
一、建筑施工混凝土的裂縫
混凝土是一種由砂石骨料、水泥、水及其他外加材料混合而形成的非均質(zhì)脆性材料。由于混凝土施工和本身變形、約束等一系列問題,硬化成型的混凝土中存在著眾多的微孔隙、氣穴和微裂縫,正是由于這些初始缺陷的存在才使混凝土呈現(xiàn)出一些非均質(zhì)的特性。才會(huì)導(dǎo)致今后建筑的質(zhì)量,混凝土建筑和構(gòu)件通常都是帶縫工作的,由于裂縫的存在和發(fā)展通常會(huì)使內(nèi)部的鋼筋等材料產(chǎn)生腐蝕,降低鋼筋混凝土材料的承載能力、耐久性及抗?jié)B能力,影響建筑物的外觀、使用壽命,嚴(yán)重者將會(huì)威脅到人們的生命和財(cái)產(chǎn)安全。如果在混凝土構(gòu)件出現(xiàn)裂縫,就會(huì)影響混凝土構(gòu)件的剛度和建筑物結(jié)構(gòu)的整體抵抗能力,即使裂縫的出現(xiàn)不會(huì)導(dǎo)致混凝土構(gòu)件的破壞或建筑物的倒塌,也會(huì)影響到建筑外觀,當(dāng)裂縫寬度超出一定限度時(shí),也會(huì)造成鋼筋銹蝕,影響結(jié)構(gòu)構(gòu)件的耐久性能。在長期荷載作用下,應(yīng)力不變,應(yīng)變持續(xù)增加的現(xiàn)象為徐變,應(yīng)變不變,應(yīng)力持續(xù)減少的現(xiàn)象為松弛。在一般情況下,混凝土具有良好的耐久性。為此對(duì)混凝土要有一定的抗凍性要求。防止裂縫的產(chǎn)生微裂縫通常是一種無害裂縫,對(duì)混凝土的承重、防滲及其他一些使用功能不產(chǎn)生危害。但是在混凝土受到荷載、溫差等作用之后,微裂縫就會(huì)不斷的擴(kuò)展和連通,最終形成我們?nèi)庋劭梢姷暮暧^裂縫,
二、建筑施工混凝土裂縫的類型
在建筑施工中混凝土容易產(chǎn)生裂縫,產(chǎn)生的裂縫主要是:
1、塑性裂縫多在新澆注的混凝土構(gòu)件暴露于空氣中的上表面出現(xiàn),塑性收縮是指混凝土在凝結(jié)之前,表面因失水較快而產(chǎn)生的收縮。塑性收縮裂縫一般在干熱或大風(fēng)天氣出現(xiàn),裂縫多呈中間寬、兩端細(xì)且長短不一,互不連貫狀態(tài),較短的裂縫一般長20~30cm,較長的裂縫可達(dá)2~3m,寬1~5mm。塑性裂縫產(chǎn)生的主要原因?yàn)椋夯炷猎诮K凝前幾乎沒有強(qiáng)度或強(qiáng)度很小,或者混凝土剛剛終凝而強(qiáng)度時(shí)很小,受高溫或較大風(fēng)力的影響,混凝土表面失水過快,造成毛細(xì)管中產(chǎn)生較大的負(fù)壓而使混凝土體積急劇收縮,而此時(shí)混凝土的強(qiáng)度又無法抵抗其本身收縮,因此產(chǎn)生龜裂。影響混凝土塑性收縮開裂的主要因素有水灰比、混凝土的凝結(jié)時(shí)間,環(huán)境溫度、風(fēng)速、相對(duì)濕度等等。
2、干縮裂縫,干縮裂縫多出現(xiàn)在混凝土養(yǎng)護(hù)結(jié)束后的一段時(shí)間或是混凝土澆筑完畢后的一周左右。水泥漿中水分的蒸發(fā)會(huì)產(chǎn)生干縮,且這種收縮是不可逆的。干縮裂縫的產(chǎn)生主要是由于混凝土內(nèi)外水分蒸發(fā)程度不同而導(dǎo)致變形不同的結(jié)果:混凝土受外部條件的影響,表面水分損失過快,變形較大,內(nèi)部濕度變化較小變形較小,較大的表面干縮變形受到混凝土內(nèi)部約束,產(chǎn)生較大拉應(yīng)力而產(chǎn)生裂縫。相對(duì)濕度越低,水泥漿體干縮越大,干縮裂縫越易產(chǎn)生。干縮裂縫多為表面性的平行線狀或網(wǎng)狀淺細(xì)裂縫,寬度多在0.05-0.2mm之間,大體積混凝土中平面部位多見,較薄的梁板中多沿其短向分布。干縮裂縫通常會(huì)影響混凝土的抗?jié)B性,引起鋼筋的銹蝕影響混凝土的耐久性,在水壓力的作用下會(huì)產(chǎn)生水力劈裂影響混凝土的承載力等等。混凝土干縮主要和混凝土的水灰比、水泥的成分、水泥的用量、集料的性質(zhì)和用量、外加劑的用量等有關(guān)。
3、溫度裂縫。溫度裂縫多發(fā)生在大體積混凝土表面或溫差變化較大地區(qū)的混凝土結(jié)構(gòu)中。混凝土澆筑后,在硬化過程中,水泥水化產(chǎn)生大量的水化熱,由于混凝士的體積較大,大量的水化熱聚積在混凝土內(nèi)部而不易散發(fā),導(dǎo)致內(nèi)部溫度急劇上升,而混凝土表面散熱較快,這樣就形成內(nèi)外的較大溫差,較大的溫差造成內(nèi)部與外部熱脹冷縮的程度不同,使混凝土表面產(chǎn)生一定的拉應(yīng)力。當(dāng)拉應(yīng)力超過混凝土的抗拉強(qiáng)度極限時(shí),混凝士表面就會(huì)產(chǎn)生裂縫,這種裂縫多發(fā)生在混凝土施工中后期。在混凝土的施工中當(dāng)溫差變化較大,或者是混凝土受到寒潮的襲擊等,會(huì)導(dǎo)致混凝土表面溫度急劇下降,而產(chǎn)生收縮,表面收縮的混凝土受內(nèi)部混凝土的約束,將產(chǎn)生很大的拉應(yīng)力而產(chǎn)生裂縫,這種裂縫通常只在混凝土表面較淺的范圍內(nèi)產(chǎn)生。溫度裂縫的走向通常無一定規(guī)律,大面積結(jié)構(gòu)裂縫常縱橫交錯(cuò)。梁板類長度尺寸較大的結(jié)構(gòu),裂縫多平行于短邊,深入和貫穿性的溫度裂縫一般與短邊方向平行或接近平行,裂縫沿著長邊分段出現(xiàn),中間較密。裂縫寬度大小不一。受溫度變化影響較為明顯,冬季較寬,夏季較窄。高溫膨脹引起的混凝土溫度裂縫是通常中間粗兩端細(xì),而冷縮裂縫的粗細(xì)變化不太明顯,此種裂縫的出現(xiàn)會(huì)引起鋼筋的銹蝕,混凝土的碳化。降低混凝土的抗凍融、抗疲勞及抗?jié)B能力等。混凝土結(jié)構(gòu)成型后,沒有及時(shí)覆蓋,表面水分散失快,體積收縮大,而混凝土內(nèi)部濕度變化小,收縮也小,因而表面收縮變形受到內(nèi)部混凝土的約束,出現(xiàn)拉應(yīng)力,引起混凝土表面的收縮。
三、建筑施工混凝土裂縫的預(yù)防和處理
在上述出現(xiàn)的施工過程中的混凝土裂縫中,針對(duì)上述所產(chǎn)生的裂縫,來進(jìn)行預(yù)防,保證施工的順利完成。
首先:對(duì)于溫度所產(chǎn)生的裂縫,要盡量選用低熱或中熱水泥,如礦渣水泥、粉煤灰水泥等。并降低水灰比,一般混凝土的水灰比控制在0.6以下,改善骨料級(jí)配,摻加粉煤灰或高效減水劑等來減少水泥用量,降低水化熱。改善混凝土的攪拌加工工藝,降低混凝土的澆筑溫度。在混凝土中摻加一定量的具有減水、增塑、緩凝等作用的外加劑,改善混凝土拌合物的流動(dòng)性、保水性,降低水化熱,推遲熱峰的出現(xiàn)時(shí)間。高溫季節(jié)澆筑時(shí)可以采用搭設(shè)遮陽板等輔助措施控制混凝土的溫升,降低澆筑混凝土的溫度。大體積混凝土的溫度應(yīng)力與結(jié)構(gòu)尺寸相關(guān),混凝土結(jié)構(gòu)尺寸越大,溫度應(yīng)力越大,因此要合理安排施工工序,分層、分塊澆筑,以利于散熱,減小約束。嚴(yán)格控制混凝土原材料的質(zhì)量和技術(shù)標(biāo)準(zhǔn),選用低水化熱水泥,粗細(xì)骨料的含泥量應(yīng)盡量減少。在澆筑混凝土之前,將基層和模板澆水均勻濕透。需要及時(shí)覆蓋塑料薄膜或者潮濕的草墊、麻片等,保持混凝土終凝前表面濕潤,或者在混凝土表面噴灑養(yǎng)護(hù)劑等進(jìn)行養(yǎng)護(hù)。
結(jié)語
因此根據(jù)裂縫的性質(zhì)和具體情況我們要區(qū)別對(duì)待、及時(shí)處理,以保證建筑物的安全使用。只有對(duì)裂縫進(jìn)行很好的預(yù)防,才能從根本上來進(jìn)行后期的處理。在建筑工程施工中,混凝土應(yīng)用的非常廣泛,能夠使建筑工程的穩(wěn)定性和堅(jiān)固性得到最大程度的保障。
參考文獻(xiàn):
[1]劉柏軍.建筑工程施工中混凝土裂縫的成因與治理[J].工程技術(shù)研究,2017(02).
[2]羅健林.住宅樓面板裂縫成因及質(zhì)量控制探析.現(xiàn)代經(jīng)濟(jì)信息.2009(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