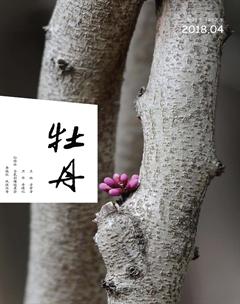荊軻的“可能性”
鞠辛陸
《我們的荊軻》是莫言歷史劇創(chuàng)作中最具代表性的一部。他以《史記》中荊軻刺秦王的情節(jié)展開劇本創(chuàng)作,同時對這一具有規(guī)范性的歷史記載實現(xiàn)了解構,塑造了一群個性鮮明、與史傳截然不同的歷史人物形象,在內在品質上與如今社會的精神生態(tài)現(xiàn)狀有了深度對接。本文將從歷史與現(xiàn)實的互文性出發(fā),通過剖析荊軻這一人物的塑造,展現(xiàn)莫言歷史劇創(chuàng)作的歷史觀念與文本特點。
歷史題材的戲劇如何寫,一直是個爭論不休的問題。歷史劇一定要尊重歷史的真實性,這個現(xiàn)實主義的前提是不容商榷的。可是,判定在何種意義上理解歷史的真實性,要取決于歷史的“現(xiàn)實觀”。黑格爾在《美學》中已有闡釋:“外在事物純然歷史性的精確,在藝術作品中只能算作次要的部分。它應該服從既真實而且對現(xiàn)代文化來說又是意義還未過去的內容。”所以,歷史之真實與否,關鍵看“今用”。克里斯蒂娃將互文性的定義為:“所有的文本,無非是其他文本的吸收和變形。”這里的其他文本用來指涉歷時層面上的前人或后人的文學作品,也可指共時層面上的社會歷史文本。這說明一個文本的創(chuàng)作必然會受到前人和共時社會歷史文本的影響,同時也影響著對前人文本的解讀。這便提醒人們,分析文本要著眼于現(xiàn)代世界,運用文本與社會歷史語境的互文性關系來解釋它。
一、荊軻之“死”
荊軻的形象在傳統(tǒng)文本接受中基本都是正面的,但莫言筆下的荊軻成為荊軻形象的顛覆性存在,這被許多文學評論指責為褻瀆歷史、甚至“膚淺庸俗”。首先應該明確的一點是,荊軻在歷史上的形象并非單一真實的存在,而是多個文本疊合成的復雜混合體。據張海明的《誰的荊軻——荊軻形象論之一》綜述,荊軻這一形象存在于《史記》《戰(zhàn)國策》《燕丹子》中,并還有若干關于荊軻刺秦王的零散記載。它們淵源不同,各自的形象特征亦明顯有別,這說明荊軻的歷史形象存在多種可能性。他的真實歷史面目縱然有無數猜測,但依然是空白的、撲朔迷離的。歷史的能指鏈總是不斷轉換,古人在記載歷史時,也會自覺不自覺地融入自己對于歷史人物事件的看法和理解,所以莫言認為,所謂的“忠于歷史本就是一個偽命題”。荊軻在諸多文本塑造之下,歷史形象早已湮沒在長久的時間積淀里,留予后人的不過是一個個文本形象。
后人對于荊軻其人其事的認識,首先就是源于司馬遷撰寫的荊軻事跡,這是后世傳播接受的第一文本,使人們在記憶和情感中對荊軻都有了非常穩(wěn)定的形象——一個頗具悲劇美和崇高美的俠客。但在這一個文本接受的過程中,人們認識到的不是歷史上真正的荊軻,而是司馬遷理解下的荊軻,時間積淀之下,荊軻的形象也由多元的文本可能變成了司馬遷塑造的一元文本現(xiàn)實。
所以,莫言對荊軻的顛覆并不是對歷史的解構重塑,而是對前人文本注入了當代人的思考,看到了荊軻的行為與現(xiàn)代社會價值取向的悖謬之處,從而對司馬遷筆下荊軻的文本形象進行了揚棄。
二、故事延承與精神出走
莫言的歷史劇觀,是舊瓶裝新酒,在相同的歷史事件框架下,裝進當代人對歷史的思考。毫無疑問,《我們的荊軻》的劇情走向是根據《刺客列傳》中荊軻刺秦王的故事基本脈絡來的,但他令荊軻的精神出走,實現(xiàn)了荊軻形象對歷史的突圍。
作者在訪談中有過明確表示,在讀過《史記·刺客列傳》后,他對當年的刺客表示了懷疑,在劇作中他也借燕姬之口對俠文化進行了直白否定:“所謂的俠士,其實是一些沒有是非、沒有靈魂、仗匹夫之勇沽名釣譽的可憐蟲。”可以看出,莫言從當代文化審視的角度,將俠文化定義為一種早該被批判和揚棄的價值存在:
“俠客這個行當的最高準則到底是什么?是追求真理與正義嗎?過去我們一直認為是這樣的。但……沒有真理,也沒有正義,因為他刺殺的人和指使他行刺的人,實際上都是為了爭名奪利、爭權奪勢。所以,俠客只是一個工具,一個職業(yè),遠沒有想象的崇高……俠客的很多高大形象是我們當代人賦予的、塑造的。所以,研究了這些以后,我覺得把荊軻還原為俗人、平常人,還原為一個要成名成家的俠客,應該是符合歷史真實的,當然是我認為的歷史真實。”
縱然莫言的論斷些許背離了司馬遷所撰《刺客列傳》的本意,但從他所秉持的現(xiàn)代意識而言,聯(lián)系到現(xiàn)實因素中恐怖襲擊、名利爭奪等社會問題,即便是一家之言,也是具有充分合理性的。
莫言毫不避諱地說,他的戲的靈魂是很年輕的。社會歷史發(fā)展到今天,已經進入現(xiàn)代社會與后現(xiàn)代社會相互交融的時期,社會觀念與價值取向發(fā)生著前所未有的松動,人們也擁有著前所未有的民主、寬松的人文環(huán)境,這就向文本創(chuàng)作與接受敞開了其更多的可能性,使多元的解讀和闡釋擁有了更寬廣的空間。這便為荊軻形象的再創(chuàng)作提供了社會現(xiàn)實語境。莫言是出于引發(fā)當代觀眾的思考這一角度去創(chuàng)作文本的,他想通過劇情的發(fā)展與演員的表演來讓觀眾聯(lián)想到現(xiàn)實,引發(fā)觀眾對自身的思索。雖然他為荊軻注入的精神品質帶著自己的影子,但他的自我“跟這個時代、跟大多數的人具有很多的共性”,他的情感方式、情感經歷、社會經驗以及對問題的看法,能夠跟大多數觀眾共鳴,這是種可遇而不可求的境界,而莫言做到了。荊軻為什么要刺秦王?歷史眾說紛紜。它的缺失造成了巨大的歷史空白,存在多種塑造可能,而莫言選擇了最適合當代社會架構思考模式的一個切入點,在歷史劇情走向不變的情況下,對人物的動機心理進行了大膽揣測——他從“熙熙而來,皆為利來;攘攘而去,皆為利往”中得到啟示,進而從文壇的追名逐利現(xiàn)象反觀俠客的初心,打通了“我就是荊軻”的血脈流貫,找到了作品的精神核心。
名利的追逐是人類最基本的生存動機,生命延續(xù)的渴望和對愛情的追求更是人類自始至終探討的話題,莫言的切入點正是人們所擁有的“共性”。文中荊軻對一刺成名毫不掩飾的渴望,對燕姬烈火一樣熾熱的愛情,對人類整體生存和存在狀態(tài)的感性直觀的追問,都流露出莫言深層的人文關懷與對普遍道德情感的認同,這與現(xiàn)當代以道德的普遍性、目的性(以人為目的)和自律性為精神底蘊的時代主流藝術觀念也是一致的。莫言將這些共性一一呈現(xiàn)在人們面前,使荊軻彰顯出以往史傳或文學作品中“英雄荊軻”被歷史所遮蔽的人性,具有獨特的藝術魅力。
莫言童年生活十分艱辛,饑餓、恐怖伴隨著他的成長。在文本中,荊軻少年時的貧困、乞食于燕國與莫言的童年經歷有相通之處;幾十年的寫作生涯中,為了改變命運、出人頭地,他曾幸運地遇到了許多“貴人”相助,也曾經受過險遭滅頂之災的政治批判,見過了各種各樣人物的名利爭奪之戰(zhàn)。這在劇作中也被一一具化,荊軻“提著小磨香油和綠豆粉絲”去拜訪名人投靠豪門,希望得以提攜重用,這與他當初為了改變命運而投身文學、渴望出人頭地的目的也是相通的。荊軻在易水河畔發(fā)出的天問,是他自我生命意識的最終覺醒,也是莫言回望自己創(chuàng)作歷程、反躬自省的新的覺悟與向往。莫言的坎坷經歷令他對人生命運有著深刻的感悟,也為他重構荊軻奠定了堅實的文學基礎,由此誕生的荊軻貼近現(xiàn)實、豐滿鮮活。
莫言的這部歷史劇,首先利用《史記·刺客列傳》荊軻部分的情節(jié)敷設篇章,從而在兩個文本間確立了一種肯定的互文關系;又通過諸多的作者自我指涉,形成了一種內文本關系;還因對司馬遷筆下人物的改造表現(xiàn)出一種否定的互文關系。所以,莫言劇作中的荊軻與歷史文本中的荊軻、莫言筆下的刺秦原因與歷史真實存在的刺秦原因,他們關系的本質不是相似性,而是他性。《我們的荊軻》的藝術成就沒有體現(xiàn)在其對歷史文本的借鑒上,更重要的恰恰體現(xiàn)在對它們的“疏離”上。莫言對史料進行解讀后,不僅運用了合理想象進行虛構,更“采用了化用前人作品的手法”,使歷史文本讓位于現(xiàn)實文本,與當今社會多元化價值取向保持了一致,并以荊軻這一人物道出了作者自身的精神品格與理想追求。
三、結語
文本作為歷史的承載者,并非客觀地反映歷史的外在現(xiàn)實,而是通過保存和涂抹等選擇性過程對歷史進行文本建構。作為描摹歷史的歷史劇,必然也不可避免地附著時代與個人色彩,其中現(xiàn)實與歷史的互文性思想也就由此顯現(xiàn)出來。《我們的荊軻》亦是如此,它誕生于21世紀,融入了當今時代的主流藝術觀念,這為荊軻注入了古今相通的情感內涵,增添了劇作的時代性色彩和持久性魅力。
(山東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