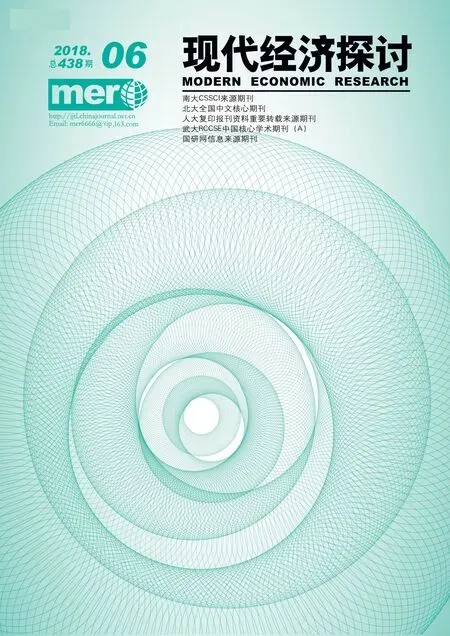國際投資仲裁中的國有企業投資者地位認定:構造、趨勢與因應※
陳 嘉 楊翠柏
一、 引言:當今全球經濟中的國有企業
隨著1989年柏林墻的倒塌,自由主義或自由放任經濟政策的勝利(即所謂“歷史的終結”),國家似乎不可逆轉的被迫從商業和經濟中撤退。全球范圍內的結構調整和私有化相繼發生。然而,歷史與國家的經濟角色不會終結。相反,它的存在在很多方面仍然是恰當的。例如2008年金融危機后,美國政府對汽車業和銀行業投資數十億美元,將某些世界著名私有企業轉變為準國有企業。即便在非特殊和緊急情況下,各國也會出于戰略考慮、社會政治或公共政策目的和(或)追求利潤而投資企業。據聯合國貿易與發展會議(以下簡稱UNCTAD)估計,大約550家國有跨國企業在全球共擁有15000多家外國子公司,控制著超過2萬億美元的海外資產,其中外國直接投資已達1600多億美元,占全球外國直接投資資金量的11%以上(Karl and Jonathan,2014)。從行業領域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2012年發布的報告稱,20家大型石油公司中的15家為國有屬性,包括俄羅斯石油公司、中石化、挪威國家石油公司和阿美石油公司(EITI,2014)。另外,國有企業還涉足采礦、能源、汽車、金融服務、公用事業、電信、航空航天等部門并得到迅猛發展。
毫無疑問,來自中國、俄羅斯、阿聯酋、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沙特阿拉伯、印度和巴西等新興經濟體的國有企業正在引領全球經濟的發展。它們的規模和治理結構決定了其能夠承受有助于目標國經濟穩定的高風險和較長投資周期。但東道國因受益于外國投資而增加就業和收入的同時,也因國有企業與本國密切的政治聯系,以及投資領域的戰略敏感性,而擔心會對社會文化、政治以及安全和競爭帶來不利后果(Guy Chazan,2017)。甚至懷疑國有企業淪為推行本國政策或外國殖民的國家工具(Kelly Riddel,2014)。所以,國有企業的投資可能不會受到普遍歡迎,特別在當今民粹主義和保護主義勢力再度升溫的背景下。
意識到需要解決此類問題的緊迫性和重要性,諸如經合組織有關“國有企業公司治理準則”等多邊舉措要求它們嚴格遵守透明度和披露義務。“準則”還規定,國有企業不應被用作資助政治活動的工具。但上述“軟法”無法避免一國與他國國民之間投資爭端的出現。此時如果投資者本國的重大利益受到牽連,則國內政府可采取外交措施、或訴諸國際法院和世界貿易組織爭端解決機制等國際(準)司法機構。而投資者可以提起投資者-國家仲裁。如今,大多數國際投資協定(以下簡稱IITs)都包含了根據既定的國際仲裁規則指定仲裁庭的仲裁條款,用以解決條約締約國與另一締約國投資者之間的爭端。其中“解決國家與他國公民投資爭端公約”(以下簡稱ICSID公約),ICSID附加便利措施和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仲裁規則等在投資仲裁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并努力以實現平等對待外國直接投資與保護東道國自然資源和其他公共利益之間的微妙平衡為基本導向。然而,這一切的前攝性條件是,國有企業能否享有IITs下的“投資者”或(和)ICSID公約下的“國民”地位*投資者訴諸第三方仲裁機構主要包括ICSID機構和SCC、ICC等國際商事仲裁機構,但目前關于東道國對國有企業投資者地位的質疑僅在ICSID仲裁庭提起過。并且ICSID公約對“國民”有專門的定義,所以若投資者提起ICSID仲裁,需要同時滿足IIT下的“投資者”和ICSID公約下的“國民”。?
二、 IITs和ICSID公約下的國有企業投資者地位
1. IITs下國有企業投資者地位的判斷:以《維也納條約法公約》第31條為中心
學者Jo En Low曾就“投資者”定義問題對851項IITs做過統計(表1),從中可看出,IITs對國有企業投資者地位的態度存在分歧。盡管在調查中僅發現1983 年巴拿馬分別與德國、瑞典的雙邊投資協定(以下簡稱BIT)明確禁止了國有企業的投資者地位,但約有80%的IITs對此不置可否,那么是否意味著可推定所有國有企業(在任何情形下)都可根據ICSID公約向東道國提出訴求?下面將從條約解釋的角度進行探究。

表1 IITs規定“國有企業”作為投資者的情況匯總
資料來源:Jo En Low. State-Controlled Entities as “Investors” under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greements.ColumbiaFDIPerspectives, 2012,9(4).
根據《維也納條約法公約》(以下簡稱VCLT)第31(1)條的規定,一項條約應依其用語按其上下文并參照條約之目的及宗旨所具有的通常含義,善意解釋之。據此,在IITs明確規定了保護國有企業投資條款的情況下,仲裁庭并不難以確定其投資者地位,因為“通常含義”一詞將在很大程度上對此作了解釋,而進一步審視IITs上下文以及目的和宗旨,很少出現推翻此條款的效果。如果沒有任何相反的明示規定,國有企業將享有與純粹私人投資者完全相同的待遇,無論其是否具有準公共性質。
例如,北美自由貿易協定(以下簡稱NAFTA)第201(1)條將“企業”解釋為依法組成的任何實體,包括任何公司、信托、合伙、獨資、合資或其他團體,不論其是否盈利,也不論私人或政府擁有。類似地,建立多邊投資擔保機構公約第13(a)(iii)條對投資者下的法人范圍涵蓋“私有或公有”。某些其他IITs甚至將保護范圍擴大到政府本身。例如,捷克共和國-科威特BIT明確規定了締約國一方的投資者包括該締約國政府,以及政府機關或附屬部門,如各種社會組織機構、發展基金、當局、基金會和代理機構。
但很多時候IITs對“投資者”的模糊處理使得仲裁庭無法像上述協定那樣可以通過對“通常含義”的解釋將國有企業定義為投資者。例如,中國-卡塔爾BIT中,卡塔爾一方的投資者是指根據卡塔爾法律組成并在其領土內擁有住所的法人,包括公司、總公司、公共組織、公共和半公共實體。然而,中國一方法人投資者指依照中國法律設立、并且在其領土內擁有住所的經濟組織。中國-加納BIT也存在類似的不對稱現象,其中加納一方的投資者是指國家公司和代理機構及依照加納法律登記,從事對外投資或貿易的私人公司。那么,雖然中國一方對投資者的定義并未明確排除國有企業地位,但卡塔爾和加納一方對國有企業的明確表述,是否表明其并不試圖賦予中國國有企業投資者地位?
又如,中國-秘魯BIT中,秘魯一方的投資者,是指依照秘魯法律設立并在其領土內擁有住所的所有法人,包括直接或間接由秘魯國民控制的,在本協定規定范圍內進行經濟活動的民營公司、商業公司和其他具有或不具有法人資格的組織。然而,中國一方的投資者指依據中國法律設立,并在其領土內擁有住所的經濟組織。與中國-卡塔爾BIT和中國-加納BIT相比,該BIT締約雙方不僅對“投資者”定義不同,而且也都未明確國有企業地位問題。
筆者以為,當出現上述兩類情形時,仲裁庭需要借助VCLT第31(1)條的另外兩種解釋方法,即通過對IITs的上下文或目的和宗旨來評估國有企業的投資者地位保護。因此,仲裁庭應調查締約雙方是否有意將諸如國有企業等不同類型的投資者涵蓋或排除在BIT中,比較締約雙方有關公司及其成立的國內立法。例如,秘魯的國內法律以對民營或商業公司和其他組織專門規定的方式,將國有企業或類似實體排除在這些條款之外。而且,IITs中可間接證明締約雙方意圖的各種其他條款也屬于調查范圍,正如中國-特立尼達和多巴哥BIT,中國-烏干達BIT,中國-埃及BIT雖都統一采用不明確國有企業地位的投資者定義但這三項協定都涉及可能與國有企業地位間接相關的另一條款,即締約一方或其指定機構有權代表投資者就代位事項提出申索的代位權條款*比如,中國-特立尼達和多巴哥BIT第九條有關“代位”的規定:“若締約一方或其指定機構基于對在締約另一方領土內的投資所作的擔保對本國投資者進行了支付,后一締約方應當認可得到補償的投資者將其全部權利和請求權依法轉讓給前一締約方或其指定機構,前一締約方或其指定機構有權代位行使與投資者同樣的權利。”。與將代位權限制于私人實體如作為投資者承保人的保險公司的做法不同,上述協定將其擴大至締約方或任何“指定機構”。其潛在意義在于,締約方如果有意賦予國家或某些國家機構投資者地位,一定會以明示的方式表達。
根據VCLT第31(2)條規定,就解釋條約而言,序言屬于“上下文”的組成部分,所以我們可依賴IITs中的序言進一步尋找證據。以德國-伊朗BIT為例,定義條款將德國一方的“公司”界定為“任何法人和任何商事或其他公司或組織”。但是伊朗一方的“公司”是指法人或公司或機構。這種寬泛、包容的定義似乎合理的將國有企業推定為公司。尤其對伊朗一方的公司而言,因為其提到了“公共機構”一詞。然而,德國或伊朗國有企業在德國-伊朗BIT項下的投資者地位,一定程度上與其序言所明確規定的“旨在刺激私人投資活動積極性”相矛盾。盡管這并未完全否定任何一方的國有企業根據BIT提出訴求的資格,但這確實意味著這些企業進行的任何“公共”投資不會獲得保護。
與此同時,仲裁庭的調查不應超越VCLT規定的解釋權限。當出現依VCLT第31條解釋,意義仍屬“不明或難解”時,該公約要求仲裁庭參考解釋之補充資料,包括“條約的準備工作及締約的情況在內”。例如IIT的起草材料和國家間的官方相關往來信函。但現實中,仲裁庭可能會被促使將當前的IIT與締約方簽訂的其他IITs進行比較。例如,仲裁庭在調查沙特阿拉伯國有企業是否有權依據沙特阿拉伯與比利時-盧森堡經濟聯盟的BIT提出主張時,它可能寄希望于沙特阿拉伯-馬來西亞間的BIT條款得到指引。特別是,試圖將沙特阿拉伯與上述兩個不同國家簽署的BIT中的投資者定義進行比較,以確定與早期的馬來西亞BIT相比,該國在之后與比利時-盧森堡經濟聯盟BIT中對投資者作了更為廣泛的界定。但是,任何此種嘗試都屬于錯誤推定。正如仲裁庭在Aguas del Tunari, S.A.訴玻利維亞共和國一案中指出的,除了涉及爭端的特定BIT以外,一國與它國締結的其他BIT實踐對完成VCLT第31條下的解釋任務并無直接價值(ICSID,2017)。在 Rompetrol 訴羅馬尼亞一案中,仲裁庭同樣認為,VCLT并未授權仲裁員援引與它國締結的其他BIT條款作為本案BIT的解釋依據。
2. 對ICSID公約第25(1)條的理解
ICSID公約第25(1)條規定,中心的管轄適用于締約國(或締約國向中心指定的該國的任何組成部分或機構)和另一締約國國民之間直接因投資而產生并經雙方書面同意提交給中心的任何法律爭端。
正如Schreuer教授所言,ICSID公約旨在填補國家間(國際法院等司法或準司法機構解決)或私人實體間(國內法院或商事仲裁等解決)爭議以外的程序空白(Schreuer et al.,2009:160)。并認為以下原因導致國家,國家機構或國際投資保險組織不能成為ICSID程序中當事方。首先,公約為國家和另一國國民間的爭端提供解決。第25(1)條的清楚表述不能被重新解釋以涵蓋投資者一方的國家,國家機構或國際組織。其次,公約第27條有關禁止通過外交保護以支持投資者的規定很好地反映了爭端去政治化的目的。最后,公約的準備工作文件表明,排除國家,國家機構或國際組織作為投資者一方進入ICSID程序實屬有意決定(Schreuer et al.,2009:186-187)。
另外,作為在ICSID公約構思和談判中起著關鍵作用的世界銀行總法律顧問Broches寫到,公約的廣泛目的是促進外國私人投資,其序言首句就使用國際私人投資一詞(Broches,1995:202)。執行董事關于ICSID公約的報告同樣指出,設立一個旨在方便解決國家與外國投資者之間爭端的機構,可能是朝著互信邁出的重要一步,從而刺激更多的私人國際資本流向那些希望吸引它的國家(World Bank,1965)。對于何為“私人國際資本”?Broches認為,當今世界,私人和公共投資之間基于資本來源的傳統區分,即使未過時,也不再有意義。很多公司是私人和政府資本的結合,部分公司雖然只由政府一方出資,但其在法律特征和活動上與私有企業并無二致。因此,基于公約目的,混合型經濟公司或政府所有型公司不應被取消作為另一締約國國民的資格,除非其作為政府代理人或履行政府基本職能(Broches,1995:201-202)。該觀點在理論界和實務界被稱之為Broches標準。
三、 Broches標準在國有企業投資者地位中的運用:基于對CSOB訴斯洛伐克共和國案的反思
1. 案情及裁決概述(ICSID,1999)
CSOB訴斯洛伐克共和國一案(以下簡稱CSOB案)無疑是Broches標準在國有企業投資者地位運用的代表性案例*雖然北京城建訴也門共和國案也涉及Broches標準的應用,但其基本遵循了CSOB訴斯洛伐克共和國案的思路,所以從開創性角度看,對該案的研究意義更大。而其他案件如HEP訴斯洛文尼亞,CDC訴塞舌爾和Telenor訴匈牙利,仲裁庭都在未作任何分析的情況下認定國有企業符合第25(1)條項下的締約國“國民”。。1989年捷克斯洛伐克發生“天鵝絨革命”之后,國有銀行CSOB逐步放棄對國家的完全經濟依賴,并采取措施使其在新的經濟環境下行使獨立的商業銀行職責。
作為轉型的一部分,CSOB與斯洛伐克共和國以及捷克共和國財政部簽訂了一項合并協議,規定由CSOB將若干不良貸款組合應收款項轉讓給分別設立于捷克共和國和斯洛伐克共和國的兩個收款公司,并由收款公司向CSOB支付轉讓的應收款。之后CSOB向ICSID中心提交仲裁請求,聲稱斯洛伐克共和國違反“合并協議”。
斯洛伐克共和國認為,CSOB是捷克共和國的國家機構而非獨立的商業實體,捷克共和國才是爭端中的真正利益方,所以兩締約國之間的爭端不屬于ICSID公約第25(1)條規定的管轄范圍。
仲裁庭首先證實,第25(1)條反映了中心對締約國間的爭端沒有管轄權,必須由另一締約國國民方可向締約國提出主張。當判定“部分或全部由政府所有”的公司是否有資格成為第25(1)條下的另一締約國“國民”時,仲裁庭采納了Broches標準:即國有企業是否作為政府代理人或履行政府基本職能。盡管CSOB股份的65%由捷克共和國擁有,盡管CSOB的“大多數存在”,為捷克共和國的代理人,促進或執行了國際銀行交易和外國商事經營活動等政府政策或國家目的的實現,但仲裁庭沒有據此否定CSOB的締約國國民資格,而是轉向了該標準的第二項要件:CSOB是否履行了政府基本職能。在此項下,仲裁庭認為僅需要考慮企業活動的性質而非目的。
通過對處于爭議中的特定投資活動特征的詳細描述,仲裁庭得出結論,ICSID公約并不排斥法人被國家所有和控制的現狀。即便CSOB活動可能由國家政策驅動或受益于政府政策和補貼,但只要其本身不從事政策制定或發展,或立法或行政活動,我們就不能說,不具有主權、次國家實體或國家機構特征的CSOB的投資屬于履行政府基本職能。因此它有資格成為第25(1)條下的締約國國民。
2. 重新審視CSOB案:Broches標準的解構與重構
(1) 第一項要件:“履行政府基本職能”認定的不充分。雖然仲裁庭完全聚焦企業行為性質而對目的不作任何考慮的做法,保證了裁判的確定性和可預見性,但基于以下兩點理由,該案不應被其他所有仲裁庭無條件接受作為判斷ICSID公約第25條對國有企業管轄權的適當標準。首先,長期以來,“商業交易”方法在很多國內法中成為法院判斷是否對外國國家及其附屬機構行為享有管轄權的標準,即只有當這些實體的活動被視為“商業”或非主權行為時,法院才會對其行使管轄權(Shaw,2008:708-714)。但最近適當的同時考慮企業活動的性質和目的已成為一種趨勢。例如《聯合國國家及其財產管轄豁免公約》第2(2)條規定,在確定一項合同或交易是否為“商業交易”時,應主要參考該合同或交易的性質,但如果合同或交易的當事方已達成一致,或者根據法院地國的實踐,合同或交易的目的與確定其非商業性質有關,則其目的也應予以考慮。又如,在“CDC訴塞舌爾案”中,推動申請人貸款活動的關鍵目的——為發展中國家的長期減貧作出貢獻——表明行使政府而非商業功能。相反,在“Telenor訴匈牙利案”中,電信服務提供商Pannon十分關注自身的盈利能力,在年度報告中經常將自己形容為“有利可圖”,并且在1999年至2003年期間其利潤幾乎翻了一番。
不少國內法院也逐漸認識到,將活動置于包括目的在內的更廣范圍內的考量有助于準確的判斷行為的主權或非主權性質。正如加拿大最高法院所認定的那樣,對所涉活動進行完全脫離目的的審查將注定是不可行的(Supreme Court of Canada,1992)。美國第五巡回上訴法院,在De Sanchez 訴Banco Central de Nicaragua等案寫到,除非我們可以調查某些行為的目的,否則我們無法確定其性質(United States Court of Appeals, Fifth Circuit,1985)。同樣,澳大利亞法律委員會也談到,行為目的和性質之間的概念區分無法持續:不可能在不考慮其目的的情況下對任何活動的性質進行分類……“政府”和“商業”的分類本身是有目的的(Australian Law Reform Commission,1984)。
其次,正如 Burlington Resources Inc. 訴厄瓜多爾共和國所指出的那樣,仲裁庭應該對國際法庭先前的決定予以適當的考慮,除非存在充分的相反理由,否則應以之前一系列案件中所確立的一貫方式加以解決(ICSID,2010)。這有助于投資法的和諧發展,從而符合國家和投資者對法治確定性的合理期待。但“充分的相反理由”應該導致仲裁庭放棄這一做法。如上所述,CSOB案仲裁庭在審查國有企業活動時完全不顧及“目的”的觀點并不十分具有說服力。而且,該裁決系統性缺失會使其他仲裁庭更易偏離其做法。考慮到CSOB案為ICSID仲裁庭管轄權最早裁決之一,其無法過多的遵循先例和受益于相關學術討論,因此,與當前投資爭端管轄權決定動輒數百頁,并引用大量權威著作和法律文件的論證說理相比,CSOB案決定僅僅12段的闡述,以及引用來源的單一,使得其無論從長度、廣度和深度都無法比擬。也許最重要的是,該案是在當前國有企業的規模、數量顯著增加以及這些國有企業對很多IIT締約國投資政策產生影響之前作出的決定。
重新審視CSOB案,我們發現此爭端產生于前蘇聯陣營剛剛解體,包括捷克共和國在內的東歐正在由計劃經濟向自由市場經濟劇烈轉型這種獨特的背景下。CSOB擔心將其參與貸款協議的行為視為政府政策的實施,但實際是CSOB就談判貸款協議接受捷克國家指令是為了阻斷其與捷克國家的關聯。換句話說,CSOB活動的真正目的不是推動政府的政策,而是通過該政策進行結構調整,促進私有化的實現,確保今后不再被視為捷克國家的一個分支。這并未威脅到ICSID公約的體系理念或基本原理。因此,如果該案的仲裁庭愿意拋棄形式主義的分析,在所發生的更大背景下審視CSOB活動的性質和目的,并考慮政府的最終目標,那么裁決會更具有說服力。
但同時也需強調的是,一國國有企業通常承擔多種功能,我們很難將商業目的與本國國家政策以及政治關切之間完全剝離。過分探究它們投資的主觀要素而對ICSID管轄權作限縮解釋并因此否定國有企業地位,不僅不符合ICSID公約的宗旨,甚至可能導致該機構淪為反對發展中國家或經濟轉型國家的工具,嚴重違背了相關國家的長遠利益。為維護ICSID的合法性和有效性,仲裁庭應賦予多功能國有企業的投資者地位,除非它們明確清楚的只履行政府基本職能。總之,只有對國有企業經營活動進行整體評估后才能確定,它們的行為是否已從商業目標導向轉至純粹的實現本國政治、經濟和社會關切。
(2) 第二項要件:“作為政府代理人”認定的缺失。如上所述,Broches標準寫到,為了公約的目的,混合經濟公司或政府擁有的公司不應被取消為另一個締約國的國民的資格,除非它履行政府職能或作為政府代理人。其中“或”一詞清楚地表明,該標準由兩項明顯不同的調查要件構成,即若任一要件得到滿足,則ICSID公約將不適用于國有企業投資保護。顯然CSOB案仲裁庭僅部分關照了“履行政府基本職能”這項要件,對“政府代理人”要件的“漠視”令人遺憾。
事實上,仲裁庭已被多次告知CSOB是捷克共和國代理人,但最終未給予其如“政府基本職能”要件那樣同等的關注。相反,它似乎有意將兩者混同,例如它寫到,“不可否認的是,CSOB的大部分存在是代表國家為促進或執行國際銀行交易和外國商業活動而行事。但在判定CSOB是否履行政府職能時,應關注這些活動的性質而非其目的。”在下一段又提到,“……即便有人認為不良資產來自于作為國家代理人的CSOB的行為,那么CSOB根據合并協議的規定將其從賬目中除去以改善余額和鞏固其財務狀況的措施必須被視為商業性質。”
Broches標準對兩項要件間的位階關系并未作任何暗示,因此,仲裁庭沒有任何理由主要關注“政府基本職能”而僅簡單提及“政府代理人”要件,也沒有任何理由推定,只要國有企業不履行“政府基本職能”,就能對此進行管轄。
在此基礎上,我們需要考慮以下兩個重要且相關聯的問題。首先,國有企業在什么情形下將“作為政府代理人”?其次,該要件如何從概念上與“政府基本職能”相區分?
也許《關于國家對國際不法行為的責任條款草案》(以下簡稱ILC草案)第8條可為理解“政府代理人”要件提供參考。ILC官方評注對此認為,盡管“作為一般原則,根據國際法實體的行為不可歸責于國家,但若因從事行為的實體與國家之間存在特定的事實關系,此種行為可歸責于國家。”它進一步解釋說, 第8條意在適用于私人或實體“按照國家指示執行的行為”或“在國家指揮或控制下的行為”兩種不同情形。并且特別指出,“指示”“指揮”和“控制”三個術語之間相互獨立,只要滿足其一就已足夠。
既然該條款與Broches標準的“政府代理人”要件都涉及判斷實體在一定條件下是否被視為一國代理人,那么,與ILC第8條有關的判例法和評注可作為仲裁庭處理Broches標準中的“政府代理人”要件的重要參考。具體來說,首先,他們可為調查Broches標準中一國與所謂的國家代理人間的關系提供一些有價值的見解。例如,ILC草案評注確認,“事實上由其授權的行為歸屬于國家在國際仲裁中被廣泛接受。”針對“是否在國家的指揮或控制下從事的行為”問題,ILC草案評注還解釋說,只有在國家指揮或控制了具體行動,且被指控的行為是該行動的組成部分時,該行為才能歸于國家。
其次,ILC草案評注特別考慮到了國有企業背景下的第8條運作。評注認為,國際法承認國內層面的企業獨立性,除非其利用公司法人面紗或其他欺詐或逃避工具。這意味著,國家最初建立公司的事實,不能成為將該公司的后續行為歸責于國家的充分依據。但如果有證據表明國家為了取得特定的結果,而正在利用其在公司的所有權或控制權,那么有關行為可歸因于國家。
最后,針對國家所有或國家控制的實體行為,第8條對國際投資法的貢獻已經得到承認,并被越來越多的仲裁案例引用。例如,EDF訴羅馬尼亞案中,仲裁庭在考慮羅馬尼亞政府是否對其擁有的兩個獨立企業的行為負責時提到了第8條。國有企業與申訴人EDF就羅馬尼亞國際機場免稅服務以及往返機場的航班事項成立合資企業。EDF聲稱,羅馬尼亞通過國有企業間接損害了其投資。仲裁庭依據第8條同意將國有企業的行為歸因于羅馬尼亞。特別是,它認為羅馬尼亞通過一系列的授權和指揮,有效地利用其對企業的所有權和控制權來取得自己利益。又如,Bayindir訴巴基斯坦案中,仲裁庭適用第8條讓巴基斯坦對該國國家公路管理局(National Highway Authority, 簡稱NHA)的活動承擔責任。Bayindir接受NHA委托,為伊斯蘭堡和白沙瓦之間的一條高速公路提供施工及配套服務。在對項目進行了多次延誤和修改之后,Bayindir提起了仲裁,聲稱巴基斯坦的非法施壓,脅迫,拒絕正當程序,以及政府陰謀驅逐公司,并把工作交給當地的競爭對手等違反了公平公正待遇。仲裁庭認識到,NHA為巴基斯坦法律規定的有權以自己名義起訴和被訴的公共法人和法人團體。但是,由于巴基斯坦政府的各種相關決定是通過NHA實施,且NHA的各項重要決定在未經政府明確批準之前未得到執行,因此仲裁庭認定,NHA行為可歸責于巴基斯坦。
然而,不管如何相似,都應清楚,根據Broches標準的“政府代理人”要件進行調查的事項本質上不同于ILC草案第8條下的調查及國家歸責問題。這種區別可能會降低第8條對Broches標準的解釋和應用價值。國家歸責問題產生于被申訴國被指控通過第三方代理人侵犯另一實體或另一國家的權利,比如,國際法院對武裝沖突行為的國家責任評估,美伊求償法庭等這種具有特定目的的國際法庭,對各種公共和私人行為的國家責任評估,以及ICSID仲裁庭或其他仲裁機構對國有企業違反合同的行為能否歸因于東道國的評估。例如在EDF訴羅馬尼亞案中,EDF只需將TAROM取消免稅服務合同行為歸因于羅馬尼亞,而無需將TAROM的一般或其他特定經營活動與羅馬尼亞聯系起來。但是,如果引用Broches標準的“政府代理人”要件,則可能需要作更廣泛的分析。特別是,為了否定國有企業的投資者地位,僅僅把國有企業的投資活動和行為的某些方面歸于其母國,可能是不夠的。相反,考慮到海外投資項目業務繁雜,階段多且周期長,并且隨著時間的推移,可能承載著與最初預期不同的特征和業務,因此仲裁庭有必要合理的依賴特定情境對國有企業活動及其目標進行更為全面的分析。
不過,ILC第8條及其相關的判例法和評注仍然為運用Broches標準的“政府代理人”要件提供了基本框架。通過此,仲裁庭可以識別出能夠證明對重要投資決策有高度控制力的具體指引,調查國有企業與本國之間的聯系以及本國對投資的控制手段,并且確定該控制是否在投資方面取得特別重要的結果。
另外,與“政府基本職能”要件關注“具有政府或監管權力要素的國有企業如何進行投資活動”相比,“政府代理人”要件關注的是“國家在多大程度上指導國有企業的投資活動。”
四、 國有企業投資者地位的中國因應
1. 充分利用ICSID機制對國有企業的友好態度,積極提起訴求。
從CSOB案可看出,仲裁庭主要以國有企業活動是否為商業性質判斷其投資者地位,另外在北京城建訴也門政府案中,針對也門政府的反對意見:“(i)北京城建是在中國政府的領導和控制下從事的以實現社會,工業和外交政策為目標的活動;(ii) 北京城建被授權在中國行使政府權力,”仲裁庭基本延續了CSOB案裁決關于“投資的民商事功能的具體情勢分析方法”,認為,“在任何有關‘代理’一詞的意義上,本案證據都不能證明,北京城建在建設也門機場航站樓方面充當中國政府代理人。”同時,沒有證據表明,中國政府參與北京城建的重大決策就能判定北京城建在特定情境下(如機場航站樓建設)履行了政府職能而非商事職能。其中仲裁庭通過指出“北京城建未在也門共和國主權領土范圍內行使中國政府職能”,強調了域外行使政府職能這一關鍵點。可以說,該裁決將可能為更多的中國國有企業進入ICSID中心提供了重要的先例。因此,國有企業應積極有效地利用這一機制以控制來自東道國的各種風險,維護正常的投資活動和國有資產價值。
2. 深化國有企業改革,認真對待和合理回應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的關切。
中國曾長期為外國直接投資的主要接受方,直到近些年來,隨著“走出去”戰略的深入開展,中國對外投資水平開始快速增長。隨之而來的是,美國等發達國家加強了對我國企業特別是國有企業的外資審查力度,并懷疑我國政府對國有企業在批準許可、政府采購和低成本的銀行融資方面實行了特別優惠的政策。因此,盡管美國主導的TPP已被新任總統特朗普推翻,但他秉持的“美國優先”的貿易保護主義政策,使得我們必須認真對待TPP中關于國有企業投資者的競爭中立條款。與將該條款視為發達國家控制國際貿易話語權的政策工具相比,筆者更愿意將其看作是為市場提供公平競爭的外部環境的高標準和原則。
事實上,自20世紀八十年代中國啟動國企改革以來,都旨在通過推動政企分開、政資分離等方式,探索厘清政府與市場邊界,為各種所有制企業在市場的公平競爭營造良好的制度環境。例如在“十二五”規劃中,中國政府指出:“要營造各種所有制經濟依法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公平參與市場競爭、同等受到法律保護的體制環境”。在2012年5月舉行的中美戰略經濟對話第四次會議上,中國承諾將“營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使各種所有制企業都能在信貸支持、稅收優惠和監管政策方面進行平等競爭、得到平等對待”。2015年8月,《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意見》提出了包括分類改革、完善現代企業制度和國資管理體制、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和強化監督防止國有資產流失等改革舉措。2015年11月,國務院發布了《關于改革和完善國有資產管理體制的若干意見》,作為《指導意見》的重要配套文件,其核心探索與國企平等參與市場競爭相適應的管理體制和機制,希望在政府、國資委、新增的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以及國企四級體系中,探索政企真實分離的可行路徑,真正確立國企的市場主體地位。總之,當前確定以管資本為主推進國企改革的政策,客觀上有助于淡化企業的所有制身份,明晰企業的職能和定位,為各種所有制企業在公平的市場競爭中創造良好的制度環境,這與TPP對國企的認定態度并不存在本質沖突。
與此同時,我們應警惕外資審查的政治化趨向。根據現有已公開的有關中美BIT談判資料來看,由于兩國的經濟發展水平不同,雙方在負面清單、環境標準、投資與投資者定義、國有企業、法律法規透明度等方面仍存在分歧。例如盡管美方將關鍵性的基礎設施、重要技術、國家安全等列入負面清單,但確切定義和范圍的缺失,外國投資委員會運作和審查過程透明度的不足,成為懸在中國國企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除了包括上述三個在內的負面清單外,中美兩國政府都應確保所有政策(包括市場準入和經濟激勵政策)的公平實施。在政府采購方面,除非有區別對待的理由,它們都應確保所有法人提供的產品和服務享受平等對待。
3. 掌握主動,明確合理的界定IITs中的“投資者”,積極構建利于國有企業發展的國際投資話語體系。
考慮到國有企業對經濟低迷的困難時期起到穩定作用,以及在促進工業轉型、產業升級和國家基礎設施建設等方面的功能,其改革注定是漸進式的。同時,隨著國有企業海外投資的快速增長,以及ICSID機制遭到一些國家的質疑,它們是否屬于IITs中涵蓋的投資者以及是否可以始終如一的訴諸ICSID仲裁等問題很可能會受到越來越多的審查和爭論。縱觀中國對外簽訂的IITs,我們發現雖然它們都未明確排除國有企業為合格的投資者*國有企業與投資者之間的關系大體分為三類:明確將國有企業納入投資者范疇如2011年中國-烏茲別克斯坦重新簽訂的BIT,2012年中國與日本、韓國簽訂的多邊投資協定,2012年中國-加拿大簽訂的BIT;締約雙方中一方的“投資者”定義包括了國有企業如中國-加納BIT,中國-卡塔爾BIT中,加納、卡塔爾一方的投資者明確包括國有企業;締約雙方的“投資者”定義都未提及國有企業如中國-秘魯BIT。,但若其不被明確納入,就有可能不被解釋為投資者。而ICSID公約對“國民”定義的有意留白,以及“Broches標準”未就國有企業是否能提起ICSID仲裁提供清晰的指導和無可爭議的結論,使得我國應認真反思并重新界定相關條款以進一步澄清和確保它們反映締約方的共同意圖。
而且,我國應充分利用區域全面經濟伙伴協定中的影響力,加快推進協定的簽署。由于該協定在對待國有企業方面不及TPP嚴格和全面,而美國的退出讓我國有機會填補美國缺位后產生的真空,主導地區貿易投資規則的制定。此外,針對目前對投資者-東道國爭端解決機制的批評如裁決缺乏一致性和可預見性、仲裁程序透明度不夠、仲裁員來源的單一化等,中國應抓住“一帶一路”倡議的歷史性機遇,真實了解區域內國家及其包括國有企業在內的投資者的現實需求,通過創新制定《“一帶一路”國際投資爭端解決機構公約》,依托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建立致力于區域內國際投資爭端解決的專門機構,公正高效地妥善處理區域內國際投資爭端。
五、 結 語
UNCTAD發布的《2017年世界投資報告》顯示,中國首次成為全球第二大對外投資國。隨著“走出去”戰略的深入實施,中國對外投資進入了高增長階段,其中國有企業功不可沒。可以預見的是,由于歐美等國投資保護主義的盛行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法制環境的不健全,中國國有企業在外資準入前和準入后都會面臨諸如國家安全審查、反壟斷審查或征收等更多的挑戰,其中核心是質疑國有企業的角色和定位。
盡管ICSID仲裁庭至今未有一起因國有企業不具備投資者地位而拒絕管轄的案例,但無論從條約解釋、Broches標準的法理研判抑或國際投資法的碎片化、國際投資仲裁的非約束性等方面考慮,該問題都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而TPP有關“國有企業”的獨立成章、中美BIT談判的艱難、歐盟投資法庭的創設都表明,中國國有企業要獲得有效的投資保護和身份認可,還需要吸收和借鑒競爭中立規則中的合理內容來推進自身的改革,以真正的“現代企業”或“私人投資者”身份參與國際經濟活動。從長遠來看,中國應以“一帶一路”倡議為契機,充分利用各種場合表達政府對國有企業改革的決心和毅力,并通過自身的經濟實力和談判技巧,完善和引導已簽訂或正在進行的雙邊或區域協定納入明確、合理的國有企業投資保護條款,主動為國有企業的國際經濟投資活動創設和發展規則。
參考文獻:
1. Australian Law Reform Commission. Foreign State Immunity.http://www.austlii.edu.au/au/other/lawreform/ALRC/1984/24.html. 2017-11-18.
2. Broches, A. World Bank, ICSID, and other Subjects of Public and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Dordrecht:MartinusNijho&Publishers, 1995.
3. Chazan, G.EU capitals seek stronger right of veto on Chinese takeovers.https://www.ft.com/content/8c4a2f70-f2d1-11e6-95ee-f14e55513608.2017-02-14.
4. Extractive Industries Transparency Initiative (EITI).Guidance on SOE participation in EITI reporting.https://eiti.org/document/guidance-note-on-soe-participation-in-eitireporting. 2017-10-15.
5. ICSID.Ceskoslovenska Obchodni Banka, A.S. v. The Slovak Republic, ICSID Case of Decision on Objections to Jurisdiction, No.ARB/97/4.http://www.italaw.com/sites/default/files/case-documents/ita0144.pdf. 2017-08-10.
6. ICSID.Aguas del Tunari,S.A. v. Republic of Bolivia, ICSID Case of Decision on jurisdiction,NO,ARB/02/3.http://www.iisd.org/pdf/2005/AdT_Decision-en.pdf. 2017-11-03.
7. ICSID.Burlington Resources,Inc. v. Republic of Ecuador, ICSID Case of Decision on Jurisdiction,No.ARB/08/05.http://ita.law.uvic.ca/documents/BurlingtonResourcesInc_v_Ecuador_Jurisdiction_Eng.pdf. 2017-12-10.
8. Karl,P.S., and S.Jonathan. State-Controlled Entities Control Nearly US $2 Trillion in Foreign Assets.ColumbiaFDIPerspectives,2014,10(1): 64.
9. Riddell,K. Middle Eastern firm’s deal to manage U.S. cargo port raises security concerns,http://www.washingtontimes.com/news/2014/jul/29/government-oks-arab-owned-company-operateus-port/. 2014-07-29.
10. Schreuer et al. The ICSID Convention: A Commentary.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09.
11. Shaw, M.N. International Law, 6th ed.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 2008.
12. Supreme Court of Canada.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v. The Public Service Alliance of Canada and others (Re Canada Labour Code) 2 S.C.R.50.http://scc-csc.lexum.com/scc-csc/scc-csc/en/item/ 880/index.do. 2017-11-25.
13. United States Court of Appeals,Fifth Circuit.de Sanchez v. Banco central de Nicaragua and Others,770 F.2d 1385.https://openjurist.org/770/f2d/1385/de-sanchez-v-banco-de-nicaragua-a. 2017-11-23.
14. World Bank. Report of the executive directors on the Convention on Settlement of Investment Disputes between States and Nationals of other States.http://icsid.worldbank.org/ICSID/ICSID/RulesMain.jsp. 2017-1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