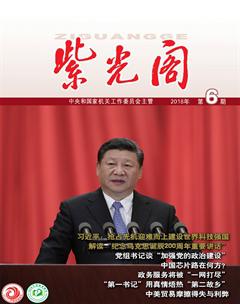中國芯片路在何方?
任鳴 張琦澤 裴季壯
中美貿易摩擦,讓中國的芯片在國人心頭掀起了波瀾。有人把中國的芯片產業說得一塌糊涂,有人慷慨激昂,似乎就要投入戰斗……
芯片,這個在智能化時代各行各業誰都離不開的小小“心臟”,我們泱泱大國究竟在世界排名第幾?現狀如何?怎樣才能趕上和超過那些國外的先進水平?帶著讀者的疑問,在中國半導體行業協會的大力支持下,我們請來了中國芯片產業的有關代表人物。5月29日下午北京長安街西側一幢高樓的會議室里,本刊記者靜靜地傾聽著這些業界專家的娓娓道來。
國防科技唱響國產爭氣歌
在與會人員的一致推薦下,首先發言的是中國半導體協會咨詢委副主任趙正平。他聲音洪亮地給我們講述了國防工業的科研人員們不懼國外壓力,讓中國的高新武器裝備不斷獲取國產芯片的奮斗經歷。
面對封鎖,無需驚慌失措。趙主任說的第一句話是:“中興事件,咱們用不著大驚小怪、人人白危!”他指出,在我國數十年的高科技武器裝備研發征程中,美國經常用芯片卡我們脖子。我國在軍用裝備領域已經與他們進行了多次正面交鋒,并且在斗爭中推動了我國芯片產業的迭代升級。
面對封鎖,必須超前部署。在集成電路研發領域,從新概念誕生到新產品完成產業化一般需要12年,這是國際公認的客觀規律。對此,趙正平反復呼吁:“我們作為追趕者,必須要在超前技術上進行超前部署,只有這樣才能盡量縮小差距、盡快突破壁壘。”“中興公司上一次遭遇禁運時,向美國、日本購買的氮化鎵器件均無法到貨,生產經營遭遇嚴重危機。關鍵時刻,我們用自主研發的器件幫助中興解了燃眉之急。”
面對封鎖,務必自主創新。趙正平表示,從歷史脈絡上看,中興事件的發生是必然的,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他語氣凝重地指出,中興事件給我們一個重要警示是:在微電子產業,除了要利用和依靠市場以外,還必須“留一手”——隨時準備用自主創新的力量應對市場變化。在長期斗爭中,軍事裝備研發機構不斷吸取教訓,一直把自主創新作為安身立命的根本。
他強調“國家在制定微電子發展戰略的時候,一定要牢記全球微電子產業發展規律。如果認識不到這一點,我們在戰略層面上就要吃大虧。”
正確認識芯片的應用價值及中國的現狀
刁石京,現任紫光集團聯席總裁,對中外芯片研發生產情況了如指掌。他明確指出,目前,在國際上擁有研發生產芯片體系的就有那么幾個國家和地區。我國在國際上已經接近第一梯隊,取得了不錯的成績。中國是工業產品生產大國,國際上70%的工業品產白中國。雖然我們進口了不少國外的芯片,但出口量也是最大的。
他還繪聲繪色地講述了參觀美國頁巖氣施工現場時,了解到芯片應用讓地下資源能便捷經濟地開發出來。他強調指出,人類的發展進步已經從體力拓展到智力,特別是隨著人工智能技術的突破,芯片將成為人工智能時代的必需品。由于其高科技、高投入、高回報、高風險、周期長的特性,集成電路體系已經成為國際競爭的決勝戰場。
他闡明:要辯證地看待目前中國芯片的發展現狀。因為在整個產業體系中企業是主體,要生存就只能從最接近市場、最容易切入的地方開始做,所以我們的產品集中在產業鏈中低端就不足為奇了。以前是跟隨式發展,但現在卻不能再只是跟隨了。隨著中國芯片業的成長壯大,我們正在向中高端發展。應該說,中美貿易摩擦引發的芯片問題是我們在不斷發展壯大中必然要出現的。
刁石京總裁的發言還對芯片產業鏈存在的問題做了系統的梳理,得到了與會專家的印證。中芯國際副總裁俞波道出自己的親身體驗:許多國人對芯片為何物不甚了解。中美貿易摩擦開始后,有些人提出的問題很是“小兒科”。其一不了解芯片的生產周期,認為只要有些“精神”,花個5年10年時間就能趕上別人。他認為芯片研究沒有長期的專注和堅持是不可能的,不能有彎道超車和人定勝天那些不切實際的想法。其二不了解芯片人才的特殊性,用國內現有的機制吸引人才是不可能的。其三不了解芯片行業研發特殊性的各地政府,正在草率地大干快上,到處撒胡椒面的風頭有正起傾向。
趕超世界先進水平雖然路長但在腳下
前來參會的企業家和有關專家,憑他們長期工作積累的經驗和教訓,提出了許多可貴的建議。概括起來有:
一是要集中資源,協調推進。現在工信部、發改委、科技部、財政部等部委都有資金支持芯片,但如何集中資源?如何協調推進?值得認真研究。要有全國“一盤棋”理念。有人提出要進一步發揮國家集成電路產業發展領導小組作用,系統謀劃統一指揮,推動全行業協調發展,要把地方的扶持、稅收優惠,加上中央層面的資金支持,瞄準一個方向形成合力。重點要在創建研發機制和市場應用機制上下功夫,強有力地推動以用促產,以產帶人,形成一個完整鏈條。科技部門要研究如何將端口前移,確定今后需要重點解決的問題。
二是要制定優惠政策鼓勵國內企業采用國產芯片。長電科技總監周健、燦芯半導體CEO吳漢明、華大九天副總經理吾立峰在發言中指出,如果國內企業能夠“信任”并大膽地使用國產芯片,中國芯片產業會發展得更好更快。他們期待相關政府部門盡快出臺這方面的政策。久而久之,我國的芯片產業體系就會協同發展起來。
三是要重視芯片基礎性工作。
首先是基礎人才的培養。中微半導體副總裁曹煉生談道,在美國的教育體系中,所有的大學除了完全純粹的文科大學以外,幾乎找不到一個學校沒有半導體專業、計算機專業、計算機工程專業,甚至幾乎所有的兩年制社區學校也設立計算機專業。就連成人教育和繼續教育也非常重視開設半導體專業,他們全方位培養出高端、中端和基礎人才。所以當硅谷形勢一好的時候,招聘的人擠得不得了,什么層次的人都能夠找到。人工智能技術將涉及社會的各行各業,芯片的研發生產及應用無不與人才培養的問題有關,這是個重要的基礎性工作。建議教育部要進行重點研究和規劃。
其次是基礎材料的創新研發。半導體材料支撐分會秘書長石瑛說:“芯片的制作其材料有8大類上千種,包括金屬材料、化工材料、高分子材料等等。”半導體制造材料也是各類材料當中最頂尖的部分,技術難度要求特別高,其生產管理和品質控制要求都非常高。在這個領域因為我們國家跟國際相比是后發展起來的,目前80%以上生產線用的材料都要依賴進口。中國科學院半導體研究所所長助理張韻談道,“要重點抓住芯片關鍵材料的源頭創新,從適應新一代芯片技術的發展趨勢出發,研究開發出部分性能可以超越硅材料的新型半導體材料,通過前瞻性布局,有可能使我國未來芯片技術產業的關鍵材料與芯片制備及應用水平接近世界前沿。”
四是要在人力財力上創新體制機制。
其一,在吸引人才和培養人才問題上,要出臺新政策。中芯國際副總裁俞波又談道,因為國內微電子學科至今仍不是大學一級學科,從而導致在該領域人才嚴重缺乏,大大滯后于產業的需求。國內高校培養出來的該領域學生十分有限,往往成了搶手貨。真正最需要大量人才的企業,往往因待遇、戶口、房子、子女教育等因素制約,長期面臨招人難、留人難的局面。他指出,我國現行的個稅制度極大制約對該領域國際人才的吸引力。美國、日本、韓國等個稅都低于我們,加上還可以進行各種抵扣,有的還有股權激勵,其實際收入非常可觀。而我國收入達到一定數量后個稅將高達45%,這么高的稅率相當于懲罰性稅收,其客觀作用是趕走人才。其結果是按照國際市場價格招攬不到人才,讓企業增加很大負擔而失去競爭優勢。建議在降低個人所得稅的同時,在集成電路領域試點專項中可特殊列支人員經費,以填補國家在該領域空白的產業化項目。
其二,在財力上要加大產業化研發支持力度。集成電路產業投資規模大,回收周期長。但隨著國家集成電路產業投資基金的成功設立和募資,這一問題得到了極大的緩解,但與此同時,集成電路工藝研發,特別是先進工藝研發投入巨大,已成為集成電路制造企業追趕世界先進水平的攔路虎。盡管國家設立了重大專項,但有限的資金往往被撒胡椒面了,龍頭骨干企業從中獲得的技術研發支持仍遠遠不足。
許多專家還談道:要解決產業發展資金成本高的問題。高投入、門檻高是集成電路產業的特點。在投資上我們有國家集成電路產業投資基金,但缺研發資金。因為研發企業投入最大,研發一個芯片可能就要耗資10億美元,沒有國家研發資金支持,單靠企業去研發根本不敢去做。另外,現在融資成本太高,國內資金成本為6%一8%,小企業可能要達到10%。比國外高得太多了。
四個多小時的研討會結束時,一些到會者還感到意猶未盡。我們認為,由于其研發高投入、高風險、周期長的特性,芯片研發和生產似乎也受各部門、各地方領導不正確“政績觀”的影響。有些部門、有些地區的領導嫌芯片的經濟效益短時見不到,也就不愿意多考慮了。
“長期關注和支持”一詞在許多專家、企業家的發言中被反復提到。在中國LED產業與應用聯盟秘書長關白玉的發言中,記者了解到南昌大學副校長教授江風益經過19年堅持研究發明我國獨有的硅襯底技術和制造工藝,孵化了2個公司,成功實現大規模生產的實例,我國的這項技術已經走在世界前列。
回眸以往,展望未來。芯片問題的出現,比起中國共產黨帶領人民歷經艱險從一個勝利走向另一個勝利的歷史征程來說,只是留給歷史的一個故事而已。
只要找準問題,把握規律,找到解決問題的方法和路徑,就能踏踏實實地走出新路。我們相信,中國芯片的發展進步,必將在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的歷史洪流中滾滾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