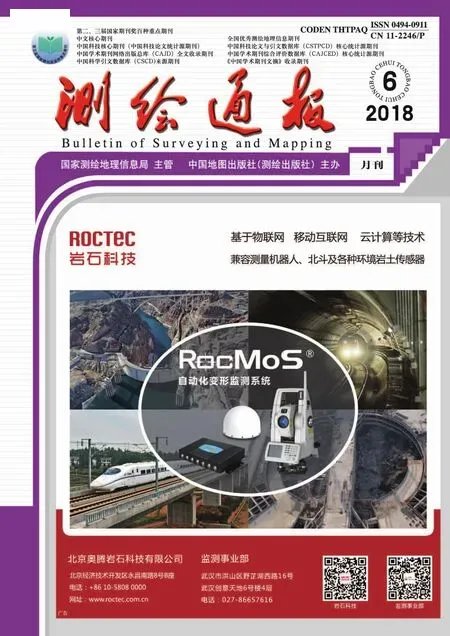GNSS技術下北京7·21暴雨水汽含量反演分析
李 森,賈光軍(1. 北京市測繪設計研究院,北京 100038; 2. 城市空間信息工程北京市重點實驗室,北京 100038)
2012年7月21—22日,中國大部分地區遭遇暴雨,尤其是北京及其周邊地區遭遇61年來最強暴雨,給北京地區帶來人員傷亡和巨大經濟損失。作為暴雨災害預警系統的技術支撐,強降水監測預報成為目前急需解決的技術問題[1-3]。20世紀90年代,國內外學者提出基于GNSS的大氣可降水量反演技術,通過與微波輻射計和探空探測大氣可降水量進行比較分析,認為該方法可用于探測大氣可降水量。隨著研究的深入,GNSS探測大氣可降水量的精度進一步提高,目前可達1.5 mm[4-5]。
本文利用北京市2012年7月18日至7月24日GNSS觀測數據,反演大氣可降水量,重點研究7·21暴雨前后北京地區大氣可降水量變化特征,并將GNSS反演大氣可降水量與NECP數據和無線電探空數據進行分析比較,驗證利用GNSS觀測數據反演大氣可降水量的正確性和可靠性。
1 GNSS反演大氣可降水量方法
1.1 基本原理
GNSS衛星發射的電磁波在到達接收機前要穿過大氣層,由于大氣中干空氣、電子濃度、水汽等物質的存在導致無線電信號產生延遲,這種時間上的延遲等價于傳播路徑的增長,從而導致GNSS定位誤差。20世紀90年代,有學者提出利用GNSS接收機接收到的無線電信號反算出大氣中的電子密度、水汽含量等[6-7]。
GNSS信號延遲表現為兩個方面:一是GNSS傳播路徑由直線變為彎曲;二是與電磁波在真空中的傳播速度相比,電磁波傳播速度減慢。這種延遲是由于傳播路徑上大氣折射指數的變化引起的,而折射率指數變化與大氣的溫度、壓力、濕度等大氣狀態相關[8-9]。
Thary提出的電磁波折射率指數表達式為
(1)

(2)
將式(1)代入式(2)可以得到天頂總延遲

ΔLzd+ΔLzw+ΔLze
(3)
式中,ΔLd、ΔLw、ΔLe分別表示大氣干延遲、大氣濕延遲、電離層延遲。由于通常情況下無法得知大氣的Pd、Pw和T的空間分布,因此,Davis將狀態方程引入,即
(4)
式中,Rd和Rw分別為干空氣比氣體常數和水汽比氣體常數。同時,干延遲使用流體靜力學代替,可得
ΔLs=ΔLzh+ΔLzw+ΔLze
(5)
(6)
1.2 大氣可降水量(PWV)獲取
公式如下
引入社會化專業分工優勢,整合社會上優秀的IT資源,將IT運維管理部門的工作定位從親力親為、以基礎事務為主的運行維護模式,轉變為以引領、評估、改善、提高、發展為主線的工作定位及與之相適應的管理模式。將基礎、重復、競爭性運維事務工作交由專業化公司來做,以最快地獲取專業化支持能力,推動和實現IT支持環境的標準化、規范化管理。借助專業服務,在提高工作效率的同時更好地管理IT成本,在提升業務部門對于IT支持滿意度的同時,為管理部門開辟新的空間從事更有價值、更有利于發展的事務,使管理部門在事業發展中的定位更準確,作用更突出。
ΔLzw=ΔLz-ΔLzd-ΔLze=
(7)
令Tm為垂直方向氣壓的加權平均溫度,得
(8)
則式(6)中的濕延遲
(9)
因此,大氣可降水量(PWV)為單位面積上垂直空氣柱內水汽全部轉化為降水時的降水量高度
PWV=∏ ΔLzw
(10)
(11)
1.3 反演流程
大氣可降水量反演是精密GNSS數據處理的附屬產品,GNSS解算過程中精密星歷、精密鐘差等數據的選擇直接決定了大氣可降水量反演精度。GNSS監測網基線長度從幾十千米到上千千米不等,數據處理時必須顧及各種攝動力、固體潮、海潮、電離層延遲和對流層延遲等誤差對計算天頂延遲的影響,同時采用精密GNSS數據處理軟件,才能獲取準確的大氣可降水量[10-12]。
本文數據處理采用IGS事后精密星歷文件(SP3文件)、衛星信息文件、、衛星軌道文件、地球自轉參數文件、天線相位中心改正文件等相關數據文件,使用GAMIT軟件進行基線解算,獲得單天時間間隔15 s的天頂總延遲,并根據GNSS監測站采集的氣象數據,提取監測站上空大氣可降水量。
2 北京7·21暴雨前后大氣可降水量分析
2.1 數據處理
利用北京及其周邊的9個國際IGS站(BJFS、BJNM、CHAN、DEAJ、GUAO、LHAZ、TNML、ULAB和WUHN)的GNSS觀測數據進行數據處理,選取2012年 7月18日至24日連續7 d的GNSS觀測數據(O文件)和氣象觀測數據(M文件)。GNSS數據處理采用GAMIT軟件,衛星星歷選擇精密星歷,每15 min估算一次大氣可降水量(PWV),獲得測站的可降水量的時間序列。
2.2 可降水量與北京7·21暴雨演變分析
根據9個國際IGS站分布情況,選取BJFS、GUAO、WUHN、ULAB和DEAJ 5個IGS站,分析2012年7月18—24日大氣可降水量的變化特征,圖1為BJFS、GUAO、WUHN、ULAB、DEAJ可降水量變化特征圖。重點分析了位于北京西南山區的BJFS站和位于北京中心城區的BJNM站,并比較兩個測站可降水量的微小變化。圖2為BJFS站和BJNM站可降水量比較,圖3為BJFS站可降水量中誤差。
通過對圖1—圖3 GNSS反演7·21暴雨前后大氣可降水量時間序列的變化特征的分析,可以發現:①北京7·21暴雨的前幾天大氣中的可降水量已經非常高,與武漢的大氣中可降水量相當,遠遠高于新疆和烏蘭巴托;②北京7·21暴雨當天大氣中的可降水量急劇上升,在短時間內迅速到達峰值,升幅大,這是暴雨形成的趨勢;③隨著暴雨的減弱,大氣中可降水量逐漸減少,暴雨過后可降水量又急劇下降,回歸到北方地區正常水平;④雖然BJFS站和BJNM站均位于北京市域內,但是兩個監測站反演得到的大氣可降水量也存在一定的差異性,尤其在7·21暴雨當天可降水量峰值區域,位于北京西南部房山區的BJFS站獲得可降水量略高于位于北京北三環海淀區的BJNM站,這一結果與氣象部門公布的當天北京市實際降水量也是一致的。

圖1 BJFS、GUAO、WUHN、ULAB和DAEJ站可降水量

圖2 BJFS站和BJNM站可降水量比較

圖3 BJFS站可降水量中誤差
3 精度檢驗
3.1 GNSS反演結果與NECP資料比較
NCEP全球再分析資料是美國國家環境預測中心(NCEP)和國家大氣研究中心(NCAR)合作建立起的資料庫。本文使用的NCEP再分析場網格資料經緯度的格距大小都是2.5°,時間分辨率為6 h,時間段選取2012年度,通過內插方法得到北京地區整層大氣可降水量NCEP/PWV[7]。
圖4為北京7·21暴雨前后大氣可降水量的GNSS反演結果與NCEP數據的比較,通過比較發現:GNSS反演結果與NCEP數據保持相同的趨勢,利用皮爾遜積矩相關系數計算公式得到二者的相關系數為0.953,表明二者具有較強的相關性;雖然GNSS反演結果與NCEP數據保持相同的趨勢,但是兩者差別較大,平均誤差達到13.38 mm,且NCEP數據均低于GNSS反演結果,存在系統性的偏差。

圖4 GNSS反演結果與NCEP數據比較
3.2 GNSS反演結果與無線電探空資料比較分析
北京無線電大氣探測站(ZBAA)是為研究大氣科學在全球設立的大氣探測站,大氣探測站UTC時間每日0點和12點分別進行一次無線電大氣探測。通過無線電探空儀可以準確探測大氣不同高度的氣壓、溫度、可降水量等數據。無線電探空儀是氣象部門常用的大氣數據探測方法,精度較高,常用作新方法的檢驗標準[13-15]。表1為北京7·21暴雨前后利用GNSS觀測數據反演得到的大氣可降水量與北京無線電大氣探測結果的比較。

表1 北京7·21暴雨前后可降水量變化比較
由表1可以看出除7月21日12:00外,利用GNSS觀測數據反演得到的大氣可降水量與北京無線電探測結果基本一致,誤差算術平均值為1.94 mm。通過分析發現7月21日12:00,較差偏差較大原因為本次無線電探測高度沒有達到設計高度40 000 m,探測高度僅有20 026 m。
圖5為2012年7月1日至7月31日,利用GNSS觀測數據反演得到的大氣可降水量與北京無線電探測結果比較圖(剔除部分由探測高度較低導致探測結果偏差較大的數據)。通過對圖5進行分析,并根據皮爾遜積矩相關系數計算公式,得到兩者相關系數為0.971 6,GNSS反演結果與無線電大氣探測站探測結果保持高度的一致性。雖然兩種方式獲得的大氣可降水量存在高度一致性,但是GNSS反演結果普遍略高于無線電大氣探測站探測結果。通過分析認為導致微小偏差的原因有兩個:一是BJFS站和北京無線電大氣探測站雖然都位于北京市域范圍,但相距50 km,氣象條件存在一定的差異性;二是GNSS衛星軌道較高,GNSS穿過的大氣層長度遠大于無線電大氣探測站所探測的高度。

圖5 GNSS反演結果與探空數據比較
4 結 論
本文通過對選取的9個IGS站GNSS觀測數據進行數據處理,獲取了測站大氣可降水量時間序列,并重點分析了BJFS站和BJNM站在7·21暴雨前后大氣可降水量的分布特征,同時將GNSS反演結果與NECP資料和無線電探空資料進行比較,得到以下結論:
(1) 北京7·21暴雨的前幾天大氣中的可降水量已經較大,7·21暴雨當天大氣中的可降水量急劇上升,在短時間內迅速到達峰值。隨著暴雨的減弱,大氣中可降水量逐漸減少,暴雨過后可降水量又急劇下降,回歸到正常水平。
(2) 雖然BJFS站和BJNM站均位于北京市域內,但是兩個監測站反演得到的可降水量也存在一定的差異性,這是因為BJFS站位于7·21暴雨中心區域北京房山區,而BJNM站位于北京市區中心區域,降水量相對弱一些。
(3) GNSS反演結果與北京無線電大氣探測站實際探測結果吻合較高,與NECP資料吻合度相對較弱,這是因為NECP資料是通過多期觀測資料進行內插再分析獲取的,現實性較差。
(4) GNSS反演結果普遍大于無線電探測站實際探測結果,這是因為GNSS衛星軌道較高(基本在2萬千米以上),GNSS穿過的大氣層長度遠大于無線電探測站所探測的高度。
(5) 雖然GNSS反演結果與無線電探測站實際探測結果保持高度的一致性,但是實際降水的形成是一個復雜的過程,并且小的降水具有較大的隨機性,與大氣中可降水量的多少相關性較弱,因此大氣中可降水量與實際降水的多少還需要進一步深入研究。
參考文獻:
[1] 劉嚴萍,張飛漣,孫曉.地基GPS可降水量用于2011年北京暴雨監測[J].大地測量與地球動力學,2013,33(2):63-66.
[2] 羅夢森,曾明劍,景元書,等.GPS反演的大氣可降水量變化特征及其與降水的關系研究[J].氣象科學,2013,33(4):418-423.
[3] 朱男男,沈桐立,朱偉軍.一次降水過程的GPS可降水量資料同化試驗[J].南京氣象學院學報,2008,31(1):26-32.
[4] ROCKEN C,HOVE T,JOHNSON J,et al.GPS/STORM—GPS Sensing of Atmospheric Water Vapor for Meteorology [J].Journal of Atmospheric & Oceanic Technology,2009,12(3):468-478.
[5] 王小亞,朱文耀,嚴豪健,等.地面GPS探測大氣可降水量的初步結果[J].大氣科學,1999,23(5):605-612.
[6] 于勝杰,萬蓉,付志康.氣壓對GPS大氣可降水量解算的影響分析[J].大地測量與地球動力學,2013,33(2):87-91.
[7] 杜明斌,尹球,劉敏,等.地基GPS/MET探測水汽等相關參數精度分析[J].大氣與環境光學學報,2013,8(2):138-145.
[8] 陳俊勇.地基GPS遙感大氣水汽含量的誤差分析[J].測繪學報,1998,27(2):113-118.
[9] 劉旭春,王艷秋,張正祿.利用GPS技術遙感哈爾濱地區大氣可降水量的分析[J].測繪通報,2006(2):10-12.
[10] 丁繼新,成英燕,王權,等.利用GPS技術遙感大氣對流層水汽含量的研究[J].測繪科學,2002,27 (2):16-19.
[11] 劉旭春,張正祿,張鵬,等.GPS反演大氣綜合水汽含量的影響因素分析[J].測繪科學,2007,32 (2):21-23.
[12] 郭潔,李國平,黃文詩,等.不同類型降雨過程中GPS可降水量的特征分析[J].水科學進展,2009,20(6):763-768.
[13] 劉旭春,王艷秋,張正祿.利用GPS技術遙感哈爾濱地區大氣可降水量的分析[J].測繪通報,2006(4):10-12.
[14] 李慧,閆偉,王倩倩.地基GPS觀測在水汽監測中的應用[J].華北水利水電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2014,35(2):89-92.
[15] 楊玲,李博峰,樓立志.不同對流層模型對GPS定位結果的影響[J].測繪通報,2009(4):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