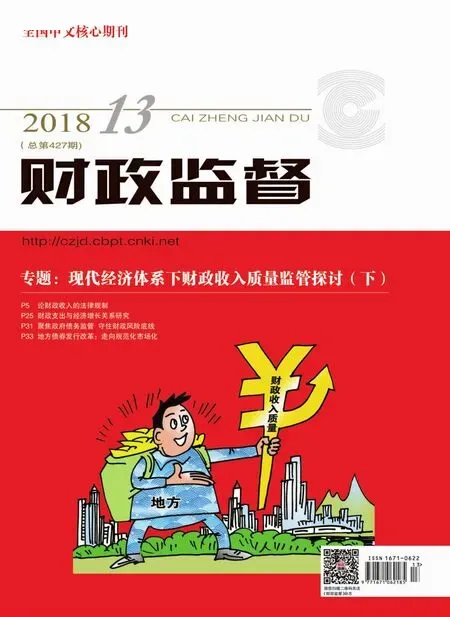財政支出與經濟增長關系研究
———基于廣東省廣州市1978—2016年的實證分析
●林 江 王瓊瓊 姚翠齊

林江,現任中山大學嶺南學院經濟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山大學自貿區綜合研究院副院長;中山大學港澳珠江三角洲研究中心副主任。曾任嶺南學院金融系教授、中山大學港澳研究所所長、港澳研究中心副主任;曾由中山大學借調香港招商局集團工作,先后任研究部研究員、金融中心副總經理、金融事業部副總經理、集團下屬上市企業、銀行和保險公司的執行董事,香港中國企業協會咨詢服務部副主任等職務。兼任中國財政學會理事、全國臺灣研究會理事、教育部高等學校財政學類專業教學指導委員會委員、海峽兩岸關系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廣東省財政學會副會長、廣東省國際稅收研究會副會長、廣東政府采購協會顧問、廣東省稅務學會理事兼學術委員、廣州市財政專家咨詢委員會專家委員、廣州市人大預算委員會專家等職。
林江在財政理論與政策、區域經濟與金融、風險投資領域有多年的研究經驗,在國內著名學術期刊上發表文章數十篇。發表論文的學術期刊包括《財政研究》《稅務研究》《世界經濟》《財貿經濟》《學術研究》《國際金融研究》。他還出版了 《財政學》、《稅收學》、《港元穩定機制研究》、《風險投資》等學術專著和教材。曾承擔國家社會科學基金、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重大科研項目、科技部和農業部的重點研究課題以及廣東省政府以及多個地方政府和企業委托研究課題。近年來應邀赴美國、意大利、澳大利亞、日本、香港、臺灣、澳門等國家和地區進行學術訪問、講學或參加學術會議。
林江致力于為政府和企業提供研究和咨詢服務,受聘為多個地方政府的顧問、特約研究員以及多個企業的董事、獨立董事、顧問職務;曾獲“2010年度東莞十大經濟人物”稱號。
林江經常接受境內外主流媒體的采訪,就中國的財稅體制改革、區域經濟和金融發展、產業升級和企業轉型等問題發表看法,這些媒體包括:中央電視臺、鳳凰衛視、無線電視、亞洲電視、有線電視、澳亞衛視、廣東電視臺、廣州電視臺、廣東電臺、廣州電臺、新華通訊社、中國新聞社、南方日報、羊城晚報、廣州日報、香港文匯報、香港大公報、美國紐約時報、英國金融時報、日本經濟新聞、加拿大環球郵報等。
一、引言
改革開放四十年,廣東取得一個又一個歷史性的突破。2017年,廣東全年地區生產總值接近9萬億大關,同比增長7.5%,占全國GDP的10.5%。廣東GDP總量自1989年開始已經連續29年位居全國大陸地區第一位,2017年的GDP總量甚至直逼在世界經濟排名第11位的韓國。同樣的,廣東財政從1992年開始就穩居全國財政的排頭兵地位,財政收入的增長也是可持續的,2017年,廣東省財政收入已經達到11315.21億元,是全國唯一一個財政收入進入萬億元級別的省份。廣州市作為廣東省的省會城市,其發展是令人矚目的。
廣州,作為廣東省省會城市和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敢為人先,先行先試,助力廣東成為全國第一經濟大省和財政大省,自身的財政發展和經濟增長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2017年廣州GDP總量突破2萬億,增長7%,成為全國第四個突破2萬億的城市;2017年廣州財政收入1533億,增長10%,財政收入在全國城市排在第8位。與此同時,廣州財政支出也一直在增加,2017年發布的《廣州市財政改革與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指出,“十三五”期間廣州全市一般公共預算支出9500億元。2018年1月召開的廣州市委十一屆四次全會更是為新時代的廣州描繪了更加宏偉的藍圖,“面向2020年,要高質量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建設實力廣州、活力廣州、魅力廣州、幸福廣州、美麗廣州;展望2035年,要奮力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先行區;到本世紀中葉,全面建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引領型全球城市”。實現高質量發展成為新時代廣州的必然選擇,而高質量高水平的發展離不開廣州財政支出的有力支持。在此背景下,探討廣州財政支出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就顯得十分迫切。
財政支出與經濟增長間的關系,一直是學術界研究的重要內容。大部分的研究都認為財政支出對經濟增長有促進作用。但是具體到財政支出的具體項目,在財政支出結構與經濟增長間的關系上,學術界仍存在爭議。國外研究中,有學者將財政支出分為生產性財政支出(投資性支出)和非生產性財政支出(消費性支出),他們的研究認為二者對經濟增長的作用不同,生產性財政支出的確可以促進經濟增長,但生產性支出并不一定越多越好,存在一個最優狀態,如果生產性支出比例過高,對經濟增長的邊際效應反而變為負的,從而阻礙了經濟增長(Devarajan,Swaroop,Zou,1996)。進一步地,眾多學者又將財政支出細分為公共支出、基礎設施投資支出、教育支出、國防支出、醫療衛生支出等,對不同國家不同地區不同內容的財政支出與經濟增長間關系進行了豐富的研究,結論也不盡相同。
國內諸多學者對國內財政支出和經濟增長間的關系也進行了研究。莊子銀、鄒薇(2003)對1980—1999年中國財政支出的總量及結構與GDP間的關聯進行了計量分析,其認為在政府財政支出不斷增加的過程中,由于“調整成本”(含與公共支出相關的安裝和調配成本、尋租和“非生產性尋利”造成的社會福利損失)的存在以及“調整成本”的增加,對經濟增長存在負作用。張明喜、陳志勇(2005)對改革開放后1978—2003年的財政支出和經濟增長數據利用最小二乘法估計得出,我國財政支出對經濟增長有促進作用,未來仍應加大財政投入。彭志文、郭路(2011)從居民福利最大化角度沿用 Romer(1990)的分析框架對財政支出結構進行理論分析,認為財政支出存在一種最優結構,不同支出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不同,相比于科教領域的支出,政府在公共資本領域的投入更能促進經濟增長。唐小鵬、孫靜、趙彬和戴東陽(2011)利用VAR模型對1952—2008年我國政府財政開支中的國防支出、科教文衛支出和政府行政管理支出等三種具有非生產性特征的財政支出進行分析,研究發現,中國國防開支并不會損害經濟增長,反而對經濟增長具有積極作用,應當適當增加國防開支。石奇、孔群喜(2012)對中國1979—2008年生產性公共支出以及三次產業國內生產總值的研究發現,對生產性領域投入的增加有利于優化資源配置,從而促進經濟增長。陳高、王朝才(2014)對中國1990—2012年的省級財政支出數據進行研究,認為中國各地區的財政支出對經濟增長都有促進作用,但是不同地區的促進作用有所不同,建議政府因地制宜地采用差異化財政支出政策。潘文卿、范慶泉和周縣華(2015)通過構建一個包含兩種政府財政支出的內生增長模型,對中國2000—2012年的縣級和地市級財政支出數據分別進行回歸分析,研究發現中國政府支出中的消費性財政支出與經濟增長間存在倒“U”型關系。
由此可見,國內外關于財政支出與經濟增長間關系的研究非常豐富,雖然因為研究對象、數據以及分類標準的不同,得出了不同的結論,但對本文的研究仍然具有積極的指導意義。從這些研究中,可以看出政府財政支出對于經濟增長來說,并不是一個簡單的外生變量,公共財政支出對經濟增長的具體作用仍有待于進一步研究挖掘。以往研究多集中在國家層面和省級層面,本文將研究對象定格到市級層面,以廣州市為例,在國內外研究的基礎上,對廣州市財政支出與經濟增長間的關系進行深入探討,并在此基礎上,結合廣州市高質量發展的要求,對廣州財政如何支持廣州經濟高質量發展、如何更好地服務于人民和企業,給出了相關的政策建議。
二、改革開放以來廣州市財政收支與經濟增長
改革開放以來,從總量上來說,廣州地區生產總值和財政收支總量逐年攀升,屢創新高,呈現不斷增長的態勢;從相對量來說,廣州財政支出占GDP的比重維持在6.3%和10.9%之間;從財政支出結構上來說,近40年也發生了比較大的改變,經歷了數次調整,財政支出結構統計口徑有所變動,數據在連貫性上存在一定的缺陷與不足,2007年前后數據難以從具體支出類進行比較。
(一)改革開放以來廣州地區生產總值規模
改革開放以來,按可比價格計算,廣州市GDP總量1979—2016年平均每年增長13.3%①,從1978年的43.09億元,以年均13.3%的增長率達到了2016年的19547.44億元,2017年GDP總量已經突破2萬億。由圖1可知,廣州市人均GDP的增長態勢與廣州市GDP總量的增長態勢十分相似,2016年的廣州市人均GDP達到141933元,是1978年907元的156倍多。

圖1 廣州市歷年(1978-2016)GDP總量(億元)和人均GDP(元)
(二)改革開放以來廣州一般公共預算收支②規模

圖2 廣州市歷年(1978—2016)一般公共預算收支規模(億元)
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廣州市財政收入和財政支出都得到了巨大的發展。由圖2中廣州市歷年一般公共預算收支規模可見,1978—1993年期間,廣州市一般公共預算收入持續穩定增長,并且一般公共預算收入一直多于一般公共預算支出,處于財政收支盈余的狀態;1994年分稅制實施之后,廣州一般公共預算收入的增長落后于一般公共預算支出的增長,一般公共預算支出在1994年開始高于一般公共預算收入,這種狀態維持至今。這一方面是由于分稅制對廣州財政收入產生了一定的沖擊,另一方面是因為深化改革開放的需要,廣州市加大了各個領域的財政支出。
(三)改革開放以來廣州一般公共預算支出占GDP的比重變化

圖3 廣州市歷年(1978-2016)一般公共預算支出占GDP的比重(%)
改革開放以來,廣州市一般公共預算支出占GDP的比重維持在6.3%和10.9%之間。其中,1986年廣州市一般公共預算支出占GDP的10.91%,是近年來的最高比例;1992年廣州市一般公共預算支出占GDP的6.31%,是近年來的最低比例;1995年以來,廣州市一般公共預算支出占GDP的比重一直在8%以上。
(四)2007年以來廣州市一般公共預算支出結構變化
2007年之前,廣州市財政支出分為一般預算支出和基金預算支出。一般預算支出又分為基本建設支出、企業挖潛改造資金、科技三項費用、流動資金、支援農村生產支出、農業綜合開發支出、農林水利氣象等部門的事業費、工業交通等部門的事業費、文體廣播事業費、教育事業費、科學事業費、衛生經費、稅務等部門的事業費、撫恤和社會福利救濟費、行政事業單位離退休經費、社會保障補助支出、行政管理費、公檢法司支出、城市維護費、政策性補貼支出、專項支出以及其他支出等。2007年,為了與國際接軌,我國對政府預算科目進行了改革,突出了小政府、大服務的市場經濟理念。由于統計口徑的改變,使得2007年前后的財政支出分類數據難以比較,數據間連貫性受損。學術界對一般公共預算支出結構的分類也并不統一,如陳天祥、趙慧(2016))將財政支出分為經濟建設性支出、社會服務性支出和維持性支出,還有其他學者將財政支出分為生產性支出和非生產性支出。但是,2007年之前的一般公共預算支出結構中有生產性屬性強的基本建設支出,2007年之后該項支出被分解到多種具體支出中,難以準確區分每項支出是否屬于生產性支出,且與之前年份的基本建設支出數據也不再具有可比性。因此,我們按照《廣州統計年鑒》中關于財政支出的分類,篩選出2007年之后均有連續性記錄的11類支出,描述性分析2007年至2016年廣州市一般公共預算支出結構變化情況,如圖4。

圖4 廣州市歷年(2007-2016)一般公共預算支出結構占比(%)
1、一般公共服務支出。廣州市一般公共服務支出在2007-2016年間占一般預算支出的比例在7.19%和14.72%之間,近年來呈現下降的趨勢。
2、國防支出。國防支出主要由中央和省一級財政提供,市一級承擔較少,2007-2016年廣州市國防支出占其一般預算支出的比例在0.07%和0.18%之間,與其他支出相比,該類支出最少。
3、公共安全支出。2007—2016年廣州市公共安全支出呈減少態勢,自2011年始,基本維持在8%左右,在所有支出中基本處于中等水平。
4、教育支出。廣州市一般預算支出中用于教育的支出比較高,且有繼續增加的態勢,近幾年占比均高于15%。
5、科學技術支出。2007-2016年廣州市科學技術支出占比雖然不高,但一直呈現增加的態勢,已由之前約3%的占比增加至2016年的5.81%,體現出廣州市對科技投入力度的不斷加大。
6、文化體育與傳媒支出。廣州市文化體育與傳媒支出占比在2010年達到最高值5.37%,之后開始減少,近幾年占比不足2%,處于一個相對穩定的較低的水平。
7、社會保障和就業支出。2012年廣州市社會保障和就業支出占比較低,為9.41%。其余年份,廣州市社會保障和就業支出占比基本在10%和13%之間。
8、醫療衛生與計劃生育支出。2007—2016年廣州市醫療衛生與計劃生育支出占比呈現不斷提高的態勢,已經由2007年的5.26%提升至2016年的8.95%。
9、城鄉社區支出。2007—2016年廣州市城鄉社區支出占比波動幅度比較大,2009年和2010年均低于10%,占比分別是7.99%和9.46%;其余年份占比均高于10%,2012年以來占比基本高于15%,2016年占比達到18.75%。總的來說,城鄉社區支出在所有支出中占比較高,且有繼續增加的態勢。
10、農林水事務支出。廣州市農林水事務支出占比在2.67%和5.32%之間,變化不大,近幾年維持在4%左右。
11、交通運輸支出。2007—2016年廣州市交通運輸支出占比與農林水事務支出占比變化態勢接近,近些年維持在5%左右,變化幅度不大。
12、其他支出。一般預算支出中除去圖4中列舉的11類支出,剩余的支出我們均歸入其他支出。其他支出占比在11.66%和23.17%之間,變化比較大,近年其他支出占比呈減少的態勢。
以上對改革開放以來廣州市經濟增長和財政支出規模以及2007年以來廣州財政支出結構變化情況做了比較詳細的分析,認為廣州市財政收支和GDP都取得了顯著的增長,財政支出結構也在不斷調整。接下來筆者將利用VAR模型,深入探討一般預算支出規模的變化與經濟增長之間的相互作用。
三、財政支出與經濟增長關系實證分析
本部分參照以往關于財政支出與經濟增長間的研究,利用VAR模型對改革開放以來廣州市1978年—2016年的財政支出規模與經濟增長間關系進行實證研究。
被解釋變量:地區生產總值(GDP),衡量的是經濟增長。
解釋變量:一般預算支出(PGE),衡量的是財政支出規模。
數據來源:本文中一般預算支出和經濟增長原始數據全部來自于歷年《廣州統計年鑒》。
數據處理:為了消除異方差和時間序列平穩性的需求,本文中變量均取自然對數,分別記為lngdp和lnpge,時間序列樣本量為39。
實證方法:本文采用Sims(1980)提出的向量自回歸(VAR)方法,這種方法可以將多種時間序列變量作為一個系統考察變量間的關系。
(一)平穩性檢驗
VAR模型要求變量的時間序列是平穩的,因此首先檢驗變量的平穩性。如圖5所示,取對數后的廣州市一般預算支出規模和國民生產總值具有明顯的時間趨勢,說明lngdp和lnpge是不平穩的。運用單位根檢驗最常用的檢驗方法ADF檢驗,我們發現無論是否選擇帶有常數項和時間趨勢項的ADF檢驗都不能拒絕lngdp和lnpge有單位根的原假設;進一步地,筆者對變量lngdp和lnpge做差分處理,同樣做單位根檢驗,結果發現無論是否選擇帶有常數項和時間趨勢項的ADF檢驗都拒絕了dlngdp(GDP增量)和dlnpge(財政支出增量)有單位根的原假設,說明差分后的時間序列變量dlngdp和dlnpge是平穩的,不再具有明顯的時間趨勢。因此,變量lngdp和lnpge均為I(1)序列。基于此,本文構建了一個含有變量dlngdp和dlnpge的二元VAR模型。

圖5 廣州市一般預算支出規模和國民生產總值的時間趨勢
(二)VAR 的估計
估計VAR之前,需要根據信息準則確定VAR模型的階數,選擇的階數必須保證擾動項為白噪聲。不同信息準則所選擇的滯后階數有時存在不一致的情況,這時選擇過低的階數可能過于簡潔,過高的階數又會損失較多的樣本量。本文中,FPE準則、AIC準則、HQIC準則、SBIC準則均選擇滯后1階,選擇結果一致。
接下來將估計1階的VAR(1)模型。模型回歸結果顯示③,兩變量間的回歸系數皆具有1%的顯著性水平,模型整體的擬合優度在0.34以上,且整體顯著,說明模型較好地擬合了真實數據。進一步地,對VAR(1)模型回歸后的各種性質和假設進行檢驗。檢驗結果認為VAR(1)模型的擾動項為白噪聲,且服從正態分布;所有特征值均在單位圓之內,VAR系統是穩定的;無論是單一方程,還是兩個方程的整體的Wald檢驗都是顯著的,方程間具有聯合顯著性。
(三)格蘭杰因果檢驗

表1 格蘭杰(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
格蘭杰因果檢驗可以幫助判斷一般預算支出與經濟增長間的因果關系。由表1格蘭杰因果檢驗結果可見,GDP增量的增加可以促進財政支出增量的增加,反過來,如果大幅度增加財政支出,也可以促進經濟的增長。因此,廣州市財政支出政策對經濟增長具有顯著的調節作用,可以通過調整財政支出政策促使經濟實現高質量增長。
(四)脈沖響應函數
估計VAR后,建立脈沖文件,并畫出正交化的脈沖響應圖,如圖6,刻畫一個內生變量的沖擊給其他變量帶來的影響。正交化脈沖響應圖6中包含4個小圖,每個圖的標題依次為irfname(脈沖結果,此處命名為gp)、impulsevariable(脈沖變量)以及responsevariable(響應變量)。比如第一行的兩個小圖均以dlngdp為脈沖變量,分別描繪了dlngdp對dlngdp和dlnpge的動態效應。從第一行可以看出,GDP增量的變化對GDP增量和財政支出增量都有明顯的影響,GDP增量的增加會提高GDP增量和財政支出增量,但是這種變化只存在于較短期,在長期中這種正影響逐漸消失。第二行的兩個小圖均以dlnpge為脈沖變量,分別描繪dlnpge對dlngdp和dlnpge的動態效應。從第二行可以看出,財政支出增量的增加會短暫地減少GDP增量和財政支出增量,但這種沖擊的負向影響短期內會消失。從脈沖響應圖可以看出,廣州市改革開放四十年來,財政支出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不如經濟增長對財政支出的拉動作用大。

圖6 正交化脈沖響應圖
(五)預測方差分解
VAR模型的作用之一是可以對變量進行預測,預測方差分解方法可以分析每個沖擊對各個變量的貢獻度,進而評價每個沖擊的重要性。由圖7的預測方差分解圖結合預測方差分解表(此處未列出)可以得出如下結論:
(1)對GDP增量進行向前一年的預測,其預測方差完全來自于GDP增量本身,即使向前做20期的預測,其93.4%的預測誤差仍來自于GDP增量本身,只有6.6%來自于財政支出增量。這說明,無論長期還是短期來看,財政支出增量的沖擊對其影響均較小,GDP增量的變化主要受自身沖擊的影響。
(2)對財政支出增量進行向前1年的預測,其預測方差9.4%來自于GDP增量,90.6%來自于自身,但是向前做20期的預測,35.3%來自于GDP增量,64.7%來自于自身。說明財政支出增量的變化短期來看受自身沖擊影響較大,長期來看受GDP增量沖擊的影響變大。

圖7 所有變量的預測方差分解圖
四、結論與建議
本文立足于改革開放四十年間財政支出與經濟增長的關系研究,以廣州市為例,利用VAR模型深入探討了二者之間的關系。研究認為,廣州市財政支出與經濟增長互為格蘭杰因果關系,經濟增長可以促進財政支出的增長,財政支出的增加也可以促進經濟的增長,但是這種促進作用稍微弱些,這可能是因為財政支出結構中不同類型的支出對經濟增長的作用不相同,存在作用抵消的可能。遺憾的是,囿于統計口徑的變化,造成2007年前后的財政支出結構數據難以比較,進而無法對改革開放四十年來財政支出結構與經濟增長間的關系進行深入研究,這是本文研究最大的不足之處。
但是,本文研究確實發現財政支出會對經濟增長產生影響,財政支出政策的變動也會對經濟產生影響。新時代下廣州探索經濟高質量發展新路徑,奮力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先行區,離不開新經濟業態的支撐,離不開高新技術產業的引領,離不開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實施,在這方方面面更離不開財政的大力支持。因此,未來的發展中,廣州市政府部門需要進一步擴大財政支出規模和優化財政支出結構,合理運用財政支出政策對經濟發展進行調節和引導,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更好地服務于人民群眾和廣大企業。■
注釋:
①數據來源:廣州統計年鑒2017。
②財政收支中包含一般公共預算收支和基金收支,本文中僅分析一般預算收支,以此代指財政收支。
③文中未詳細匯報VAR的回歸系數及其他結果,一方面是因為篇幅所限,另一方面是因為這些回歸系數的經濟學含義難以解釋,因此我們更關注脈沖響應函數、預測方差分解以及格蘭杰因果檢驗的結果。
[1]陳天祥,趙慧.從財政支出結構變遷看地方政府職能轉變——基于廣東省1978—2013年的數據分析[J].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06).
[2]陳高,王朝才.中國地方財政支出與經濟增長關系研究——基于1990~2012年省際數據的線性混合模型分析[J].財政研究,2014,(08).
[3]潘文卿,范慶泉,周縣華.消費性財政支出效率與最優支出規模:基于經濟增長的視角[J].統計研究,2015,(11).
[4]彭志文,郭路.財政支出結構、最優稅率區間與經濟增長[J].財政研究,2011,(03).
[5]石奇,孔群喜.動態效率、生產性公共支出與結構效應[J].經濟研究,2012,(01).
[6]唐小鵬,孫靜,趙彬,戴東陽.國防支出與經濟增長的向量自回歸模型分析[J].軍事經濟研究,2011,(09).
[7]張明喜,陳志勇.促進我國經濟增長的最優財政支出規模研究[J].財貿經濟,2005,(10).
[8]莊子銀,鄒薇.公共支出能否促進經濟增長:中國的經驗分析[J].管理世界,2003,(07).
[9]Shantayanan Devarajan,Vinaya Swaroop,Heng -fu Zou.The composition of public expenditure and economicgrowth.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1996,(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