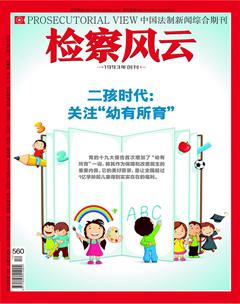中國北極正當權益應受尊重
馮壽波
學界對“北極(Arctic)”的不同界定關涉北極國家及域外國家的利益。2018年《中國的北極政策》白皮書將北極的地理位置、面積和范圍表述為:“地理上的北極通常指北極圈(約北緯66度34分)以北的陸海兼備的區域,總面積約2100萬平方公里。在國際法語境下,北極包括歐洲、亞洲、北美洲毗鄰北冰洋的北方大陸和相關島嶼,以及北冰洋中的國家管轄范圍內海域、公海和國際海底區域。北極的大陸和島嶼面積約800萬平方公里,有關大陸和島嶼的領土主權分別屬于加拿大、丹麥、芬蘭、冰島、挪威、俄羅斯、瑞典、美國八個北極國家。絕大多數北極地區為冰封的海洋。”
北冰洋為美、加、丹、挪、俄五國所環繞。隨著氣候變化和北極地區海冰的消融,新航道的浮現、豐富的資源等因素正在改變著北極乃至全球的地緣政治、經濟關系版圖,同時該地區也吸引了許多域外國家的關注和對北極事務的參與、博弈。隨著海洋科技的發展,北極的重要戰略地位日益凸顯,美、俄、加等國對北極的主權聲索和博弈,有不斷加強之勢,軍事化趨勢明顯。
近年來,氣候變化導致北極環境正在呈現的變化已超出人們預期的速度,國際社會對北極的關注度日益提升。隨著中國利益所涉地理范圍、存在形式和實現方式等方面的顯著變化,中國在北極存在著國家戰略利益的事實日益清晰。
人類命運共同體:《中國的北極政策》秉持的理念
北冰洋對于理解全球性氣候變化過程來說至關重要。北極氣候變化涉及全人類的共同利益,北極大陸架劃界爭議的解決、環境保護問題、軍事化問題,僅依賴域內國家的努力并不夠,需加強地區、全球合作。
北極環境具有特殊的敏感性、脆弱性特征,該地區的環境變化具有全球性影響,再加上北極國家間、域外國家間以及其相互間的矛盾,使得應對北極環境變化、維護北極和平秩序及可持續發展的努力面臨許多復雜因素的阻礙。中國基于大國國際法下義務及道義擔當,超越零和博弈與冷戰思維,秉持體現合作、平等、共贏、互利價值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并著眼于中國北極利益的維護,積極參與、應對北極事務,對北極國際法制的演變過程逐步施加中國影響。
《中國的北極政策》強調:“北極的未來關乎北極國家的利益,關乎北極域外國家和全人類的福祉,北極治理需要各利益攸關方的參與和貢獻。”白皮書指出北極問題具有全球意義和國際影響,作為近北極國家和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中國是北極事務的重要利益攸關方,肩負大國責任。
《中國的北極政策》 :政策目標與原則
隨著氣候變化的演進,北極終年為冰層覆蓋的海洋環境出現了令人不安的變化,冰層正以超過以往的通常速度在融化。
中國的北極政策目標是:“認識北極、保護北極、利用北極和參與治理北極,維護各國和國際社會在北極的共同利益,推動北極的可持續發展。”主要政策主張為:“中國參與北極事務堅持科研先導,強調保護環境、主張合理利用、倡導依法治理和國際合作,并致力于維護和平、安全、穩定的北極秩序。”
《中國的北極政策》第四部分闡述了相關原則:“中國主張穩步推進北極國際合作。加強共建‘一帶一路倡議框架下關于北極領域的國際合作,堅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則。”中國積極推動并參與北極新航道建設:“中國愿依托北極航道的開發利用,與各方共建‘冰上絲綢之路。”
中國參與北極事務的路徑
《中國的北極政策》基于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尊重UNCLOS等國際法制,結合中國“一帶一路”“冰上絲綢之路”倡議,提出了若干參與北極事務的具體路徑:
加強海洋科技研究
盡管加大了對北極科研的支持力度和重視程度,但限于主客觀條件,中國對北極了解仍有限,不利于參與北極事務的國際合作,擴大在北極的影響力。
應通過技術創新和加大投入來提升探索、認知和利用北極的能力。技術裝備是認知、利用和保護北極的基礎,中國正在建造第二艘破冰船。中國鼓勵發展注重生態環境保護的極地技術裝備,積極參與北極開發的基礎設施建設,推動深海遠洋考察、冰區勘探、大氣和生物觀測等領域的裝備升級,促進在北極海域石油與天然氣鉆采、可再生能源開發、冰區航行和監測以及新型冰級船舶建造等方面的技術創新。
加強北極環境保護的國內立法和國際合作
通過加強立法,我國保護海洋環境的國內法規逐步得以完善。此外,交通運輸部組織專家編寫了《北極航行指南(東北海道)/ (西北航道)》。
《中國的北極政策》第四部分指出,在區域層面,中國積極參與政府間北極區域性機制。中國建設性地參與國際海事組織事務,積極履行保障海上航行安全、防止船舶對海洋環境造成污染等國際責任。中國主張加強國際海事技術合作,在國際海事組織框架內尋求全球協調一致的海運溫室氣體減排解決方案。
善意履行條約義務,推動北極治理國際法制與時俱進
迄今尚無明確北極法律地位的國際條約,應對北極環境變化的國際法制呈“碎片化”,尚存局限性。UNCLOS僅為北極環境保護提供了初步的法律框架,鑒于北極環境的特殊性和脆弱性,尚難以適應保護北極環境的現實需要,且其實施效果尚依賴于各國,尤其是海洋國家對公約的尊重程度以及善意履行條約義務的政治意愿。
與美國退出《巴黎協定》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中國一向尊重國際環境條約的權威性,并切實履行條約義務。正如《中國的北極政策》所指出,在全球層面,中國積極參與全球環境、氣候變化、國際海事、公海漁業管理等領域的規則制定,依法全面履行相關國際義務。中國不斷加強與各國和國際組織的環保合作,大力推進節能減排和綠色低碳發展,積極推動全球應對氣候變化進程與合作,堅持公平、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和各自能力原則,推動發達國家履行在《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京都議定書》《巴黎協定》中作出的承諾,為發展中國家應對氣候變化提供支持。
《中國的北極政策》第一部分指出了北極國際法制:“北極事務沒有統一適用的單一國際條約,它由《聯合國憲章》、UNCLOS、《斯匹次卑爾根群島條約》等國際條約和一般國際法予以規范……北冰洋海域的面積超過1200萬平方公里,相關海洋權益根據國際法由沿岸國和各國分享。北冰洋沿岸國擁有內水、領海、毗連區、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等管轄海域,北冰洋中還有公海和國際海底區域。”
自2009年以來,國際海事組織已在致力于制定具有法律拘束力的《北極法典》工作,旨在涵蓋南極和北極地區環境保護、搜救以及船舶的設計、建造、裝備、船員培訓等諸多事項。北極理事會也就該工作加強了與國際海事組織的合作。
中國主張推動北極國際法制與時俱進。在善意履行條約義務的同時,應堅決維護中國的合法權益。筆者認為,似不應明確支持加拿大、俄羅斯關于西北航道、北方航道內水化主張。
“中國尊重北極國家依法對其國家管轄范圍內海域行使立法權、執法權和司法權,主張根據UNCLOS等國際條約和一般國際法管理北極航道,保障各國依法享有的航行自由以及利用北極航道的權利。中國主張有關國家應依據國際法妥善解決北極航道有關爭議。”俄、加等國的北極海洋權益主張應當符合UNCLOS等國際條約和一般國際法。
目前北極國際法制尚不完善,處于確立、發展等演變階段,中國應積極加入該進程,確立、擴大中國對北極事務的話語權。
將中國與北極地區相關國家間的合作與“一帶一路”倡議對接
北極新航道對中國來說具有極其重要的軍事、經濟價值,豐富了“一帶一路”建設的內容。中俄正在積極推進打造“冰上絲綢之路”,加強中國在北極的經濟存在,夯實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經濟基礎。
《中國的北極政策》研究的學術價值
隨著氣候變化問題成為國際關系中的熱點議題,全球氣候變暖、極端天氣頻現,已成全人類共同面臨的挑戰。2015年11月,巴黎聯合國氣候大會期間,各國為實現本世紀末將升溫幅度控制在兩攝氏度以下的目標而討價還價。
就北極而言:一方面,氣候變暖已導致冰川融化,數百萬年以來的終年冰蓋在近期逐步變為季節性冰蓋,這對北極環境和生物多樣性帶來明顯影響,也使得經由北極的海上新航線成為可能,開采北極礦產資源的技術難題在減少;另一方面,冰層的融化對如何保護北極地區日漸脆弱的生態環境提出了很大挑戰。
對北極氣候變化與《中國的北極政策》的研究,對于構建人類生態命運共同體、推動北極國際法制與時俱進、應對北極環境變化、維護中國北極利益,并逐步明確各國在應對北極環境變化中的責任、義務和權利,具有重要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