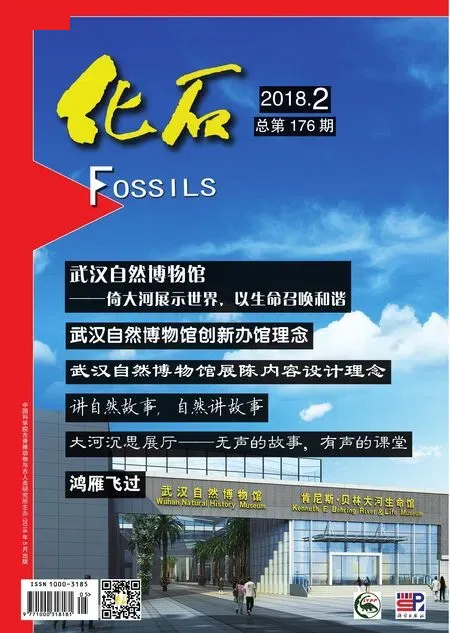進化論系列講座(十)達爾文
——(一)從懵懂少年走向貝格爾號
郭建崴
歷史上總有一些饒有趣味的巧合。就在拉馬克發表奠定其“進化論創始人”地位的《動物學哲學》的1809年,在英國的施魯斯伯里小鎮誕生了一個嬰兒,他就是后來使進化論發揚光大并由此改變了人類認識歷史的查爾斯·羅伯特·達爾文(Charles Robert Darwin)。
達爾文在青少年時期并沒有顯露出什么過人之處,以至于被老師認為是一個智力在一般水平之下的孩子;他的父親甚至曾經指責他“只會打鳥、玩兒狗和捉老鼠,將會辱沒家門”。但誰會想到,熱衷于打獵、采集礦石和動植物標本,這些在當時英國男孩子中很普遍的愛好,實際上卻奠定了達爾文最終成為科學大師的基礎呢?
達爾文的祖父和父親都是當地的名醫,既有社會地位又有可觀的收入,因此父親當然希望他能夠繼承祖業,于是在1825年把16歲的達爾文送到愛丁堡大學學醫。達爾文對醫學課程缺乏興趣,尤其是對血淋淋的外科手術感到厭惡。相反,他對博物學情有獨鐘,閱讀了大量的相關書籍,還向約翰·愛德蒙斯頓(John Edmonstone)學習動物標本的剝制技術。進入大學的第二年,他加入了一個由地質學家羅伯特·詹姆森(Robert Jameson)教授贊助的博物學學生團體——普林尼學會,并且投到擁護拉馬克主義的動物及解剖學家羅伯特·愛德蒙·葛蘭特(Robert Edmund Grant)門下,參與了葛蘭特研究團隊在佛斯灣對潮間帶海生動物生命周期的研究。1827年3月,達爾文把自己在這些研究中的兩個發現寫成兩篇文章,在普林尼學會上宣讀并獲得同學們的好評。其中一個發現是,牡蠣殼中所常見的黑色物體,是一種海蛭的卵衣,而不是過去所認為的幼齡階段的墨角藻;另一個發現是,前人認為的能借助鞭毛而獨立運動的板枝介的卵實際上是其幼蟲。
在此期間,達爾文上過詹姆森講授的地質學和動物學課程,并隨同他以及同學們進行野外考查,聽他現場解釋巖石的成因。此外,達爾文還學習了植物的分類等大量自己感興趣的課程。
父親對兒子在“專業”上沒有進展但是卻“不務正業”非常不滿,于是在達爾文進大學兩年后將他轉送入劍橋大學基督學院就讀人文學士課程,希望他將來成為一位收入不菲的“尊貴的牧師”。然而達爾文對騎術與射箭的興趣遠勝過讀“圣書”,尤其熱衷于與他的遠房表哥威廉·達爾文·福克斯(William Darwin Fox)比賽收集甲蟲。經福克斯介紹,達爾文結識了植物學教授同時也是甲蟲專家的約翰·亨斯羅(John Henslow)。達爾文一下子就迷上了亨斯羅的博物學課程,并成為亨斯羅的密友和家中常客,因此還被人嘻稱為“走在亨斯羅身旁的人”。
談到達爾文當年對甲蟲的癡迷,就不得不提那件被人們津津樂道了不知多少遍的故事。1828年的一天,達爾文在倫敦郊外的一片樹林里轉悠。突然,他發現在一棵老樹將要脫落的樹皮下有蟲子在蠕動,便迅速剝開樹皮,發現兩只奇特的甲蟲。達爾文立刻左右開弓將它們抓在手里,興奮地觀察起來(編者注:武漢自然博物館有一個抓甲蟲的互動展項,相當有趣,去那兒參觀者不妨體驗一下)。此時樹皮里又跳出一只甲蟲,達爾文情急之下把一只手里的甲蟲塞進嘴里,騰出手去把第三只甲蟲抓到。嘴里的那只甲蟲卻在這時排放出一股辛辣的毒汁,把達爾文的舌頭刺激得又疼又麻。達爾文趕緊張口把它吐到手里,然后帶著滿嘴的“不是滋味兒”和三只甲蟲,心滿意足地回到劍橋大學。后來,這種首先被他發現的甲蟲物種就被命名為“達爾文”。
不過在劍橋大學,達爾文很可能也接受了當初在愛丁堡大學時的教訓,他在考試臨近的時候私下接受亨斯羅的指導,同時將重心放在課業。在1831年2月的期末,他的神學成績優異,其他諸如古典學、數學、物理學等也能應付過關,最終以非優等生中排名第10的結果從劍橋大學畢業。當時的達爾文信仰基督教,更確切地說,他是自然神學者,這要“歸功”于他自幼以來的家庭和社會背景以及劍橋大學基督學院的那些神學課程和神學著作。其中對達爾文影響尤其大的是副主教威廉·佩利(William Paley)的著作,包括論證神必定存在的《目的論的證明》。佩利認為生命對自然環境的高度適應恰是對上帝存在的證明,而且表明上帝并不需要過于忙碌,也并不需要一再創造奇跡來干預生命。上帝只是擔當了偉大的宇宙設計師。佩利用類比的方法論述了這一問題,“如果你找到一只表,你幾乎不會懷疑它是由制表者設計的。因此,如果你對一種更高級的有機體及其復雜的和有目的的器官如眼睛等加以考慮,那么你就一定會得出結論,它必然是由有才智的造物主所設計的。”當時年輕達爾文對這樣的論述欽佩之至,但是20多年以后當他建立起科學的進化世界觀之時,達爾文對這個著名的“佩利問題”進行了有理有據的徹底否定。
畢業之時,達爾文對父親建議他做一名鄉村牧師的想法還是頗感興趣的,因為那種悠閑的生活會使他有充裕的時間開展自然神學探索并進行創作。不過他接受了亨斯羅的勸告,并未馬上投入神職工作,繼續在劍橋逗留到了6月份。在此期間他受到德國地理學大師亞歷山大·馮·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所寫的《個人記述》啟發,希望能和一些同學一起去馬德拉群島研究熱帶博物學。在準備中,達爾文經亨斯羅介紹又結識了地質學家亞當·塞奇威克(Adam Sedgwick,以曾經的中譯名“薛知微”而聞名于中國地質學界),學習了地質學課程,并跟隨他去威爾士進行地質考察。在野外,塞奇威克教會了達爾文如何采集巖石標本、如何觀察研究遠古巖層的地質和化石、如何弄清一個地區的地質狀況,還指導他怎樣思考和分析地質學問題。這次難得可貴的科學實踐鍛煉了達爾文,為其后來的獨立野外工作和深入的科學研究奠定了扎實的基礎。

收藏在劍橋大學動物博物館中的達爾文采集的甲蟲標本(王原供圖)
威爾士考察結束兩周后,達爾文在8月份回到家里,發現了一封亨斯羅的來信,希望并推薦他去跟隨皇家海軍貝格爾號巡洋艦的艦長羅伯特·費茨羅伊(Robert FitzRoy)出海遠航。當時費茨羅伊正準備受命在4周后前往南美洲海域考察并繪制當地航海圖,他希望旅途中能有位年輕的紳士作伴,于是想要招一名不計薪酬的博物學家。達爾文的父親竭力反對兒子參加這個為期兩年的旅程,認為這純屬浪費時間。一心想抓住這個機會的達爾文找來了舅舅(后來成為了老丈人)說情,終于說服了老爹同意他參加航程。
隨后,達爾文又僥幸通過費茨羅伊艦長的面試,登上了貝格爾號。這艘后來因達爾文而流芳百世的軍艦于1831年12月27日楊帆起航,從此改變了達爾文,也因此改變了世界。當然,這樣的改變不是一蹴而就的,其跌宕起伏請聽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