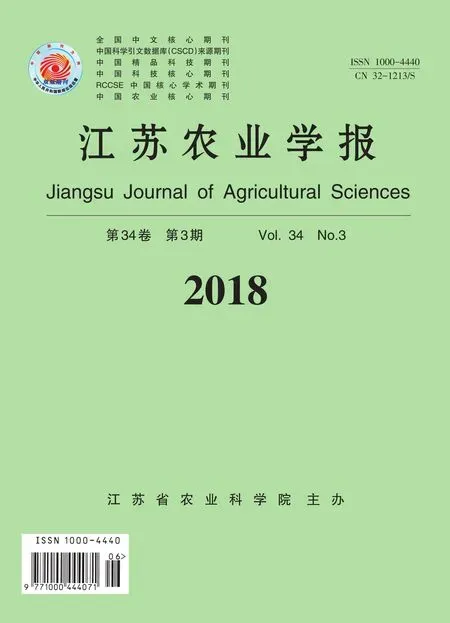陜南水稻根際細菌多樣性變化趨勢
王夢姣
(1.陜西理工大學陜西省資源生物重點實驗室,陜西 漢中 723000; 2.陜西理工大學陜西省食藥用菌工程技術研究中心,陜西 漢中 723000; 3.陜西理工大學生物科學與工程學院,陜西 漢中 723000)
植物根際微生物是根際微生態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能夠直接影響土壤物理結構,對土壤肥力、植物營養轉化起決定性作用,是衡量土壤肥力的重要指標[1-2]。對農作物根際微生物結構組成、空間分布、多樣性變化趨勢的分析,有助于從微生物角度改善土壤環境和土壤結構,對進一步研究根際微生物與農作物的互作關系,提高陜南農作物產量和質量具有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意義。
目前,人們對小麥(TriticumaestivumL.)、玉米(ZeamaysLinn.)等作物的根際微生物多樣性進行了許多研究,均發現根際微生物多樣性與作物的生長發育密切相關[3-4]。例如,胡桂萍等[5]針對水稻內生菌和根際微生物群落多樣性進行共同研究發現,不同水稻品種其根際微生物群落多樣性具有顯著差異;借助根際微生物群落多樣性的平臺,劉波等[6]進行新的微生物分離方法的研究,這為從不同發育時期分離不同微生物,并對其功能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張仕穎等[7]利用丁草胺污染對水稻及水稻根際微生物區系作用的試驗闡明了外界影響能夠對水稻根際微生物群落特征有顯著影響,這也反應了在“根際微生物-土壤-作物”這個微生態系統中,根際微生物的變化能夠直接關聯作物的生長發育;化感水稻根際微生物的生物學特性研究[8],可以使我們了解特定水稻品種的根際微生物的生態學特性。這些研究結果都證明,水稻根際微生物與水稻生長發育密切相關,根際微生物多樣性與作物的生長發育存在緊密的互作和聯系[9-10]。
陜西南部地區是陜西省水稻的主產區,也是中國重要的水稻主產區[11],該地區的水稻種植方式屬于輪作制[12]。前人研究還未涉及到陜南這一具有油菜-水稻輪作制耕種體系的根際微生物多樣性分析,本研究旨在利用培養法研究陜南水稻-油菜輪作區的2個水稻品種在其五葉期、分蘗期、孕穗期[13-14]的根際細菌多樣性組成,擬從土壤細菌層面探討水稻生長發育與根際細菌之間的關系,為進一步指導實際生產提供理論依據。
1 材料與方法
1.1 采樣地及水稻概況
本試驗在陜西南部地區水稻主要種植區漢濱、城固和寧強[15-16]進行,這3個采樣地氣候分別屬于亞熱帶大陸性季風氣候、北亞熱帶濕潤季風區和暖溫帶山地濕潤季風氣候,降水集中在9月,經度分別為109°01′ E、107°13′ E、105°60′ E,緯度分別為32°42′N、32°75′N、32°55′N,海拔高度分別為260 m、480 m、820 m,供試土壤均為潴育性水稻土,灌溉水源均為河水,使用肥料均為尿素、復合肥(N∶P∶K=15∶15∶15,質量比)。前茬作物為油菜。
水稻K優082為平原地區主栽品種[16],3個采樣地產量分別是10 062.0 kg/hm2、10 207.5 kg/hm2、9 100.5 kg/hm2,千粒質量分別為31.9 g、31.2 g、31.6 g,單株有效穗數分別為17.3、16.7、16.9,每穗粒數分別為180.8、160.6、161.4,結實率分別為84.3%、85.8%、82.6%。先豐優901為山區地區主栽水稻品種[17],3個采樣地產量分別是9 762.0 kg/hm2、9 906.0 kg/hm2、9 252.0 kg/hm2,千粒質量分別為29.7 g、29.2 g、29.4 g,單株有效穗數分別為18.1、17.4、16.2,每穗粒數分別為182.5、170.0、169.1,水稻結實率分別為86.9%、84.7%、80.7%。
1.2 水稻根際采集時間及采集方法
采集土樣時間為2015年4月至8月,具體采樣時間見表1。采用五點采樣法進行根際樣品采集,將水稻根系從土壤中挖出,用抖落法[17]抖掉與根系松散結合的土體,然后將土壤連帶植物組織包裹帶回實驗室后進行充分混勻,過2 mm篩。

表1 采樣時間表
1.3根際微生物的分離計數及純培養
稱取10 g水稻根際放入裝有100 ml無菌水的三角瓶中,150 r/min振蕩10 min,吸取5 ml至裝45 ml有無菌水的三角瓶中,制成1∶100的稀釋液,再依次制備成10-1、10-2、10-3梯度稀釋液。吸取各稀釋液100 ml至牛肉膏蛋白胨培養基的培養皿中,涂布均勻,37 ℃培養 14~18 h。每個稀釋梯度做3個重復。利用菌落計數器對每一個平板上的土壤細菌進行單菌落計數,計算分離出來的土壤中的細菌數[18]。
菌落數=菌落平均數×稀釋倍數/干土質量×100%
1.4 細菌16S rDNA的擴增及序列分析
用天根細菌基因組DNA提取試劑盒將細菌基因組DNA提取后,用通用引物27F(5′-AGAGTTTGATCCTGGCTCAG-3′)和1492R(5′-GGTTACCTTGTTACGACTT-3′)進行16S rDNA的序列擴增。PCR反應體系(50.00 μl)為:10×Buffer 5.00 μl、2.5 mmol/L Dntp 5.00 μl、上下游引物各2.00 μl、模板1.00 μl、Taq酶0.25 μl,加水至50.00 μl。PCR反應條件為:94 ℃預變性5 min;94 ℃變性30 s、55 ℃退火30 s、72 ℃延伸90 s,35個循環;72 ℃延伸5 min,終止PCR反應。采用0.8%瓊脂糖對PCR擴增產物進行電泳檢測,并送上海英駿測序公司測序。
測序完成后,對所有菌株進行 16S rDNA序列測定。測序結果利用BLAST軟件(http://www.ncbi.nlm.nih.gov/blast/Blast.cgi)與GenBank 數據庫中的序列進行比對分析,初步確定分離得到菌的種屬。
1.5 系統發育樹的構建
選取同源性最高且有效發表的菌株序列,利用 MEGA5.1 軟件(http://www.megasoftware.net/mega5.1.html)進行分析,用 Clustal W 按照最大同源性的原則進行排序,采用Kimura-2 計算核苷酸差異值,最后用鄰接法(Neighbor-Joining method)[19]構建系統發育樹。
2 結果與分析
2.1 水稻根際細菌的數量變化
對3個地區根際細菌菌落數的統計(圖1)發現,在溶液稀釋10倍和100倍的條件下,漢濱和城固地區K優082的根際細菌菌落數大于先豐優901,寧強地區則相反。這可能是由于平原主栽品種K優082在平原地區(漢濱和城固)生長狀態更好,與根際微生物互作關系更強,能夠被分離得到更多的細菌,而山地主栽品種先豐優901則在山地(寧強)地區更有生長優勢。這說明,水稻品種及地理位置對水稻根際細菌數量有顯著影響,這與黃柳琴等[20]、厲桂香等[21]的研究結果較為一致。稀釋1 000倍的土壤溶液中可培養的細菌數量均較小,不能進行比較和分析。
分析曲線變化可以發現,在五葉期的10倍和100倍根際土壤稀釋液中分離得到了較多的細菌菌落,且其數量較其他兩個時期有顯著差異。這一現象均出現在3個采樣地的2個水稻品種根際土壤細菌分離過程中。可以初步推斷,水稻可能在五葉期與微生物互作更為緊密,分蘗期次之,孕穗期最差。這可能與水稻生長特性相關,隨著水稻的生長發育,土壤含水量逐漸升高,導致細菌數量下降[22]。

圖1 細菌菌落數變化趨勢圖Fig.1 The variation tendency of bacterial colony
2.2 水稻根際土壤細菌組成
對分離獲得具有明顯差異的單菌落進行DNA提取及16S rDNA擴增,每個采樣地的每個水稻品種3個時期的根際細菌單菌落均篩選出 70株細菌。從圖2中可以看出,提取的DNA較為完整,擴增后得到約為1 500 bp的細菌16S rDNA條帶,可保證后續測序結果的完整性。
每個采樣地的每個品種在每個時期均成功進行了62個測序,通過對測序結果的分析發現,水稻根際中共檢測出4個門,分別為擬桿菌門(Bacteroidetes)、放線菌門(Actinobacteria)、變形菌門(Proteobacteria)和厚壁菌門(Firmicutes)。其中,厚壁菌門為優勢菌種,在每個采樣點所占比例均超過70%,在漢濱采樣地的水稻分蘗期先豐優901的根際細菌均屬于厚壁菌門。從圖3中還可以發現,隨著水稻的生長發育,厚壁菌門所占比例也逐漸上升,在分蘗期達到最高峰,又在孕穗期下降。變形菌門在所有的五葉期和孕穗期的根際中均能發現。

A圖和B圖中M代表Maker,用來指示條帶長度,為康為世紀的100 bp ladder,貨號為CW0636M。A圖中1~6代表6個不同的細菌菌液提取出來的基因組DNA,B圖中1~6代表6個細菌基因組DNA經過PCR擴增出來的16S DNA條帶。圖2 水稻根際細菌基因組DNA提取(A)及細菌16S rDNA擴增圖(B) Fig.2 Results of DNA(A) and 16S rDNA(B) on soil bacteria form rice rhizosphere

a:K優082-五葉期;b:先豐優901-五葉期;c:K優082-分蘗期;d:先豐優901-分蘗期;e:K優082-孕穗期;f:先豐優901-孕穗期。圖3 水稻根際細菌組成Fig.3 The group of bacteria in rice rhizosphere soil
進一步從屬的角度分析,從圖4中可以看出:首先,在分析的所有根際樣本中,共有26個屬,1~26分別為芽孢桿菌屬(Bacillussp.)、假單胞菌屬(Pseudomonassp.)、葡萄球菌屬(Staphylococcussp.)、節桿菌屬(Arthrobactersp.)、根瘤菌屬(Rhizobiumsp.)、產堿桿菌屬(Alcaligenessp.)、腸桿菌屬(Enterobactersp.)、泛菌屬(Pantoeusp.)、不動桿菌屬(Acinetobactesp.)、短桿菌屬(Brevibacteriumsp.)、嗜冷桿菌屬(Psychrobactersp.)、鞘氨醇菌屬(Sphingobacteriumsp.)、Lysinibacillusvarians、弗拉托氏菌屬(Frateuriasp.)、Fictibacillus、黃單胞菌屬(Xanthomonassp.)、巴斯德菌屬(Pasteurellasp.)、噬氫菌屬(Hydrogenophagaatypica)、梭菌屬(Fusiformis)、Terribacillus、叢毛單胞菌屬(comamonas sp.)、寡養單胞菌屬(Stenotrophomonas)、土壤桿菌屬(Agrobacteriumsp.)、阪崎腸桿菌屬(Cronobactersp.)、氣單胞菌屬(Aeromonassp.)和嗜氮根瘤菌屬(Azorhizophilussp.)。其中,枯草芽孢桿菌屬為優勢菌,其在除漢濱地區K優082的五葉期根際樣本(枯草芽孢桿菌屬細菌占總菌數的64.52%)以外的所有根際樣本中所占比例均超過80.00%,最高甚至達到98.39%(寧強采樣地的K優082在孕穗期的根際樣本)。
其次,3個采樣地的2個水稻品種在五葉期的根際樣本中細菌豐度最好,這一結論也與本研究關于細菌計數及細菌組成分布的結論一致。因此,五葉期水稻與土壤及根際微生物互作最為顯著。
2.3 系統進化樹的構建
根據測序結果對所有分離得到的細菌進行了統一歸類,對獲得的細菌DNA序列與GenBank數據庫中的序列進行比對,選擇一些與測定序列同源性較高的抑制種序列作為參考序列,構建系統發育樹。結果(圖5)表明,在所有土壤樣本中,共得到66個不同的細菌種,枯草芽孢桿菌屬為優勢細菌類群。

圖4 3個采樣地不同水稻生長時期根際細菌多樣性變化趨勢Fig.4 The diversity trends of bacteria in rhizosphere soil in different rice growth period

圖5 基于16S rDNA的水稻根際細菌系統發育樹Fig.5 Phylogenetic tree of bacteria in rice rhizosphere soil based on 16S rDNA
3 討 論
本研究主要針對西北水稻主產地——陜西南部地區,對不同生長發育時期,2個水稻品種的根際微生物組成進行了分析。結果表明,從所有根際樣本中共分離得到了26個屬的細菌,分別劃歸于4個門。其中厚壁菌門的細菌占大多數,芽孢桿菌屬為優勢屬。本研究數據對構建陜南土壤微生物數據庫提供了基礎試驗數據。同時,試驗還發現了一些其他具有一定研究價值的菌屬,比如前人研究較少,具有良好抗鹽效果的Terribacillus屬[23],將會在后續研究中繼續進行探索。
本研究還對不同生長階段的細菌多樣性變化趨勢進行分析,結果發現,2個水稻品種根際細菌均在五葉期的多樣性最強,隨后逐漸降低,但分蘗期和孕穗期差異不大。這說明,與分蘗期和孕穗期相比,五葉期水稻與根際細菌互作更為頻繁。這就意味著,在下一步研究輪作制狀態下水稻與根際微生物互作關系時選擇五葉期更為合適。
本研究僅采用牛肉膏蛋白胨單一培養基分別對水稻根際細菌進行分離研究,初步揭示了陜南油菜-水稻輪作制下,水稻根際特有生境中微生物種群的組成特征,但仍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有必要采用不依賴純培的分子生物學方法,以獲取更全面的水稻根際微生物多樣性信息。
參考文獻:
[1] ASEMOLOYE M D, AHMAD R, JONATHAN S G.Synergistic action of rhizospheric fungi with Megathyrsus maximus root speeds up hydrocarbon degradation kinetics in oil polluted soil[J]. Chemosphere, 2017, 187:1-10.
[2] 段紅平,張乃明,李進學,等. 高產水稻根基微生物類群數量初探[J]. 中國農學通報,2007,23(2):285-289.
[3] ROSIER A, BISHNOI U, LAKSHMANAN V, et al. A perspective on inter-kingdom signaling in plant-beneficial microbe interactions[J]. Plant Mol Biol, 2016, 90(6):537-548.
[4] LAKSHMANAN V, SELVARAJ G, BAIS H P.Functional soil microbiome: belowground solutions to an aboveground problem[J]. Plant Physiol, 2014, 166(2):689-700.
[5] 胡桂萍. 水稻內生菌及其根系土壤微生物群落多樣性的研究[D]. 福州:福建農林大學,2010.
[6] 劉 波,胡桂萍,鄭雪芳,等. 利用磷脂脂肪酸(PLFAs)生物標記法分析水稻根際土壤微生物多樣性[J]. 中國水稻科學,2010,24(3):278-288.
[7] 張仕穎,夏運生,肖 煒,等. 丁草胺污染對高產水稻土微生物區系的影響[J]. 生態環境學報,2014,23(4):679-684.
[8] 林文雄. 化感水稻抑草作用的根際生物學特性與研究展望[J]. 作物學報,2013,39(6):951-960.
[9] KUMAR A S, BAIS H P.Wired to the roots: impact of root-beneficial microbe interactions on abovegroundplant physiology and protection[J]. Plant Signal Behav, 2012, 7(12):1598-1604.
[10] LAKSHMANAN V, RAY P, CRAVEN KD.Toward a resilient, functional microbiome: drought tolerance-alleviating microbes for sustainable agriculture[J]. Methods Mol Biol, 2017, 1631:69-84.
[11] 馬 欣,吳紹洪,戴爾阜,等. 氣候變化對我國水稻主產區水資源的影響[J]. 自然資源學報,2011,26(6):1052-1063.
[12] YU L, ZHU J, HUANG Q, et al. Application of a rotation system to oilseed rape and rice fields in Cd-contaminated agricultural land to ensure food safety[J]. Ecotoxicol Environ Saf, 2014,108:287-293.
[13] 湯 潔,梁 爽,張 豪,等. 吉林省西部鹽水田水稻生長不同時期土壤有機碳和堿解氮的動態變化特征[J]. 中國科技論文,2015,10(9):1053-1057.
[14] 朱海平,李貴勇,夏瓊梅,等. 不同時期干旱脅迫對水稻產量及生長特性影響[J].中國稻米,2017,23(4):135-138.
[15] 張選明,馮志峰,李 勤,等. 陜西漢中優質稻生產現狀及思考[J].陜西農業科學,2010, 56(3):126-128.
[16] 喬 帥,王夢姣,鄧百萬,等. 輪作區水稻根際土壤鈣鎂離子含量、含水量和酸堿度變化趨勢[J].江蘇農業科學,2017,45(5):284-288.
[17] FUJII Y, AKIHIRO F, SYUNTARO H. Rhizosphere soil method: a new bioassay to evaluate allelopathy in the field [C]//TUPPER G, WILKES S, FLYNN H, et al. 3rd Australian New Zealand Soils Conference: Novel Approaches. Australia: Charles Sturt University Press, 2004: 490-492.
[18] 岳 輝,李志真,鐘炳林. 水土流失區芒箕生長與土壤微生物區系研究[J].林業科技,2009,34(4):22-26.
[19] TAMURA K,PETERSON D,PETERSON N,et al. MEGA5:molecular evolutionar y genetics analysis using maximum likelihood,evolutionary distance,and maximum parsimony methods[J]. Molecular Biology & Evolution,2011,28(10):2731-2739.
[20] 黃柳琴. 我國部分地球關鍵帶中氨氧化菌群分布及其對環境的響應[D]. 北京:中國地質大學,2015.
[21] 厲桂香,馬克明.土壤微生物多樣性海拔格局研究進展[J]. 生態學報,2018,38(5):1521-1529.
[22] 楊瑞紅,趙成義,王新軍,等.梭梭和怪柳土壤微生物多樣性初步分析[J]. 土壤,2016,48(6):1120-1130.
[23] LIU W Y, JIANG L L, GUO C J, et al.Terribacillusaidingensissp. nov., a moderately halophilic bacterium[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ystematic and Evolutionary Microbiology, 2010, 60:2940-29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