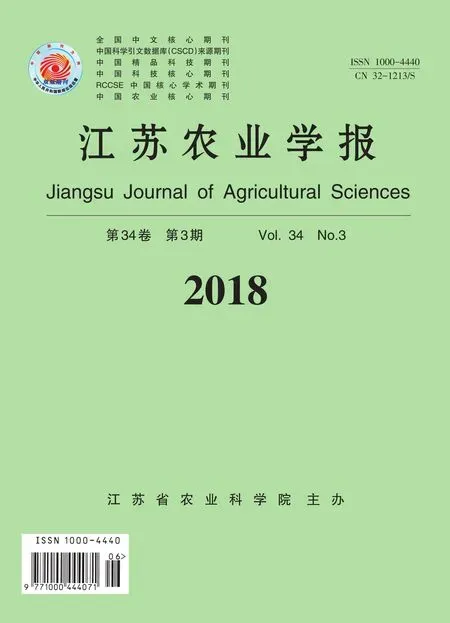豬極體的排出與退化規律及其活性保存
徐小波, 章熙霞, 王公金, 譚小東, 周曉龍
(1.江蘇省農業科學院畜牧研究所/農業部種養結合重點實驗室,江蘇 南京 210014; 2.南京市畜牧家禽研究所,江蘇 南京 210036)
哺乳動物卵母細胞第一次減數分裂產生1個卵母細胞和第一極體(PbⅠ),第二次減數分裂產生1個卵母細胞和第二極體(PbⅡ),極體(Pb)排出后一般幾小時至十幾小時便退化,部分第一極體會繼續分裂為2個小極體。之前,人們認為極體只是退化的沒有生物學功能的染色質,很少有人對其進行研究,直到1995年,Evsikov等[1]發現小鼠極體可以參與受精卵發育,從而證明了極體中的染色質具有與卵母細胞中染色體一樣的功能。隨后,極體作為含有與卵母細胞相近遺傳物質的特殊細胞,其生物學功能和利用價值得到人們的重新認識與重視。有學者利用PbⅡ和PbⅠ的遺傳物質重組卵母細胞,得到能正常繁殖的小鼠后代[2-3]。人卵母細胞PbⅠ的排出與否及其形態與卵母細胞本身的質量和發育率有關,而與能否受精無關[4-5]。國內科學家對極體的研究起步較晚,大多是將極體作為一種生物信號或標記,而針對極體的生物學功能及如何保存與利用的研究報道很少。其中,蘭宗寶等[6]發現豬卵母細胞是否排出PbⅠ直接影響胚胎早期發育,鮑時華等[7]發現通過小鼠卵母細胞PbⅠ的形態可預測受精卵質量。在人類醫學臨床實踐中,極體的染色體已成功應用于人類的基因診斷,以降低遺傳缺陷的發生率[8-9]。李澎濤等[10]發現,PbⅠ與人卵母細胞的受精和發育能力有關,可根據PbⅠ的形態來預知卵母細胞的發育情況。谷瑞環等[11]認為,根據受精后PbⅡ出現的比例可一定程度預知體外受精結果,并且發現早出現PbⅡ的卵母細胞質量或質核成熟同步化較好。劉芳等[12]也發現,人卵母細胞受精后3~5 h出現PbⅡ且 18~20 h形成2個原核的胚胎發育潛能較好。本研究擬對豬卵母細胞和受精卵在體外培養條件下PbⅠ和PbⅡ的排出與退化規律進行觀察與判定,對其形態學以及不同保存條件下的活性進行鑒定與評價,以期為極體功能的深入研究提供優質材料。
1 材料與方法
1.1 豬卵巢和卵母細胞的采集
于生豬屠宰場挑選年齡在6月齡左右,體質量 95~110 kg的杜長大或杜大長育肥豬中的未閹割母豬,摘取生產線上剛屠宰開膛后溫熱胴體的豬卵巢,置于盛有生理鹽水的 28~37 ℃保溫瓶中。于2 h內,在無菌室用注射器抽吸直徑 3~5 mm卵泡的卵泡液,在實體顯微鏡下,檢出有3層以上顆粒細胞包圍的卵丘卵母細胞復合體(COCs),轉移至平衡2 h以上的TCM-199液滴中,清洗 2~3次,進行體外成熟培養(5% CO2的空氣,飽和濕度,39 ℃, 24~72 h)。
1.2 極體的排出與采集
不同時間段取體外成熟培養的COCs,將卵母細胞周圍的顆粒細胞除去,每隔4 h觀察一次PbⅠ 的排出情況。精卵共孵育在改進型Tris緩沖液(mTBM)中進行,完成后轉入北卡萊羅納州立大學-23培養基中,每隔4 h觀察一次PbⅡ的排出情況。PbⅠ和PbⅡ的采集均采用顯微操作法:選擇含有 1~2級PbⅠ和PbⅡ的卵母細胞或受精卵,以顯微操作儀固定針固定卵母細胞或受精卵,用內徑 20~25 μm的拔尖去核針刺入透明帶,伸入卵周隙,吸取PbⅠ和PbⅡ。
1.3 極體的形態學分級和活性鑒定
PbⅠ和PbⅡ的形態學評估標準參照Ebner等[13]的方法進行,根據外形、胞質均勻度、膜表面平滑度和完整度分為5個等級。
PbⅠ和PbⅡ的活性鑒定參照劉文華等[14]的方法進行,即通過臺盼藍染色的方法進行鑒定,有活性的胞質不染色,無活性的呈藍色。
1.4 極體的體外保存
本試驗主要探討39 ℃、4 ℃、-20 ℃、-196 ℃ 4種溫度條件下Pb的保存情況。
1.4.1 常溫及低溫保存 根據形態分級選取含 1~2級PbⅠ的卵母細胞和含 1~3級PbⅡ的受精卵,放入預平衡的組織培養液-199(TCM-199)微滴培養系統中,分別在4 ℃及39 ℃下保存,在設定時間取部分卵母細胞或受精卵對Pb進行活性鑒定。
1.4.2 冷凍和超低溫冷凍保存 將含有PbⅠ的卵母細胞和含有PbⅡ的受精卵裝入含乙二醇40(EG40)冷凍保護液的微管中(直徑 200~300 μm),置于-20 ℃冰箱中冷藏或直接投入液氮(-196 ℃)中冷凍保存。在設定時間取樣,解凍并對Pb進行活性鑒定。
1.5 數據分析
卵丘擴散率、極體排出率、保存成活率及形態學差異等數據采用SPSS16.0進行統計,采用多重比較檢驗數據的差異性。
2 結果與分析
2.1 極體的排出時間
2.1.1 PbⅠ 表1顯示,體外成熟培養過程中卵丘細胞呈現不同程度的擴散,培養 32~36 h開始排出PbⅠ,培養40 h時卵丘細胞擴散率(86.8%)最高,PbⅠ排出率(66.7%)也達到最高。培養 40~52 h,卵丘細胞慢慢脫落,擴散率有所降低。
2.1.2 PbⅡ 2批610枚(第一批310枚,第二批300枚)受精卵培養觀察結果(表2)顯示,卵母細胞受精后4 h就有少量的PbⅡ排出,16 h排出量迅速增加,20 h的排出率(49.5%)最高,24 h部分PbⅡ出現退化或消失,排出率開始下降。

表1 不同培養時間PbⅠ排出率
同列數據后不同小寫字母表示不同處理間差異顯著(P<0.05)。

表2 受精后不同培養時間PbⅡ排出率
同列數據后不同小寫字母表示不同處理間差異顯著(P<0.05)。
2.2 不同排出時間極體的形態與活性
2.2.1 Pb Ⅰ 表3顯示,卵母細胞體外培養32 h至36 h開始有Pb Ⅰ排出,并發現開始排出的Pb Ⅰ中1~2級的比例(37.5%)不是很高。培養40~44 h排出的Pb Ⅰ較多,其中培養40 h的1~2級的比例高達51.7%,3級的比例30.7%,4~5級的比例只有17.6%。培養44~52 h,1~2級Pb Ⅰ的比例下降,而4~5級的比例升高,到52 h時1~2級Pb Ⅰ只有14.8%。形態分級與活性鑒定結果表明,1~2級Pb Ⅰ大多具有生物活性, 3級Pb Ⅰ的活性相對較差,4~5級Pb Ⅰ基本沒有活性。

表3 不同排出時間PbⅠ形態分級
同列數據后不同小寫字母表示不同處理間差異顯著(P<0.05)。
2.2.2 PbⅡ 表4顯示,受精后4~20 h排出的PbⅡ中1~2級所占比例均高于50%,受精后24 h 1~2級PbⅡ所占比例明顯下降。其中受精后16 h和20 h排出的PbⅡ1~2級的比例分別保持在50.4%和58.9%,結合前述受精后不同時間PbⅡ的排出率結果(受精后20 h排出率最高,49.5%), 確定受精后20 h左右是豬PbⅡ最佳的采集時間。活性鑒定結果表明,PbⅡ在形態與活性的相關性方面與PbⅠ一致。

表4 受精后不同排出時間PbⅡ的形態分級
同列數據后不同小寫字母表示不同處理間差異顯著(P<0.05)。
2.3 不同保存溫度對極體形態與活性的影響
2.3.1 PbⅠ 表5顯示,39 ℃下保存2 h,PbⅠ的形態正常且存活率較高,保存4 h時形態尚正常,但存活率顯著下降,保存6 h形態不正常,并且存活率只有18.2%。4 ℃條件保存 20~40 h,PbⅠ仍然保持良好的形態與較高的存活率,但保存60 h時,PbⅠ開始崩解或消失(形態正常率30.5%),完全喪失活性(存活率為0)。-20 ℃冷凍保存168 h,PbⅠ形態正常率為98.3%,存活率為95.0%。-196 ℃超低溫冷凍保存1 344 h,PbⅠ形態正常率(97.8%)和存活率(89.1%)均保持在較高水平。

表5 不同保存溫度下PbⅠ的形態與活性
同列數據后不同小寫字母表示不同處理間差異顯著(P<0.05)。
2.3.2 PbⅡ 表6顯示,受精卵中的PbⅡ在39 ℃下保存12 h仍有75.9%的存活率,保存16 h存活率顯著下降,為34.5%。4 ℃下保存30 h,PbⅡ的存活率為87.5%,保存60 h時,存活率僅有8.3%,形態正常率為25.0%。-20 ℃冷凍保存240 h,PbⅡ的存活率為84.6%,保存360 h時,PbⅡ的存活率為69.2%,保存480 h時,PbⅡ的存活率為23.1%。-196 ℃超低溫冷凍保存1 344 h后,PbⅡ的形態正常率和存活率分別為95.7%和87.0%。
3 討 論
不同哺乳動物極體的排出時間有很大差異。小鼠注射人絨毛膜促性腺激素后12 h得到的PbⅠ數量最多[14],與公鼠交配后24 h,PbⅡ排出率最高,達到79.7%[15]。在體外成熟培養過程中,牛卵母細胞PbⅠ的排出高峰出現在16 h,排出率為37.0%,培養24 h時排出率達74.5%[16]。孫青原等[17]發現,牛受精后5 h時PbⅡ被排出。用乙醇對體外成熟培養 26~30 h的延邊黃牛卵母細胞進行預激活(5~7 min),培養 2~3 h后第二極體大量排出[18]。華再東等[19]發現,豬COCs培養時間不足38 h時,雖能看到極體,但激活后卵裂率極低,說明卵母細胞并未真正成熟。本研究中,豬卵母細胞體外培養36 h時出現PbⅠ,40 h排出率達66.7%。受精后4 h就有少量的受精卵排出PbⅡ,受精后16 h PbⅡ排出率顯著增加,20 h時達到最高。另外,本研究發現,豬PbⅠ和PbⅡ的排出時間不同,這可能與屠宰場所取卵巢周期不同以及采卵所選卵泡成熟度不一致造成卵母細胞發育不同步有關,有待進一步研究。

表6 不同保存溫度下PbⅡ的形態與活性
同列數據后不同小寫字母表示不同處理間差異顯著(P<0.05)。
人的PbⅠ排出后可存活20 h[20],而小鼠的PbⅠ排出后僅僅存活 6~12 h[1]。劉文華等[14]將小鼠PbⅠ第二次減數分裂中期的卵母細胞在4.0 ℃、室溫和37.5 ℃下進行保存觀察,發現在室溫和37.5 ℃下PbⅠ從細胞核排出后6 h完全失活,而在4.0 ℃下PbⅠ排出后12 h存活率為90%,排出后48 h存活率約為70%。39 ℃下豬極體(包括PbⅠ和PbⅡ)活性很快喪失,隨著保存溫度降低,其存活時間相應延長,在超低溫(-196.0 ℃)條件下,極體的活性保持時間相對較長,保存1 344 h的PbⅠ和PbⅡ存活率仍保持在89.1%和87.0%。說明,降低卵母細胞極體在體外保存的環境溫度,可有效延緩極體的退化與凋亡。同時還發現PbⅡ在39.0 ℃下的存活時間比PbⅠ長,-196.0 ℃低溫冷凍保存下PbⅠ的存活率高于PbⅡ。
PbⅠ和PbⅡ遺傳物質的全能性已被證實并得到公認[21]。極體中胞質很少,主要是細胞核,因此與精子一樣易于冷凍長期保存。極體的冷凍保存為哺乳動物(特別是珍稀動物)雌性種質資源的保存開辟了新途徑,在豬的雌配子(卵母細胞)或受精卵的冷凍保存研究方面雖已獲得成功,但豬卵母細胞脂肪含量高,所以冷凍解凍后的成活率很低。豬極體冷凍保存的成功,繞過豬卵母細胞冷凍的困難,實現了豬雌配子遺傳物質的長期保存。
參考文獻:
[1] EVSIKOV A V, EVSIKOV S V. The first and second polar bodies in mouse oogenesis[J]. Ontogenez, 1995, 26(3): 196-200.
[2] FENG Y L, HALL J L. P-050 birth of normal mice after electrofusion of the second polar body with the male pronucleus: a possible treatment for oocyte-factor infertility[J]. Fertility and Sterility, 1997, 68: S116-S117.
[3] WAKAYAMA T, YANAGIMACHI R. The first polar body can be used for the production of normal offspring in mice[J]. Biology of Reproduction, 1998, 59(1): 100-104.
[4] EBNER T, YAMAN C, MOSER M, et al. Prognostic value of first polar body morphology on fertilization rate and embryo quality in intracytoplasmic sperm injection[J]. Human Reproduction, 2000, 15(2): 427-430.
[5] EBNER T, MOSER M, SOMMERGRUBER M, et al. First polar body morphology and blastocyst formation rate in ICSI patients[J]. Human Reproduction, 2002, 17(9): 2415-2418.
[6] 蘭宗寶,何若鋼,莫品方,等. 豬卵母細胞第一極體排出與否對其早期胚胎發育的影響[J]. 西南師范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 2008, 33(5):64-68.
[7] 鮑時華,彭弋峰. 卵細胞第一極體形態與受精卵及胚胎質量關系的研究[J]. 皖南醫學院學報, 2003, 22(2):86-88.
[8] VERLINSKY Y, GINSBERG N, LIFCHEZ A, et al. Analysis of the first polar body: preconception genetic diagnosis[J]. Human Reproduction, 1990, 5(7): 826-829.
[9] MUNNé S, DAILEY T, SULTAN K M, et al. The use of first polar bodies for preimplantation diagnosis of aneuploidy[J]. MHR: Basic Science of Reproductive Medicine, 1995, 1(2): 94-100.
[10] 李澎濤,王 娜,殷晨星,等. 卵母細胞第一極體形態對受精結局的影響[J]. 廣東醫學, 2016, 37(24):3732-3734.
[11] 谷瑞環,孫貽娟,陸小溦,等. 第二極體排出時間在預測體外受精結局中的價值[J]. 中華臨床醫師雜志(電子版), 2011, 5(14):4127-4132.
[12] 劉 芳,王 瑩,金 銳,等. 常規IVF短時授精第2極體排出及原核形成與胚胎發育潛能的相關性研究[J]. 寧夏醫學雜志, 2013, 35(9):799-802.
[13] EBNER T, MOSER M, YAMAN C, et al. Elective transfer of embryos selected on the basis of first polar body morphology is associated with increased rates of implantation and pregnancy[J]. Fertility and Sterility, 1999, 72(4): 599-603.
[14] 劉文華,孫 潔,王公金,等. 小鼠卵母細胞第一極體的采集與保存[J]. 江蘇農業學報, 2006, 22(1):42-45.
[15] 張世生. 小鼠第二極體發育潛力研究[D]. 重慶:西南農業大學, 2004.
[16] PARK Y S, KIM S S, KIM J M, et al. The effects of duration ofinvitromaturation of bovine oocytes on subsequent development, quality and transfer of embryos[J]. Theriogenology, 2005, 64(1): 123-134.
[17] 孫青原,秦鵬春,劉國藝,等.牛體外授精的程序及超微結構研究[J].動物學報,1996,42(3):303-308.
[18] 林 濤,李曉霞,刁云飛,等. 延邊黃牛卵母細胞激活后第二極體排出的研究[J]. 畜牧與獸醫, 2008, 40(8):50-52.
[19] 華再東,鄭新民,魏慶信,等. 豬分級卵母細胞體外成熟時間規律的研究[J]. 中國畜牧獸醫, 2011, 38(3):155-159.
[20] ORTIZ M E, LUCERO P, CROXATTO H B. Postovulatory aging of human ova: II. spontaneous division of the first polar body[J]. Molecular Reproduction and Development, 1983, 7(3): 269-276.
[21] 范必勤. 哺乳動物第一和第二極體的研究[J]. 農業生物技術學報, 2000, 8(2):103-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