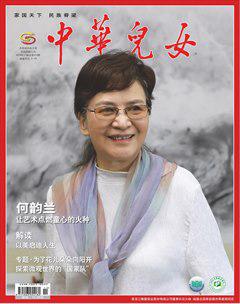李曉冰“博士爺爺”原來是“老頑童”
彭玉冰
“籬落疏疏一徑深,樹頭花落未成陰。兒童急走追黃蝶,飛入菜花無處尋。”讀到楊萬里這首詩,我腦海中浮現(xiàn)的是當(dāng)年在中央人民廣播電臺(tái)少兒部共事多年的老朋友李曉冰。
李曉冰膚黑人隨和。我女兒三歲那年,在我們僅有不到10平米的辦公室被李曉冰用平時(shí)拖書報(bào)用的平板小車拖著,在狹小的空間轉(zhuǎn)圈圈兒,靦腆的女兒快樂開心地叫他“小叔叔”,他開朗的性格特招孩子喜歡。
蓬頭稚子學(xué)垂綸
李曉冰畢業(yè)于河北師范大學(xué)中文系兒童文學(xué)專業(yè)。1984年,中央人民廣播電臺(tái)少兒部領(lǐng)導(dǎo)到學(xué)校指名道姓要了他,令其擔(dān)任《小喇叭》節(jié)目助理編輯。因?yàn)槟菚r(shí)候的少兒部想要個(gè)男丁。這也成了李曉冰事隔多年依然懷揣感恩之心,堅(jiān)守《小喇叭》崗位34年不挪窩,成為中央臺(tái)為數(shù)不多名副其實(shí)“釘子戶”的原動(dòng)力。
剛進(jìn)到《小喇叭》節(jié)目組的李曉冰,信心滿懷地開始選材、改編、寫稿,并盡其所學(xué)把稿子寫得文采飛揚(yáng),那種興奮和認(rèn)真勁兒決不亞于中學(xué)生的作文考試。可一連數(shù)日,他的10多篇稿子一篇也沒通過。看著被退回來的稿子上,《小喇叭》組長、主任們修改的字跡鋪天蓋地,單從字體和顏色上就能感到這稿子所經(jīng)歷程:紅的,黑的,還有毛筆的;草體的,楷體的,甚至還有用代號(hào)的,非仔細(xì)閱讀不能理清。看著冥思苦想出來的那些華麗詞句、奇妙構(gòu)思被毫不留情刪掉,李曉冰第一次領(lǐng)悟到“大白話”對(duì)孩子們的意義。
從那以后,他靜下心來查閱翻看《小喇叭》保留多年的歷史稿本。那一篇篇好聽的故事,那一首首上口的兒歌,沒有絲毫華美語句和離奇內(nèi)容,但展現(xiàn)在他腦海里的卻是一幅幅優(yōu)美的景象和詩一般的語言。他似乎明白了,給孩子們做節(jié)目,第一是要讓他們聽得懂,那些華麗的詞藻遠(yuǎn)不及“白話”來得更直接,更通達(dá);其次是要讓他們理解所講內(nèi)容,那些遠(yuǎn)離他們生活的情節(jié)是無法讓他們產(chǎn)生聯(lián)想和想象的。李曉冰開始意識(shí)到,一個(gè)好的兒童廣播節(jié)目,難就難在要降低自己的“水平”,以兒童的語言和思維去給他們編故事、講故事,去跟他們交流,要學(xué)會(huì)寫大白話。給孩子聽的大白話最難寫,不僅要淺顯易懂,還要有一定思想內(nèi)涵,也就是“白話”所說的道理。而這個(gè)“道理”,李曉冰深思熟慮透了以后,一篇《老鷹飛走了》的稿件終于送審?fù)ㄟ^。這是一篇根據(jù)連環(huán)畫改編的科普小童話,時(shí)長僅有兩分四十秒。這也是李曉冰在《小喇叭》節(jié)目組展開寫作翅膀的第一稿。

在那段日子里,李曉冰寫了系列童話《小熊和他朋友們的故事》,以及四季散文,更多的是創(chuàng)作了一大批兒童廣播劇。其中,以泰坦尼克號(hào)沉船為題材編寫的兒童廣播劇《難船》比電影《泰坦尼春號(hào)》早近兩年播出,并獲得當(dāng)年中國廣播劇獎(jiǎng)兒童劇一等獎(jiǎng)。16集系列廣播短劇《皮克的故事》至今仍頻頻得到小聽眾的點(diǎn)播。童話劇《小烏鴉和它的媽媽》在錄制時(shí),四歲的小演員竟然入戲太深,被劇中人物感動(dòng)得泣不成聲,無法繼續(xù)演播。最后在導(dǎo)演和其他演員以及錄音師的幫助下,“小烏鴉”把同臺(tái)扮演“壞狐貍”的大演員“痛”打一頓之后,才解了心頭之恨。無故挨了頓“暴捶”的“壞狐貍”,正是著名的配音演員桂斌老師。
漸漸成為《小喇叭》節(jié)目主力編輯的李曉冰,前后幾十年精心改編了30多部兒童廣播劇;為收音機(jī)前的孩子們剪輯了七、八部適合兒童收聽的電影錄音;撰寫改編了海量的童話故事。他的作品,兩次榮獲亞廣聯(lián)兒童廣播節(jié)目大獎(jiǎng)。
牧童歡喜騎黃牛
白羊座的李曉冰屬牛。牛屬相的他,性格中也帶著牛的執(zhí)拗勁兒。
上世紀(jì)80年代,在《小喇叭》工作,突破性別“奇”視是一個(gè)很重要的難關(guān)。這不僅要能夠接受在采訪時(shí)幼兒園的小朋友那種驚詫眼光和無意脫口而出的“阿……叔好!”(幸虧孩子們機(jī)靈,臨時(shí)把阿姨的“姨”字改成了“叔”,給他留了半個(gè)面子),而且還要克服男性心理上的“大男人”障礙,學(xué)會(huì)把自己變成一個(gè)“長得老相”的孩子。李曉冰從第一次拿起話筒面對(duì)孩子不知道說什么,到采訪時(shí)一小朋友因擠不到他跟前兒,急得直喊他“爸爸”——這功夫李曉冰耗費(fèi)了5年時(shí)間。到現(xiàn)在,去幼兒園采訪已成為李曉冰的一大樂趣,有時(shí)候坐在幼兒園潔凈的地上給孩子們講故事,故事剛講到一半,就被孩子們疊羅漢似地壓在下面當(dāng)“大灰狼”打——因?yàn)樗麑W(xué)大灰狼的聲音太形像了……這之中那份“憋屈”的樂趣,只有他自己最能解。
說到李曉冰的執(zhí)拗,1980年代的一天李曉冰去天津采訪,一位小朋友給他講喜歡去海邊看海時(shí)說:(大意是)那海浪涌來的時(shí)候,浪花很美,像“一字模”一樣。當(dāng)時(shí)李曉冰沒有聽懂,更想不出那“一字模”是什么樣的景象。之后10多年,一直琢磨這個(gè)“一字模”的他,突然有一天頓悟:原來“一字模”就是天津話的“胰子沫”(肥皂泡)啊!興奮的他把這個(gè)想了10多年才參透的結(jié)果告訴我,電話中都能感受到他飛揚(yáng)起的得意笑意。

愛孩子的人,多半也愛小動(dòng)物。這些年,李曉冰除了采訪孩子,還特喜歡“采訪”動(dòng)物。像狗熊猴子小老虎,羚牛山羊小花貓,甚至連他明知是孔雀卻偏愿叫“鳳凰”的飛禽也采訪過。他說,動(dòng)物是大自然里跟人類最為親近的朋友。它們雖然不說人話,但句句都是真話!他和小聽眾都能聽懂。
一次,李曉冰在哈爾濱街頭,被路遇的一只薩摩耶犬給“強(qiáng)吻”了,正好被同事給抓拍下來。這讓自認(rèn)為有動(dòng)物緣的他更加得意。
忙趁東風(fēng)放紙鳶
在采訪李曉冰的過程中我問他,做了 30多年《小喇叭》節(jié)目,印象最深的是什么?李曉冰偏頭想了想,說:“失敗,全是失敗。從一開始不敢面對(duì)孩子,到后來采訪緊張……”打開“失敗”的話匣子,許許多多難忘的往事便涌上李曉冰心頭。
最讓他耿耿于懷的,是上世紀(jì)90年代初他在延安的一次采訪。
那天,剛剛千辛萬苦采錄了一群爬到樹上的男孩子大談將來要當(dāng)兵打日本鬼子的錄音,忽然聽到不遠(yuǎn)處一位四五歲的小姑娘,一邊唱著“劉胡蘭姐姐是英雄”,一邊拉著娘的手走上坡來。
這音響!這環(huán)境!這機(jī)遇!在李曉冰眼里,絕對(duì)千載難逢!
他立刻跟了過去……結(jié)果,樹上那群男娃的錄音被后面的音響覆蓋了。悔得他呀,不行不行的!
可就在這時(shí),一輛拖拉機(jī)載著一群唱著陜北民歌的孩子開過來,
哇!這音響!這環(huán)境!這機(jī)遇!真真也是千載難逢!李曉冰立刻打開錄音機(jī)沖了過去……結(jié)果,唱歌謠小女孩的音響又被覆蓋了。

每每說起這些,李曉冰鏡片后的眼神依然是青色的!
李曉冰說,還有一次,1994年的7月,他與同事去甘肅山丹軍馬場——中國最大的軍馬場采訪。一到馬場,他就迫不及待要去看牧場上的馬群,而且他心中計(jì)劃的夢想,是一定要親自采錄一組“萬馬奔騰”的音響。但馬場的干事告訴他,七月正是軍馬進(jìn)山吃草的季節(jié),大部分馬群已經(jīng)進(jìn)入了祁連山,留下的也僅是一部分帶著小馬駒的馬群。即便如此,李曉冰也仍不愿放棄采錄馬群的念頭。于是在跟馬場的干事研究多個(gè)方案之后,決定由干事去聯(lián)絡(luò)和組織附近游牧的三個(gè)馬群,第二天中午集結(jié)到一個(gè)不大的山口前,合群沖過山口,造成“萬馬奔騰”的氣勢供他錄制。
這天的李曉冰,興奮得連夜檢測著采訪機(jī)(那時(shí)還使用MD5型盒式采訪機(jī)),甚至每一個(gè)小的環(huán)節(jié)他都反復(fù)檢查試錄了多次。
第二天,李曉冰如約來到那個(gè)山口。舉目一望,果然是個(gè)極好的錄音地點(diǎn):前面是一片開闊平坦的草地,正好把三個(gè)馬群集中起來,并且還有一個(gè)理想的“助跑距離”。問題是,他要按照那位干事的要求,站在山口的中央迎著“萬馬”錄音——這讓他膽量和意志不由打了個(gè)寒蟬。他詢問干事這些馬“是否聽話?”“是不是認(rèn)生?”“會(huì)不會(huì)把他踩成肉醬?”得到放心答復(fù)后,他終于勇敢地站在了馬群的必經(jīng)之地。
十幾分鐘過去,沉悶的馬蹄聲開始震動(dòng)大地,由遠(yuǎn)而近滾雷般迎面撲來。隨著越來越近的蹄震聲,李曉冰的心仿佛提升到了喉嚨,并隨著那三匹高大威武的頭馬出現(xiàn),一起飛了出去。
那一刻,他的世界,無我,無聲,無世界,也無了魂魄。
當(dāng)意識(shí)完全回歸腦海,他回身看到的,只是離他遠(yuǎn)去的幾匹驅(qū)趕著小馬駒的母馬尾巴。好在,他毛發(fā)未損。因?yàn)檐婑R,本身就是一群能夠服從命令的“戰(zhàn)士”。
然而,讓他永生難忘的,不是那三群奔騰涌過的軍馬,而是他因?yàn)榫o張,在采錄音響的時(shí)候,竟有一個(gè)很小很小的db鈕沒有復(fù)位……
側(cè)坐莓苔草映身
采訪李曉冰的過程,歡快而有趣。他本身就是一個(gè)童心不滅的風(fēng)趣之人。
在臺(tái)內(nèi)出版的一本內(nèi)部刊物中他自書道:“話說在中央臺(tái)有一糙老爺們兒,頂著一腦袋白頭發(fā),胡子拉碴不修邊幅,踢足球愛喝酒,貌似民工乙,一把年紀(jì)了還不退休(注:長相與實(shí)際年齡不相符),一打聽,卻是個(gè)給孩子們做節(jié)目的編輯,私下里還號(hào)稱‘博士爺爺。其實(shí),除了小聽眾知道《小喇叭》里有這么個(gè)老頭兒以外,就連隔壁辦公室的老王被來訪的孩子們問及時(shí),竟也是一頭霧水,甚至還悄悄朝《小喇叭》辦公室里張望,自語道:哪兒有什么‘博士爺爺呀?我怎么沒見過?呵呵,這就是本人——李曉冰。一個(gè)蔫不出溜兒的行里‘老炮兒。”的確,“博士爺爺”的名頭比李曉冰本名更響亮。
從1985年開始撰寫“熊系列故事”的李曉冰,他的郵箱名也是用的“bear”(熊)。2011年在李曉冰還擔(dān)任著中國廣播電影電視社會(huì)組織聯(lián)合會(huì)青少廣播節(jié)目工作委員會(huì)秘書長時(shí),他一反社會(huì)上流行的“月亮姐姐”、“知心姐姐”等姐姐系,獨(dú)創(chuàng)了仁慈和藹可親可敬的“博士爺爺”形象。他自編(一位小喇叭的老作者、科普作家石國勇是他的助手)自導(dǎo)自演播的“博士爺爺”,成了孩子們每天晚上8點(diǎn)睡前的知識(shí)寶庫“掌門人”。
為了給孩子灌輸正確的科學(xué)知識(shí),培養(yǎng)孩子探求真理的精神,李曉冰努力把每一期節(jié)目都做成經(jīng)得起科學(xué)檢驗(yàn)的精品。
“長頸鹿脖子為什么那么長?”“近日點(diǎn)和遠(yuǎn)日點(diǎn)的區(qū)別?”“恐龍到底長的什么樣?”李曉冰說,科學(xué)上有爭議的東西,沒有十足的把握不能貿(mào)然告訴孩子。低齡低幼的孩子沒有辨別能力,所以他必須以科學(xué)的態(tài)度進(jìn)行科學(xué)的解釋,要盡可能避免錯(cuò)誤的發(fā)生。
孩子們有問不完的問題,“博士爺爺”李曉冰有難不倒的答案。30多年專注于《小喇叭》節(jié)目的李曉冰,猶如“路人借問遙招手,怕得魚驚不應(yīng)人”的孩童,把自己深深沉靜在“拂堤楊柳醉春煙”的童話世界里,他甘做為孩子們放飛“夢想紙鳶”的和煦東風(fē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