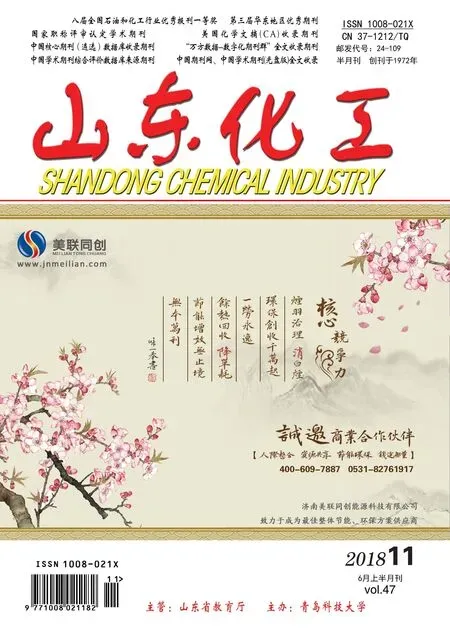淺析翻轉課堂教學中的問題與對策
馬洪娜,檀龍顏
(貴陽中醫學院 藥學院,貴州 貴陽 550025)
翻轉課堂主要包括兩部分:第一部分是在課堂外進行的以計算機為基礎的個性化教學活動,另一部分是在課堂內進行的相互作用的小組學習活動(圖1)[1]。

圖1 翻轉課堂

圖2 以學生為中心的學習理論和方法的關系
近年來,在亞洲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在通過移動信息應用軟件進行彼此之間的交流,比如:WeChat(中國,用戶約7億),WhatsApp(美國,用戶近10億) 和LINE(日本,用戶近5.7億),這些軟件平臺能夠為社交、分享信息和交流提供平臺[2],因此能夠為翻轉課堂提供課堂外教學活動部分的基礎。相互作用的小組學習活動主要包括6種形式,分別為:同伴輔助學習、合作學習、共同學習、同伴指導、以問題為中心的學習和主動學習。根據出版類型、出版年份、課程、教育機構、學習類型、樣本量、測量工具、理論框架、課堂內活動和課堂外活動等指標,將這6種形式的相互作用的小組學習活動關系進行概括和總結[1](圖2)。
1 翻轉課堂在教學中的作用
1.1 符合學生的認知規律
建構學習理論認為學習過程是學生基于原有的知識經驗建構新的知識經驗[3]。教師是知識傳遞者及學習的建構者,應同時重視知識的傳遞與內化過程,而翻轉課堂的“先學后教”,使教學成為知識的處理與轉化過程,體現了“生成型”課堂的特點[4]。同時,基于“學習金字塔”理論,學生課前學習提出問題,課上解決問題,有助于學生對知識的內化[5]。
1.2 體現新的教學形態
翻轉課堂的知識來源為多元化的社會主體,使得傳統教學中教學主體的權威性淡化,使得教學過程中不同主體之間實現平等、民主[6]。翻轉課堂憑借不同的教育技術能夠實現學習的立體化,同時其教學過程較為靈活使得課堂教學發揮出最大功能[4]。
1.3 有助于構建新型師生關系
翻轉課堂翻轉了學生和老師之間的角色,把傳統的“以教師為中心”轉變為“以學生為中心”,實現了教學互動、教學相長[4]。
2 翻轉課堂教學存在的問題與對策
2.1 教育信息化程度不高致使學生負擔加重
目前,我國的教育信息化程度仍然不高,學生在查詢資料方面較為困難,所以這是制約翻轉課堂在國內推廣的重要因素[7]。
2.2 學生課前自主性欠缺,知識準備難以衡量
由于學生從小習慣了傳統式的被動教學方式,加之初高中學習給學生帶來的高壓力、高負擔,導致學生來到大學以后在思想、態度和行動方面的惰性,因而面對新型教學方式缺乏自主性。基于此,對進行教學前學生是否具備足夠的知識量很難做到合理的評估。即使有的教育工作者進行了相關方面的探索,其可信度仍值得進一步的探討[7]。
2.3 課堂教學實施和學生反饋難以把握
學生水平的參差補齊,加之翻轉課堂也沒有標準化的實施方式,因此高校教師只能根據學生的實際情況進行摸索。同時,由于師生情感交流的缺失,加之學生受規避沖突、言談謹慎的影響[8-9],往往造成教師的行動收不到理想的學生反饋,而使教學流于形式。
2.4 缺乏合理的教學效果評價體系
目前,我國翻轉課堂教學仍屬于起步階段,在教學管理和評價體系方面存在較大欠缺,沒有形成合理的教學管理與評價制度,需要進一步探索[10]。這給教學效果的評價帶來了困難,難以進一步指導相應的教學改革。
3 翻轉課堂教學問題的對策
3.1 大力開展慕課、微課、合理優化學生課程設置
目前,各高校在積極開展慕課、微課建設,特別是“中國大學MOOC”APP的上線,使得不同學校的教育資源能夠達到共享。盡管這是一個好的開端,仍存在課程數目少,門類欠缺等問題,還需進一步課程資源的豐富。筆者所在高校教師也在積極開展代表性課程的慕課建設,為本校學生學習提供資源。另一方面,為了使學生能夠合理利用微課資源,學校在學生課程設置上還應加以調整,使學生有時間、有精力學習。
3.2 積極引導學生,創建課前“已有知識”準備評價體系
在開始進行翻轉課堂教學前,教師應與學生進行交流,充分調動學生的積極性,引導學生認可新型教學方式。同時,教師應對于一節課學生應該掌握的基礎知識綜合考慮,通過多種方式進行評價,當達到課堂教學要求時再進行后續的教學活動。當然,這需要學生的積極配合,同時學生和教師的工作量也會相應的增加。所以,學校還應積極進行相應鼓勵機制的探索。
3.3 合理設計課堂教學環節,充分調動學生積極性
為避免教學流于形式,教師在進行課堂教學前應對課堂的各個教學環節進行合理的設計規劃,增加教學環節的趣味性,引導學生積極反饋,營造良好的教學氛圍。同時,建立相應教學互動的獎懲機制,進而達到對不同學生的調動。
3.4 建立符合實際的教學效果評價機制
傳統的教學效果評價主要是通過一張期末試卷評定成績,這樣的形式已不能準確地體現教學效果。目前,筆者所在高校正在積極開展形成性評價措施的探索。
4 結語
翻轉課堂的教學方法是由課堂內教學和課堂外教學活動部分組成,目的是利用合適的互動學習活動的設計培養學生的主動學習,同時,通過學生們的合作和以問題為導向的學習活動建立更具有邏輯的思維技能。由于翻轉課堂的教學方法有更明顯和高效的教學效果,為了確保教學的進步與發展,翻轉課堂的教學研究應該每學期采用通過傳統和調查表的對照研究方式進行客觀測驗,而且,建議教師采取已存在的翻轉課堂研究手段和理論框架指導使用和設計課堂內教學活動。
[1]Bishop J L,Verleger M A.Flipped classroom: A survey of the research—ASEE national conference proceedings[C].Atlanta,2013.
[2]Sweeny S M.Writing for the instant messaging and text messaging generation: Using new literacies to support writing instruction[J].Journal of Adolescent & Adult Literacy,2010,54:121-130.
[3]周 平.基于現代教育技術的翻轉課堂及其理論基礎溯源[J].外語電化教學,2015(2):72-77.
[4]鄭瑞強,盧 宇.高校翻轉課堂教學模式優化設計與實踐反思[J].高校教育管理,2017,11(1):97-103.
[5]王 艷.淺談“學習金字塔”理論在高中新課改的運用[J].科技信息,2013(14):358.
[6]郭文良,和學新.翻轉課堂:背景、理念與特征[J].教育理論與實踐,2015,35(11):3-6.
[7]尹 達.對“翻轉課堂”的再認識[J].當代教育與文化,2014(2):64-67.
[8]于 洋,傅海倫,張艷麗.“翻轉課堂”:信息技術下的“先學后教” [J].教學與管理,2015(30):111-114.
[9]張學新.對分課堂:大學課堂教學改革的新探索[J].復旦教育論壇,2014(5):5-10.
[10]田愛麗.“慕課加翻轉課堂教學”成效的實證研究[J].開放教育研究,2015(6):86-94.